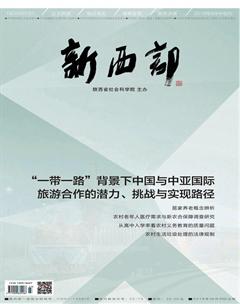居家養老概念辨析
【摘 要】 本文對居家養老概念的不同認知角度進行了梳理,并從老年人的居住場所和養老服務來源兩個角度對居家養老、家庭養老和機構養老進行了有效區分。在此基礎上,深入剖析了居家養老四個方面的鮮明特征,即居家養老適用對象的廣泛性、地位的基礎性、服務需求的多樣性和服務提供主體的多元性,這為認識居家養老的內涵提供了新的視角。
【關鍵詞】 居家養老;家庭養老;機構養老;養老服務需求
自1999年進入老齡社會以來,中國的老齡化程度一直呈持續加深態勢。至2017末,中國60歲及以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別占總人口的17.3%(2.41億)和11.4%(1.58億)(國家統計局,2018),[1]較2016年均增加0.6個百分點,分別超出國際上通用的老齡化標準7.3和4.4個百分點,也意味著養老壓力進一步增大。作為一種有效的養老方式,居家養老在整個養老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居家養老也因此成為政府、學界關注的焦點。綜覽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學者們對居家養老內涵的認識仍是見仁見智,因此亟需對這一概念進行厘清與界定,以期能夠為理論研究者和實際工作者提供參考,也為推進居家養老工作提供借鑒。
一、既有文獻對“居家養老”的界定
目前,學者們對“居家養老”內涵的認識,主要基于以下三種視角:
1、經濟社會發展的視角
這實質上是一種經濟基礎決定論,即認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形式的養老方式,二者一一對應,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養老方式也隨之發生變遷。如張衛東(2000)認為,“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及生產方式決定相應的養老方式”,家庭養老和農業社會(以自然經濟為主)相適應,“養兒防老”、“反哺模式”等觀念是這種方式的典型體現;社會養老為主的養老方式與工業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和社會財富異常豐裕)相適應,介于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之間的居家養老模式和中國目前二元經濟并存(傳統農業和現代化工業并存)相適應,居家養老是“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優勢功能的互補結合”;[2]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養老方式的變化,是一種社會進步的現象,由家庭養老過渡到社會養老,是普遍規律”(袁緝輝,1995)。[3]這方面,張文范(1998)也認為,“居家養老是養老機制的轉變,是傳統家庭養老的歷史延伸”;[4] “居家養老”的提出是人們思想認識上的一次飛躍,居家養老不與家庭養老、機構養老等養老形式并列,是“一種新的養老模式的總稱”(陳大亞,1998)。[5]丁建定(2013)就目前對居家養老存在的認知誤區做了澄清,認為居家養老“源于工業化,其基本支持系統為社會關系,責任主體與支撐單位包括家庭、社會與政府。”,而傳統的家庭養老則適應于農業社會,從家庭養老轉變為居家養老,“既是工業化與城市化所使然,也是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家庭核心化的必然。”[6]
2、養老場所的視角
這種觀點認為,養老方式決定于老年人養老的地點,即在什么地方養老就稱之為什么養老方式。如袁輯輝(1996)認為,居家養老(或家庭養老)和入院養老就是一對從養老場所劃分的概念;[7]在談及有人將居家養老和家庭養老內涵混同時,楊宗傳(2000)指出,居家養老“是指老年人養老的居住方式是在自己的家庭,而不是集中居住在各養老機構,即講的是居住方式問題”,[8]是指“老年人長期居住的熟悉社區及附近的居家養老服務機構向老年人提供的醫護、家政、餐飲、旅游、娛樂、精神慰藉等各種方式的養老服務”(楊春華,2009)。[9]俞賀楠等人(2011)則進一步明確指出,與家庭養老側重于養老資源承擔主體(誰提供)不同,居家養老側重于居住方式上,和機構養老相對應,是“老年人在家居住”,由社區和社會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的“一種社會化養老模式”。[10]
3、養老體系的角度
這種觀點將“居家養老”等同于“養老體系”,即認為居家養老并不是一種單一的養老方式,實質為多種養老方式的綜合(涵蓋機構養老、家庭養老以及社會養老等)。如有學者就認為居家養老是以“居家養老為形式,以社區養老服務網絡為基礎,以國家制度政策法律管理為保證,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的養老體系”(穆光宗,姚遠,1999);[11]居家養老是社會養老與家庭養老的有機結合,是一種“半社會半家庭的養老模式”(陳軍,2001)。[12]相對而言,敬乂嘉和陳若靜(2009)從協作的角度,認為居家養老是“將家庭養老和機構養老的合理要素結合起來,通過進一步整合社會、市場、政府、社區和家庭的養老功能,建立起新型的社會服務體系。”[13]的觀點較為新穎,但根本上仍是認為居家養老是一個養老體系,沒有脫離前述觀點的藩籬。
前述幾種觀點,從不同視角對居家養老的含義進行了界定,為本研究提供了諸多借鑒,特別是經濟發展狀態決定養老方式,居家養老和經濟高速發展相伴而生的觀點,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但有幾點需要明確:(1)家庭養老、居家養老和社會養老,對應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但它們并沒有必然的替代關系,嚴格意義上的家庭養老方式,在中國一些農村地區仍然存在;(2)居家養老和家庭養老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并非如有些學者認為二者是混同的(如袁輯輝,1995);(3)居家養老只是一種養老方式,其單獨一種并不能構成整個養老體系,養老體系的概念包含居家養老的概念。
為了厘清居家養老與其他養老方式之間的區別與聯系,需要一種新的認識居家養老的緯度。
二、界定居家養老的新視角
從前文對既有文獻的回顧中可以發現,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界定了“居家養老”的含義,但也存在一個突出的問題,即在區分居家養老、家庭養老、社會養老、機構養老等的含義時,使用了不同的分類標準,如在中國較早提出居家養老的袁輯輝(1996)認為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應從養老資金來源和提供方式來劃分,在家養老和入院養老主要從資金來源不同劃分;俞賀楠及其合作者(2011)也認為,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主要是從養老的經濟來源上進行的區分,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側重于養老居住方式,而社會養老和家庭養老側重于提供養老資源的承擔主體,家庭養老、社會養老、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在經濟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既互相聯系又相互區分。標準的不統一,實質上也為這幾個概念的區分與界定帶來了一定的難度。
在借鑒學者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對居家養老、家庭養老與機構養老進行區分,兩個根本性的方面必須考量,即居住場所和服務來源。
1、居住場所
居住場所就是老年人的住所,即老年人是住在家里還是其他地方,這是很多研究對居家養老進行界定的一個主要依據,不再贅述。Higgins(1989)對在家養老和機構養老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將二者的不同之處歸納為機構與家的主要特征,包括老年人的居住環境的私密性、居住成員的熟悉程度及相互關系、接受服務的專業化程度、日常活動等方面。她進一步提出了辨別老年人選擇的是機構養老或家庭養老的最簡單途徑,即老年人晚上休息的地點。[14]因此,將老年人的居住場所作為對幾種養老方式區分的一個緯度,具備一定的理論基礎。
2、服務來源
隨著年齡增長,人的身體機能呈下降趨勢,因此,老年人要接受其他人為其提供的各種服務在情理之中。依據提供服務者與老年人的關系,可將服務的來源分為幾種:家庭成員(或其他親屬)、專門的服務機構(包括一些社會組織)、家庭成員與服務機構的組合。當然,家庭成員提供的服務專業化程度相對較低,服務機構提供的專業化程度則比較高。關注養老模式中服務來源問題主要基于以下幾方面的考慮:其一,比較幾種養老方式中的服務問題是很多學者的旨趣所在,比如李鳳琴和陳泉辛(2012)就從服務發生場所、服務的專業化程度、社會認同程度、資金來源、運行機制、信息獲取程度等六個方面對家庭養老、居家養老和機構養老的進行了比較分析;[15]其二,和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相契合,老年人所需要的服務也是分層次的,生活照料、衛生保健等是最基本的服務;伴隨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體育健身、文化教育以及權益維護等服務需求逐漸突出;此外,一部分老年人的情感孤獨與心理健康問題迫切需要解決,[16]與之對應的精神慰藉服務的需求也逐漸增大。這些服務的提供,已經超出了單一主體所能及的范圍;其三,這也是福利多元主義理論的內在要求。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 pluralism)是指:“福利提供不應局限于政府一家,而應由多個部門(如志愿部門、私營部門和非正式部門)共同提供。”[17]政府、市場和家庭在養老服務中依據各自特點,既實現了優勢互補,又可以很好地滿足老年人的服務需求;即控制了福利開支,又減輕了政府在福利提供中的負擔。因此,福利多元主義的主張在現實中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
綜上,從居住場所和服務來源兩個緯度可以對養老方式進行如下劃分:
圖1 幾種不同的養老方式
在圖1中,橫軸表示的是老年人的居住地點,縱軸表示老年人的服務來源。其中,居住地點依據老年人是否在家養老,分為在家和不在家兩種;依據前文對養老服務來源的分析,將后兩種服務來源(專門的服務機構、家庭成員與服務機構的組合)合并為其他組織和個人,服務來源也就成了兩大類,則整個區間就分為了四部分。這四部分分別對應了不同的養老方式:
(1)家庭養老。這種方式下,老年人居住于自己家中,服務來源僅僅為其家人(及其宗親)。正如前文一些學者的觀點,家庭養老是傳統社會(農業社會)最重要的養老方式,但進入現代社會后,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特別是人口流動的加劇,原來的家庭結構、老年人的贍養方式以及養老觀念也都發生了變化,家庭原有的養老功能已經逐步弱化,純粹意義上的家庭養老已經變得比較少見。
(2)居家養老。這種方式下,和家庭養老一樣,老年人居住于自己家中,但服務的來源已經較家庭養老發生了很大改變,由單純的家人(及其宗親)變為了其他社會組織和(或)個人,即服務的來源已經多元化,具有半社會化的特征,這也是居家養老和家庭養老最根本的區別。
(3)機構養老。這是一種社會化的養老方式,這種方式下,老年人不在家居住(只能居住于養老機構),和居家養老一樣,其服務的來源也是多元的,當然也包括老年人的家人(及其宗親),如老年人的親屬定期或不定期探望居住于養老院的老年人,并對其實施必要的服務等。
當然,這里的機構養老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老年療養院、護理院、臨終關懷機構、社會福利院、老年康復機構、托老所、敬老院、社區養老院等都屬于機構養老的范疇。
(4)這種“養老方式”比較特殊,老年人不是居住在自己家里,但服務的來源卻僅僅是自己的家人(及其宗親),這在邏輯上行不通,在現實中也缺乏可行性,因此這種養老方式不存在。
依據上述對居家養老、家庭養老和機構養老的劃分標準,對于居家養老,可以進行界定:所謂居家養老,是和機構養老、家庭養老等養老方式相區別,老年人居住在家中,以家庭為基礎,以社區為依托,由家人和(或)專業的社會組織為老年人提供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服務的一種半社會化養老方式。
這一概念包含幾方面內容:(1)居家養老是一種半社會化的養老方式,有別于家庭養老和機構養老,和家庭養老與機構養老一起構成了養老體系;(2)居家養老的居住地是老年人自己的家,服務來源多元,既有非專業的服務(主要是家人的服務),也有專業化的服務(由專業的為老服務組織提供);(3)服務內容多樣,包括經濟支持、生活照顧和精神慰藉等,以滿足居家老年人不同層面的服務需求。
三、居家養老的特征
前面從居住場所和服務來源兩個緯度,在和家庭養老、機構養老比較的基礎上,對居家養老的內涵進行了界定。為了更深入地認識居家養老,有必要進一步揭示出居家養老的特征。居家養老的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居家養老適用對象的廣泛性
中國人對“家”有特殊的情感——家使血緣關系得以延續,更是人們心靈的棲息地,因此有深刻的文化意蘊。據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2012年的結果顯示,86.7%的老年人傾向于選擇居家養老,并且老年人年齡越大越傾向于選擇居家養老,收入越低也越傾向于選擇居家養老(王軻,2017)。[18]和中國的觀念相似,國外人也認為,“家”是物質維度(可見可感)、社會維度(人類關系)與文化維度(人的價值觀、信仰等)等諸多方面的集合,不僅是僅容棲身的物質場所,更是一種情感寄托(Iecovich,2014),[19]同時也能體現自我、保護自我、促進人格意識的形成(Gitlin,2003),[20]正因如此,居家養老在國外也備受推崇。
適用對象的廣泛性,也為進一步推進居家養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居家養老服務工作,實質上也是在提升老年人福祉。
2、居家養老地位的基礎性
居家養老適用對象的廣泛性、中國傳統文化對“家”的重視、養老積累不足的社會現實,共同決定了中國現階段只能采用居家養老為主、機構養老為輔的養老格局,也即居家養老在養老體系中居于基礎性的地位。這種基礎性地位也和國外的養老服務發展實踐相一致。西方國家已逐步放棄單純的社區照顧模式,從而呈現出一個“從機構化到去機構化進而走向居家養老服務的過程”(丁建定,2013)。
當然,居家養老地位的基礎性是相對于其他養老方式而言的,單純的居家養老并不是養老的全部,居家養老與其他養老方式一起,共同組成完整的養老服務體系;同時,由于居家養老依托于社區進行,因此居家養老基礎性作用的發揮,還需要社區完善的養老服務基礎設施作為支撐。
3、居家養老服務需求的多樣性
前面已述及老年人需求的多層次性,具體到居家養老,這也是養老服務需求多樣性的體現:
首先,與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密切相關的生活照料和護理類服務(如家政服務、購物、清潔、助浴等)是居家養老老年人最主要的服務,這和老年人的身體機能隨年齡增長不斷下降有關;
其次,居家養老老年人對醫療保健類服務(如健康咨詢、衛生保健、陪同看病、上門護理、上門就診、家庭病床等)的需求量也很大,這和前一類服務相比,屬于老年人在基本生活服務滿足之后對生活的更高層面的追求;
再次,精神慰藉類服務(如陪同聊天、婚介服務、娛樂、心理輔導等)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其原因主要有老年人離開工作崗位后的主體地位喪失、喪偶后的孤寂、子女長時間不在身邊的“空巢化”等;
此外,突發情況下(如突然患病或發病)的救急(應急)類服務,對于部分老年人也不可或缺。
因此,居家養老老年人對居家養老服務的需求呈現出多樣化的態勢,已經不再滿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與更加幸福的晚年生活相關的服務也是他們追求的目標,這既和居家養老老年人自身身體狀況相適應,又和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相契合。居家養老服務需求的多樣性,就使為他們提供多樣化的服務成為必要,這也就涉及居家養老服務提供主體的問題。
4、居家養老服務提供主體的多元性
作為居家養老理論支撐之一的福利多元主義認為,社會總福利的提供者除了國家(政府)外,還有市場、家庭等主體。就居家養老服務而言,國家(政府)是最主要但不是唯一的提供主體,家庭和市場都是居家養老服務的提供者。
在提供服務的具體過程中,家庭提供的服務最為直接,但專業化程度相對較低;市場受利潤的驅動,不僅可以提供專業化的服務,而且可以實現服務的高效率;國家(政府)的直接程度和效率相對有限,但可以采用提供和生產相分離的方式,即將原本由國家(政府)直接提供的居家養老服務委托給有相應資質的社會組織,讓這些社會組織為老年人提供服務,也即是采用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的方式,政府是服務的最終提供者,承接服務的社會組織是服務的生產者,從而實現服務的專業化與專門化。
提供居家養老服務的多元主體之間并不是競爭與排斥的關系,而是相互協作、相互補充的,其共同目的都是為了給居家養老的老年人提供更完善、更貼心的服務。
【參考文獻】
[1] 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OL].(2018-03-01)[2018-02-28]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2] 張衛東.居家養老模式的理論探討[J].中國老年學,2000(2)120-122.
[3] 袁緝輝.強化家庭作用 支持居家養老[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06)30-34.
[4] 張文范.堅持和完善家庭養老,積極創造居家養老的新環境[J].中國老年學雜志,1998(3)129-131.
[5] 陳大亞.家庭養老問題探討[J].航天工業管理,1998(9)10-11.
[6] 丁建定.居家養老服務:認識誤區、理性原則及完善對策[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02)20-26.
[7] 袁緝輝.養老的理論與實踐[J].中國老年學雜志,1996(05)300-303.
[8] 楊宗傳.居家養老與中國養老模式[J].經濟評論,2000(03)59-60+68.
[9] 楊春華.城市社區居家養老的困境和出路[J].前沿,2009(08)161-163.
[10] 俞賀楠,王敏,李振.家養老模式的出路研究[J].河南社會科學, 2011(01)02-205+219.
[11] 穆光宗,姚遠.探索中國特色的綜合解決老齡問題的未來之路——“全國家庭養老與社會化養老服務研討會”紀要[J].人口與經濟,1999(2)58-64+17.
[12] 陳軍.居家養老:城市養老模式的選擇[J].社會,2001(09)22-24.
[13] 敬乂嘉, 陳若靜.從協作角度看我國居家養老服務體系的發展與管理創新[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05)133-140.
[14] HIGGINS J . Defining Community Care:Realities and Myths[J].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1989.23(1)3-16.
[15] 李鳳琴,陳泉辛.城市社區居家養老服務模式探索——以南京市鼓樓區政府向“心貼心老年服務中心”購買服務為例[J].西北人口,2012(1)46-50.
[16] 成海軍.當前中國老年人社會福利的困境與對策[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123-129.
[17] 黃晨熹.社會福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9.
[18] 王軻.老年人的資源稟賦與養老方式選擇——基于CLASS 2012數據的實證檢驗[J].西部論壇,2017.27(04)116-124.
[19] IECOVICH ESTHER. Aging in Place:From Theory to Practice[J].Anthropological Notebooks,2014.21(1)21-33.
[20] GITLIN L N. Conducting Research on Home Environments:Lessons Learned and New Directions[J]. The Gerontologist,2003.43(5)628-637.
【作者簡介】
王 軻(1982—)男,河南泌陽人,管理學博士,博士后,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地方政府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