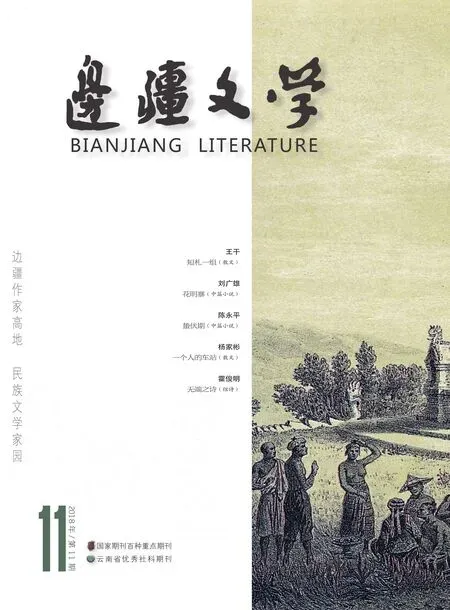兩代人
唐曉華
一
十八歲我們都向往遠方,眺望山,就認為山的背后會有不一樣的風景。帶著去看世界的迷茫和激動,我參軍入伍,第一次遠離家鄉。從湖南到了四川,那是一個峨眉山腳下叫黑橋的附近的無名山頭。對于我這個從小生長在農村的青年,站在那個無名山頭上,看著周圍幾十里連綿不盡的山巒,我想,那天我的失望肯定如那天的黃昏一樣籠罩四野。
這個山頭在群山懷抱之中,偏僻、孤獨,走出山頭幾里路才能看見集鎮。山頭上,駐有我們偵察連和防化連兩個連隊,營房都是平層的,聽說是早前在這里的一個汽車運輸公司留下的,很陳舊,就像堆在山上的沒有人要的廢舊盒子。山下有幾戶農家,或許還有一條孤獨的老狗。在靠近農家的一側,距離連隊二百多米遠的山坳中,有一條蜿蜒的公路,是樂山通往峨眉的主干道,黃昏時從山頂上往下望,路像一條斷斷續續的河流,也像一條被雨水洗得發白的扔在草叢中的繩索。當地老百姓對當兵的很好,過往的客車看見有當兵的招手搭車時,都會一腳剎車停下來。
到了連隊后,我對能夠分在城里的同鄉很羨慕,每次請假外出,我們不是去名山峨眉山和樂山大佛等景點,而是迫不及待地到樂山和峨眉的縣城里去逛街,五光十色、琳瑯滿目,城市的熱鬧和浮華,從來讓我們留連忘返。或許是我繼承了我父親不認輸、做事努力的脾性,加上連隊干部見我是帶著畫夾到部隊的,喜歡寫寫畫畫,就把我調到連部當了通信員。第二年,還推薦我報考了軍校。我到連隊后,就聽說我們連隊已經有好幾年沒有人考上軍校了。為了給我報考軍校創造條件,在連隊主持工作的副連長臨時動議讓我當了副班長。副連長是湖北人,胖高個,講一口普通話夾雜著地方口音,像流水里滾著流沙和卵石。但軍事素質過硬,在連隊,這樣的領導威望極高,很多兵都懼怕他、服氣他。在他宣布我任副班長的命令時,一些戰友是不服氣的,在隊列中紛紛交頭接耳,我自己也覺得過意不去,渾身不自在。特別是一些兵齡比我老的,軍事素質比我好的戰友,而我卻僅僅因為要報考軍校就當上了副班長。如果考不上軍校,那就太對不起連隊對我的關心和寄予的厚望了,當然也無法面對戰友的眼光。我在師部參加完軍事院校招生統考回到連隊后不久的一天上午,我記得那天陽光明媚,萬物清晰,我正帶著全班在訓練場上搞器械訓練,突然耳邊響起“嘟嘟嘟”的緊急集合的哨聲。全連列隊整齊清點人數后,才發現在平時連隊干部站的地方,多了幾位陌生的軍官,個個神態嚴肅、肅殺。原來是師副參謀長和偵察科長帶著一些人來連隊宣布作戰命令的。當天下午,連隊的兵一律理了清一色的光頭,晚上,在野草涌動的山坡上,我們看了一場《南征北戰》的戰爭影片,算是出征前的慰問。
幾個月后,我從戰友的來信中知道我已經考上軍校,師部機關的大門口已經張貼了軍校錄取人員的名單,當我得知這一消息時,已經距離戰友寫信的時間有兩個月了。也許是命中注定,我這一生該與云南有緣。當兵時,我從四川到云南參加作戰,軍校畢業分配時,其中大部分的學員分到了其他省份,而我又來到云南。轉業后,又留在云南工作和生活。我是湖南人,但是我對湖南的了解沒有云南的多,我到過云南的一百多個縣,而在我的故鄉,卻只到過有親人居住的三個縣市和省會城市長沙。
二
我的父親唐自書也是個軍人,高大個子、臉方長,顴骨微突,目光犀利,生于1934年,因為上世紀50年代沒能入朝參戰,至今耿耿于懷。至今依然最喜歡說抗美援朝第二批的事,這是他的驕傲,也是他的塊壘。
1950年10月,戰爭爆發后不久,部隊要征兵開赴朝鮮,村頭的土墻上張貼了紅紙書寫的標語。那時候父親剛滿十六歲,可當父親氣喘吁吁地到了鄉政府后,接兵的干部看他還不滿十六歲,硬是沒有接收他。許多年后,父親說起當時參軍的動機,一是毛頭小伙子一個,雖不完全明白事理,但知道響應號召;二是在農村的日子太苦,經常連飯都吃不飽,沒有像樣的衣服穿,盼望當兵能在戰場上建功立業,改變家庭貧困生活的窘境。直到第二年的1月,部隊開始征召第二批抗美援朝的兵員。當時的鄉政府在火湘橋,離村里有十多公里的土路,爺爺走得早,家里缺乏勞動力,加上父親的年齡又小,奶奶說什么也舍不得讓父親去當兵,一路哭著喊著追了出來,羊腸般的土路坑坑洼洼,凌晨的小雨讓人走在路上像是蕩船,奶奶追了一半的路程就跑不動了,齊耳短發被風吹得零亂,悲傷的哭聲,也沒能趕上父親的步伐。但父親他們坐上火車后才被告知,這批原本第二批抗美援朝的兵員,因為戰場情況的好轉,不再開赴朝鮮了,要送去福建的部隊。故鄉漸遠,我無法想象父親坐在轟隆隆的鐵皮列車上,回望落日中故鄉村墟的心境。只知道后來父親被分到了炮兵十四團當了一名炮兵。且那支部隊打過淮海,過江打過上海,是一支打硬仗出了名的部隊,1952年才轉隸炮兵建制。能在一支有著光輝歲月和歷史的部隊服役,我想父親是感到榮耀的。即使在晚年恬淡的生活中,我依然能夠從他閃爍的眼光中,看見他對他的軍旅生涯的熱愛。
從農村走出來的孩子大都能夠吃苦耐勞,父親又是個要面子的人,不管做什么事都不甘心落后,事事爭表現,又寫得一手好字的父親,在部隊的那些年,算得上是成功的了,他立了功,在全團只有一個入黨名額的情況下,還光榮地入了黨。生命里有了當兵的歷史,一輩子都會有割舍不開的軍人情結。這我深有體會,我想父親也是。在父親轉業后的幾十年來,他穿的用的,總是喜歡部隊的東西,老式軍服、膠鞋,部隊時帶來的生活習慣——就連在門球場上擔任裁判時的判罰動作,也規范有序,干凈利落,口令聲如洪鐘就像當年指揮炮兵炮擊金門一樣。
三
人一生都在路上走,不管走了多遠,腦海里都無法走出故鄉的版圖。有時恰恰相反,離開家鄉的時間越久,思鄉的情緒卻越濃。光陰流轉,人情涼暖,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這些年,走過和歷經的山水很多已經忘卻,而家鄉的山山水水、孩提時的點點滴滴,卻時常憶及,并越來越清晰。
父親勤奮節儉,他轉業到地方工作的時候,每個月領著三十四元五角錢的工資,在維持他和兩個哥哥的日常生活開支外,還要想方設法省下點錢,留給在鄉下生活的我和姐姐用。整個家庭經濟上的捉襟見肘、入不敷出,讓我們兄妹幾人很早就懂了事,兩個哥哥每天放學后和星期天,就到火柴廠去背回一些火柴盒的半成品,在別的小孩外出玩耍時,就在家里糊火柴盒。一盒裝有火柴棒的火柴,在商店里售價是二分錢,兩個哥哥糊十個火柴盒只能換來二厘錢的報酬,每次賺了錢后,都舍不得用,都要將硬幣全部存在一個鐵罐罐里,每天都數一遍,仿佛多數幾遍,錢就會多出幾分那樣。省錢的辦法,在父親那兒也是各式各樣,到外地出差時,他帶著自做的辣子醬下飯,省單位的伙食補貼;食堂里吃飯時,三個人只買二份菜吃,只買素菜不買葷菜也是經常的省錢方式,所以那些年父親學會了腌制各種咸菜,家他腌制的蒜臺、黃瓜、生姜、辣子,后來竟然還特別可口。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父親到外縣出差,看見商店里有便宜的白毛巾賣,三條毛巾可以做一件衣服,他就買了一大梱白色的大毛巾回來,染了色后給兩個哥哥縫制衣服穿。
然后就是對我們管教特別嚴厲。我從小就和姐姐跟著母親在鄉下生活,父親帶著兩個哥哥在城里讀書。有一次我從鄉下到父親單位去玩,看到過道上有一件小物品,覺得很好看,就懵懵懂懂地拿回了家,父親知道后,十分生氣,左手五指抓著我的屁股,右手抻開巴掌就揍了我一頓,兩個哥哥在旁邊嚇得也不敢出聲。打完了我,父親就問我在哪拿的,牽著我的手,將小物品還給了人家,還反復向人家解釋和賠禮道歉,嘴里不斷說:小孩不懂事,小孩不懂事。而在之前,我每次到父親那里,父親總是含著寬厚的微笑,向我伸出溺愛的雙臂。
初中畢業后,我心想高中可能考不上了,很沮喪,對前途一片茫然,就去找父親,想在城里找點事做。那晚,父親和我并肩走在街上,父親一會兒沉思不語,一會兒自言自語。返回時,碰見一位四十來歲的阿姨,這位阿姨聽說我剛畢業,想找點事做,想讓我跟著她去砂石場碎石,第二天一大早,父親就把我帶到了她家門口。砂石場人聲嘈雜,大多是中年婦女和一些年齡跟我差不多的青年。砂石是送去鋼鐵廠煉鋼用的,要將石頭碎成核桃大小的多邊形,才能驗收合格,按立方米計價。每次放炮炸石后,人們都爭先恐后,蜂擁而上。一天下來,我累得精疲力竭,穿在身上的白襯衣被汗水浸透得變成了黃顏色,右手掌也被小鐵錘的竹片手柄磨出了水泡。黃昏時,我回到家,父親一見我就說:還是要讀書才有出息呀!若干年后,我才發現,這是父親對我進行的最好的教育。
記憶總在留存給我們人生的另一個側面,那么多年了,我依然記得我拿走小東西的縣革委會的,那個堆滿了壞掉的椅子、破敗的蜂煤球、在鍋碗瓢盆的叮叮當當的打架聲中,永遠彌漫著一股油煙味的昏暗的走道,以及走道望出去的幾棟青磚的瓦房,瓦房旁邊空蕩蕩的籃球場,和籃球場邊停著的綠色吉普車。
還有我中學畢業和父親并肩走在路燈下的那一晚,有些焦躁的氣氛和路燈下飄飄蕩蕩的碎屑,那飄落的碎屑,像一些蛾子碎下來的翅膀。當然,還有碎石場那被削平了半邊的石山、轟隆隆的人聲和叮叮當當的碎石聲,已經烈日下的滾滾塵土和我耳后的汗滴。
四
我坐在父親的辦公室里,看他起身提起一個竹編外殼熱水瓶,若有所思地擰開軟木塞,給我倒了杯霧氣騰騰的白開水后,然后左手按住桌上的黑色手搖電話機,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著話柄搖了幾圈子后,拿起話筒,請單位的總機掛長途電話,到縣民政局了解情況。通話結束后,父親反復告訴接線員,這是私人電話,一定要從自己的工資中扣除。這是在我當兵兩年后,請父親幫忙問參軍補助費的場景。我坐在父親辦公桌的對面,聽到他和接線員的對話,心想父親也太死板了,打個電話是公是私別人未必會知道,父親從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想法,對我說:“別人是不知道,但是我們自己清楚”。三十多年的工作中,當初父親與接線員對話時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與之相反,父親總愛說的一句話是:朋友不怕多,仇人怕一個。在朋友眼中,他有著天然的親和力和幽默感,還經常根據當時的情景脫口而出打油詩。無論是單位離退休的老同事,還是家屬院里的年輕人,都喜歡聽父親談天說地。有父親在的地方,總會爆發出陣陣笑聲。特別是在退休之后,他的一些同事和朋友在壽辰、喬遷等喜慶事時,也都喜歡邀請父親到場,父親也都會說上些開心的俏皮話,活躍氣氛。父親好友的兒子程一平,在新房落成喬遷之喜時,父親不顧年邁行動不便,趕到幾十里外的鄉下,前去慶賀。父親看見這里的村村寨寨都通了水泥路,鎮上新建了許多房屋,很高興,現場即興書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橫塘鎮成鬧市,民眾歡天喜地”;下聯是:“小河邊建高樓,我家幸福來臨。”橫塘鎮地處山區,每逢街子天,方圓數里的村民們都要到鎮上來趕街。改革開放后,特別是近幾年來,這里的交通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村民們的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以說,父親的這副對聯,正是我國新型農村面貌發生巨大變化的真實寫照。
父親喜歡用打油詩的形式,喻事說理和為年輕人勵志。為教育晚輩們為人處事,搞好鄰里關系,還專門寫有一首打油詩:“見面問個好,點頭笑一笑;鄰里常往來,和睦最重要”。老家姑家塘的一位親戚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困難,想打退堂鼓。父親知道后,就為她打氣鼓勁:“困難好比是座山,看你敢攀不敢攀,膽小的永遠在山下,膽大的就能站頂端;困難好比是石頭,決心好比是榔頭,榔頭敲石頭,困難就低頭”。在家里,父親也同樣喜歡用打油詩表達自己的心情。大年三十這天,在除夕夜的年夜飯桌上,全家人四世同堂,父親異常高興,興致勃勃,當即吟到:“兒孫孝敬好,老人壽年高;年年鬧春節,歲歲都歡笑。”,見父親如此高興,全家人心里也是樂滋滋的,常年在外地的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父母的健康,就是兒女的幸福”和“家有老人是個寶”的真切含義。畢竟我的父親,已經是80多歲的高壽老人了。
但父親不服老,對社會上流行起一些新的時潮時,他也喜歡去琢磨。送了一臺電腦給了父親,他還笨手笨腳地學著在電腦上與我視頻。當流行起在手機微信上視頻聊天后,他就時常與我在微信上視頻聊天。并得意洋洋地到處宣稱:我的QQ號和微信號的昵稱都叫活到老,學到老。以前通信太不方便了,現在不管相隔多遠的距離,拿起手機就可以通話和視頻,這是他以前做夢都沒有想到的。大哥在讀小學的時候,提著熱水瓶到鍋爐房去打開水,因為看管鍋爐的人離開崗位的時間過長,水溫超過了極限,鍋爐發生了爆炸,大哥的全身被開水高度燙傷,危及到了生命,不巧的是父親又在外出差,單位的人打了一天多的電話才找到父親。想想當年,看看現在,通信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啊。
去年春節我回家時,第一次見到父親流淚。父親流淚是因為話題突然轉到爺爺奶奶時。他的聲音突然變得低沉而沙啞,低著頭一直在看腳下的地面。
在我出生前,爺爺奶奶就已不在人世。太爺爺生有爺爺和大爺爺兩兄弟,爺爺是老二,叫唐貴燦,大爺爺叫唐貴炳。爺爺生于1900年,在種田的間隙,還靠著給村里村外的人做些木工活和縫制衣服來養活家人,1947年5月,他在四十七歲那年,因貧窮和過度勞累患了癆病,無錢醫治而早逝。奶奶叫卿桂蘭,在大鬧饑荒時餓死了。她離世時才五十多歲。父親小時候日子過得很苦,家境十分貧寒,經常是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煮青菜時鍋里都沒有油放,因為家里太窮了,無錢供他讀書,在十一歲時,他才偷偷地跑到鄰村的一個私塾里,零零星星地讀了兩年的私塾。他十三歲時下地種田,也就是那年,他當了村里的兒童團團長,十五歲時,全國剛解放不久,因為個子高大,還當上了民兵營長。奶奶生有父親和叔叔兩兄弟,因為爺爺奶奶走得早,所以父親一生都和叔叔相依為命,感情特別好,叔叔小父親六歲,人老實,不多說話,在四十多歲時才和嬸娘生下堂妹。父親把堂妹視為己出,拿堂妹比我和哥哥姐姐幾個還要緊,從堂妹一出生到讀完大學,事無巨細,樣樣關心,就連堂妹叫曉亮的名字也都是父親取的,直到堂妹考上公務員,當了一名警察后,他才徹底放下心來。
父親四十多歲時,就患有風濕性關節炎,天氣一冷,四肢骨關節就疼痛。二十多年前來昆明看我時,就查出右大腦毛細血管梗塞,這些年來,一直靠著藥物治療。歲月不饒人,辛苦操勞了一輩子的父親,已逐漸顯現出來老年人的形態:躬著背、步子緩慢,讀書看報和擺動東西時,也顯得有些遲緩了,在門球場上打球時,動作也沒有了前些年的靈敏。所以我最怕離開家時父親送我,我最怕車子駛離了老遠,后視鏡中,父親還站在屋外幾十米遠的斜坡路上。
第一次見到父親流淚的那天,天空一掃陰綿細雨,突然放晴,在涼意漸少的和風中,一家人圍坐在門外還沒有干透的水泥路面上,聽父親聊天。門外幾十幢清一色的紅磚墻青瓦屋頂的平層老房子,從坡頂到坡下呈階梯形,在一條水泥路的兩邊依次并排矗立著,因為地勢較高,視野開闊,可以看見大半個縣城的面貌。斜面有一顆沒了樹葉的大樹,上面還零星掛著不知名的果子。每一幢房子的門前,都留有十多米寬的空地,大嫂種的蔬菜在藍空的映照下,正在那塊空地中迎風泛綠。

劉宇 雪山下 36cm×51cm 水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