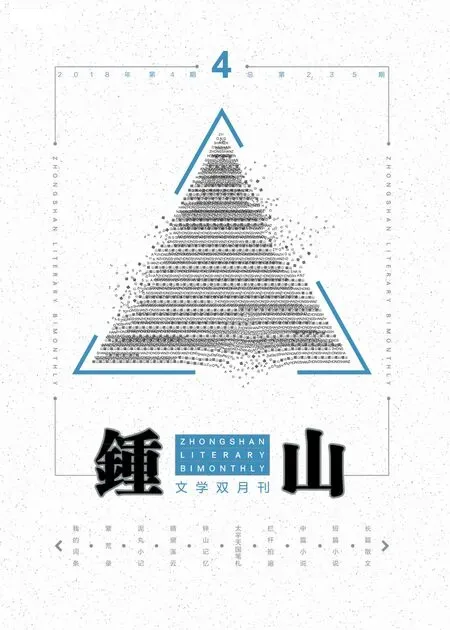遠 游
韋 隴
W E I L O N G
春華的女兒珠珠,跟小馬老師學鋼琴一年多了。珠珠12歲生日這天,春華給她買了架鋼琴,并邀請小馬過來。
此前,春華每周兩次送珠珠到小馬家里練琴,她發現自己和小馬特別投緣,每次都有說不完的話。春華就有了想法,想讓小馬到自己家里來教鋼琴,這樣,等到每次的教學結束之后,她可以和小馬從容地喝茶、聊天,想怎么聊就怎么聊。她知道小馬有晨練的習慣,練的是“快走”。這一天,她特地去了一家“耐克”專賣店,給小馬買了一雙中高檔的運動鞋。買鞋時她在想,本來只是給女兒找個鋼琴老師,沒想到給自己找了個知己,實在是值得慶幸的事。
春華下廚弄了幾樣精致的小菜,不一會兒,小馬來了,還給珠珠帶了個生日蛋糕。珠珠吹了蠟燭,閉著眼睛不肯睜開。春華和小馬都看著珠珠的眼睛,好生奇怪。過了許久,珠珠眼睛開了,像從夢里醒來一樣,先看一眼媽媽,又看一眼小馬老師,又朝門口瞅了瞅,嘴一扁,哭了。
“我剛才許的愿是‘爸爸及時出現’。”
春華和小馬都呆住了。春華安慰女兒說:“沒事,以后讓小馬老師經常過來看你,好不好?”
珠珠點了一下頭,眼里含著淚。春華又問小馬老師:“你說呢?小馬老師?”春華在稱呼上平時叫“小馬”,當著女兒叫“小馬老師”。小馬一千個愿意地說:“一定的,那是一定的。珠珠又乖巧,又懂事,可人著呢。”
這時,春華才提出讓小馬到家里來教珠珠鋼琴,小馬再無異議。接著,她們談了談珠珠的學習。小馬說,珠珠的坐姿、手型、觸鍵、看譜這些基本動作已完全沒有問題,接下來是要練好曲子。之前她已經學過拜厄、車爾尼以及肖邦的一些練習曲,接下來要集中精力練好《東方紅》,因為三個多月后縣里要組織一場三百多臺的鋼琴大合奏,她希望珠珠也能報名參加。到時候去面試一下,應該沒問題的,小馬說,她也是那天的面試評委之一。
珠珠早些吃好,到自己房間寫作業去了。春華表示應該喝點酒,說著開了瓶紅酒,先給小馬倒了半杯,又給自己倒了半杯。兩個人你一口我一口喝了起來。小馬一邊剔著蟹腳,說:“珠珠真漂亮,和你一樣漂亮,這孩子真是懂事。”
春華說:“其實你也很好,小馬你知道嗎?你一坐到鋼琴前,那種氣質,連我都著迷。”
小馬搖搖頭,嘆了口氣。
春華說:“怎么?難道你家先生沒有告訴你?”
小馬笑了:“我家先生?沒有。不過有你的贊美,我也是很開心的。”
春華說:“對了,你等等,我給你買了雙鞋子。沒有事先征求你的同意,你不會怪我吧?”
小馬說:“哎呀呀!我怎么受得起呢?”
說話間,春華拿出了鞋。小馬試了,尺寸正好,合腳又好看。
小馬說:“謝謝你春華姐。”
春華說:“這么叫太俗氣,我不喜歡。”
小馬說:“嗯,我也覺得,但怎么叫‘雅氣’一點呢?”
春華說:“我發現自古以來,女子之間的稱呼禮節,其實常常是模仿男子的,比如《紅樓夢》中大觀園女子之間的詩文唱酬,經常稱‘子’、‘君’什么的。”
小馬說:“你這么說我就想起了《紅樓夢》中有一首史湘云的《對菊》,詩中就有‘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之句,顯見是女子以男士自喻。”
春華說:“我也記得這一首,接下來二句是,‘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唯有我知音’。”
小馬說:“怎么這么巧,你也記得這首詩?”
春華說:“我讀書不多,但《紅樓夢》倒是反復地讀了又讀。”
小馬說:“哎呀呀!我也喜歡讀紅樓。”
春華說:“這叫什么,不就是剛才說的‘看來唯有我知音’嗎?”
二人越說越投緣,話里都有了相見恨晚的意思。其實這個意思她們早就想表達了,只是苦于沒有這樣的方便,現在她們你一口我一口地飲著紅酒,你一句我一句地說著知心話,這個意思就像酒瓶里的紅酒一樣汩汩流出,而她們說的每一句話,又像喝進口里的紅酒一樣,甜甜澀澀的,卻又勁道十足。
“干脆,”春華歪著頭看著小馬說,“我們也不要姐妹相稱了,你叫我哥哥,我叫你妹妹,怎樣?”
小馬看春華說得認真,猶疑了一下,低聲說:“沒人的時候……也是……可以……”
春華攬住了小馬的腰,模仿越劇里寶玉的腔調叫了聲:“好妹妹!”
小馬的臉剎時紅得跟酒一樣。
不知不覺間,一瓶紅酒見底了。小馬的臉這下真的紅了。小馬說吃不消了,暈暈乎乎的。接著,暈暈乎乎的小馬,講起了一個暈暈乎乎的故事。
小馬講,她有個女同學,離婚后,同時交了兩個男朋友,當然了,一方面是生理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慢慢考察,想物色一個再婚對象。有一天晚上,兩個男友先后來到她的家里。一個是事先說好的,早一步來。才幾分鐘,門鈴響了,她以為是物業管理人員——這不是常有的事嗎?——她開門一看,卻是另一個男友。只好也讓他進來。她想來想去,這可怎么辦呢?情急之下,也是一時糊涂,她打電話招來了一個單身女友,介紹給后來的這一位。其結果是,一番酒菜招待過后,當晚二男二女同處一室,情不自禁地過了銷魂的一夜。后來兩個男人都把這件奇事說給各自的朋友分享。而這個女同學,因為這次事故,跟兩個男友同時分了手,直到現在也沒有找到結婚對象。
春華見小馬有了醉態,勸她到床上躺一會兒。小馬說不用,她在沙發上歪一下就行。小馬先是靠在沙發上,春華收拾完桌子,發現她已躺下來,睡著了。春華去臥室拿了件被單給她蓋上,再去收拾廚房。忙前忙后將近一個小時,中間春華又過來看了小馬兩次。倒半杯開水放在茶幾上,因怕小馬身上太單薄了,容易著涼,她又拿了件珠珠小時候用的四方形小毛毯,輕輕蓋在小馬腹部。這時,小馬長長的睫毛動了一下,又動了一下,醒了。
“幾點了?”小馬問。
“不急,喝一杯蜂蜜醒醒酒。”春華說著倒了兩勺蜂蜜在溫開水里,用一把湯匙拌勻了,端給小馬喝。又看了看時間,發現珠珠該上學了。十分鐘后,她開車送珠珠去了學校,又送小馬回了家,再到單位上班。
“你睡醒的時候,睫毛一動一動,我就想起了陽臺上的那盆含羞草。”她在車里對小馬說。
“哈!”小馬說,“下次我要看看陽臺上的那個我。”
下班后回到家里,春華用一個小噴壺給含羞草灑了點水。盯著含羞草出了一會兒神。含羞草承受了水,葉子慢慢閉合起來,而枝條紛紛柔順下去,幾秒鐘后,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小馬在睡和醒之間的那一瞬間,也是如此。
珠珠學琴時間安排在周五晚上7點和周日上午9點。
每到周日,珠珠練完琴,春華已經弄好了飯菜,留小馬吃飯。吃了飯,珠珠有時候出去玩,更多時候回房間寫作業,或者上上網,或者睡覺。春華和小馬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喝紅茶,嗑瓜子,是那種白色的南瓜籽。前幾次春華備了好幾樣茶點,但她發現小馬只喜歡吃白瓜子,別的一點也沒動,后來她就每個周末下班時買回6包,其中4包是她和小馬的茶點,2包是珠珠的零食。
她們喝茶,懶懶散散地聊一些生活里的小八卦,偶爾也說說各自私生活。小馬不時會提到珠珠學琴的進度和現在面臨的問題,但春華似乎對這個話題不怎么感興趣,沒說上幾句,話題就被她改變,引向一個她所預設的方向。
“這個你可以跟珠珠說,我想她會明白的……哦對了,我現在忽然想起了‘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春華以類似這樣的方式把話題一變再變,“生活真是荒唐。妹妹,你一定有什么話想問我,有嗎?”
小馬點了點頭。
“你在我家里從來沒有見過男人。我想沒有一個女人會忽略這種現象的,對嗎?”
小馬說:“是啊!我心里想什么,你總是知道。”
春華說:“我沒有跟別人說過,但是我想跟你說。”
小馬說:“你說什么我都喜歡聽。”
春華把放著白瓜子的碟子移到小馬左手邊的茶幾上,說:“我要跟你說,是因為我知道,我注定要跟你——而不是別人——分享我的隱私。”
怎么說呢?說是隱私,其實也是極普遍的事。現如今這個社會,誰的感情生活沒有個三波四折的?有的人看似沒有,好像各方面都很好,好得讓人嫉妒,但我總懷疑那不是真的,那種表面的狀態里一定隱藏著我們所不知道的內情,就像我一樣。你也知道,雖然我只是個縣文聯副主席,身份微不足道,但我的感情生活稍有變故,就必然會有人說三道四,它會成為別人攻擊、貶損我的武器。
春華繼續說,這是個濫情的時代,這個時代幾乎沒有什么愛情能夠自始至終保持完好無損,出軌或移情別戀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我實在不明白問題究竟出在哪里,我只知道,三年前他就不碰我了,睡覺時躺在床上,他背對著我,一直看電視,看到睡著又醒來時,“叭”一聲摁掉遙控器。那“叭”的一聲,是他親手切斷了我最后的一個期待。三年來的日復一日,我的期待早已蕩然無存。早上起來,他有時會問我一聲,昨晚你睡得可好?一開始我說一個“好”字,后來我默然不語,不再表示什么,而他也就不再問了。
我經常出差,有時一走好幾天,回到家里,我就發現了家里有“狼狽為奸”的蛛絲馬跡。我什么也沒說,只是給自己在另一個房間鋪了張床——不想再碰那張床了。可他終于還是失去了耐心,提出離婚。我說,再等等。他說,反正不能挽回了,還等什么?我說我還沒準備好,再等等。其實我對他早就沒有任何幻想了,可他不知道,以為我心存幻想。于是他越來越過分,在家里公開和別的女人在電話里調情說笑,想以此讓我徹底絕望。每過幾天他就會問我一次,想好了嗎?我說,再等等。
我終于等到了那個時候。再一次出差前,我在他的臥室里安裝了攝像頭……你簡直難以想像,他們在一起時是那么的放肆和淫蕩,先是一起沖涼,在浴室里就交纏在一起了,纏成一團水淋淋的,像兩條水蛇。從浴室出來后,窗前、地上、床沿,遍地狼煙,到處是戰場,他們站著、跪著、側著、趴著,各種奇葩的交歡姿態,眼、耳、鼻、舌、身,樣樣都用到淋漓盡致,說實話,我見所未見——他的表現與我所認識的他完全判若兩人。說來可笑,雖然這種情景深深剌痛、傷害了我,可我還是禁不住被他們撩撥得春心激蕩,欲罷不能。
我把攝像作了備份,而后告訴了他。他也是在政府部門從職的,這種事絕對見不得光,如果他把我逼急了,我就破釜沉舟,大不了兩敗俱傷。他一聽就知道我并非虛言恫嚇,他意識到我要敲詐他。他表示,可以把一切財產都給我,他可以凈身出戶。我說不是這意思,財產各半,女兒珠珠歸我,他也可以搬出去住,我們私下里協議離婚,只是不必辦離婚手續。他很詫異,說那你要什么?我說,只有一點要求,每周六晚上,你必須陪我在我們小區周圍散步一個半小時,并把這一點也寫進協議里。他完全沒有料到,我的“敲詐”竟然如此的溫情。但我知道,如果不是他有把柄落在我的手里,哪怕這一點要求,他也絕不可能答應。
哦!他當然答應,也做到了——他也只能如此。現在,每周六他都陪我散步。我們手牽著手,走在小區的花園里,每次都會遇到一些朋友、熟人或彼此的同事,他們跟我們打招呼,點點頭,或隨便聊上幾句,他們的眼里滿是羨慕。
于我而言,這就夠了。
周六晚7點20分,小馬悄悄來到春華居住的小區,在一棵比較隱蔽的大樹下找了張石凳子坐著。這地方距離前方道路有十幾米遠,四周的樹木疏密有致,路旁的燈光散散落落漏進枝葉之間,形同一張破網。小馬孤零零坐在那里,感覺自己就像一條漏網之魚。她想起春華說的話:“我注定要跟你——而不是別人——分享我的隱私。”便隱隱覺得“注定”二字頗有些玄妙,到底怎么玄妙卻又說不清楚。
大約過了十幾分鐘,便看見春華挽著一個男人的手臂,從她的左前方走來。小馬覺得他們不可能發現她,她只需要像錄像機一樣,靜靜地觀察他們,錄下他們從出現到消失的這一段路程就可以了,她的目的就是這么簡單。可是,“不可能”的事忽然發生了。他們快走到她正前方的瞬間,春華似乎感應到了她的存在,眼睛像定向的雷達一樣,幾乎不用任何搜尋,一眼就看見了她。春華極其自然地朝她點了點頭,那神態仿佛在說,瞧見了吧?我對你可沒有任何隱瞞啊!小馬也點了點頭,盡管她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至于那個男人,因為發生了剛才自己被發現這個意外,小馬就沒有把他看得仔細,印象中是個挺帥氣的中年男子,身材幾乎可以用“偉岸”一詞來形容,他與春華走在一起,說“讓人羨慕”一點也不算夸大其詞。只是這個男人呢?好像是旅游觀光來的,目光游走于山石樹木、流水落花之處,手拉手的行走之間,卻透露出了他的漫不經心,以及他們的貌合神離。所以剛才,他一點也沒有發覺自己身邊的女人與小馬的相互點頭致意。
次日午后,小馬教完鋼琴,就把自己的所見所想一一說給春華聽,于是她們開始討論愛情。她們說,性和愛情不是一回事,但也不是兩回事,性不是愛情,但沒有性也就無所謂愛情。她們說,就像軀殼和靈魂,它們根本不是同一件物事,但它們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彰顯各自的存在,愛情和性也是如此。她們又說,那靈魂存在嗎?不對,軀殼是事實存在的,但軀殼用什么來佐證靈魂的存在呢?這么說,性是存在的,愛情也許只是種種說法,就像人對于靈魂的各種各樣的臆想一樣。她們又說,但也許,靈魂存在才是真的,軀殼只不過是一個虛假的影像,轉眼成空。說到這里,春華忽然發問:
“妹妹,你做過與愛情或性有關的夢嗎?每次都是同樣情景?我想一定是有的。”
小馬說:“有的呀!我經常夢里見到一個人,就在我的閨房里,就在我的身邊,就在我的床上,有時就在我的身體上。”
春華說:“這個人模模糊糊的,你看不清面容,甚至于不能確定是男是女,但你經常在夢里見到,你甚至能夠確定你見到的其實是同一個人,是也不是?”
小馬詫異得一時說不出話,嘴巴張成了一個“O”形,良久才說:“為什么?為什么你知道我的夢?”
春華說:“因為,我的夢和你一樣。現在我才明白,你在我的夢里,我也在你的夢里。你第一次來我家時,我就有這樣的預感,所以我說,我注定要跟你——而不是別人——分享我的隱私。”
她們已經喝完了好幾盞茶,嗑了大半包白瓜子,她們像往常一樣,要休息了。春華拉起小馬的手,二人進了臥室。床二米寬,二人躺上去還空了大半張。但小馬惴惴不安,一會兒,她起來站在床邊,看著春華。
“怎么了?妹妹。”
“你會覺得我是個壞女人嗎?”小馬問。
“你想說什么?”
“我跟你說的那個故事,我那個有兩個男友的女同學,后來招來了一個單身女友——我跟你是這么說的——其實,那個‘單身女友’就是我。”
春華不說話。
“那個男的始終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們只有過那么一次露水之歡,此前互相完全不了解,所以,我所幸并未因為那一次輕浮而受到更多的傷害。”
春華不說話。
“這話不說,我覺得辜負了你對我的好意。”
春華起身,拿了車鑰匙,開了門,一言不發地站在門口等她。
春華開車把小馬送到家門口,路上有十來分鐘,兩個人俱是一言不發。小馬伸手開車門時,春華攔了一下,說:
“你說的我早就想到了,但我沒有要你說出來。”末了又問一句,“你還會來我家教珠珠鋼琴的,對嗎?”
小馬默默地點了點頭。開了車門,她又轉頭對春華說:“我家種了一盆忘憂草,你知道忘憂草嗎?”
“忘憂草?好像沒見過。”
“你見過的,只是你不認得它。”小馬說,“下次方便時候,你來我家里,好不好?”
春華說:“好!”
春華想了想,以前她送珠珠到小馬家學琴,見過她陽臺上的幾種花草,印象里都是認得的,沒有小馬說的忘憂草啊。
時間又過了一個星期。周五晚,小馬教完了鋼琴,她緊緊挨著春華坐在沙發上,主動講起了自己的情感經歷:
“我一直沒有結婚,也不打算結婚了。至于說生兒育女嘛,看開了其實也沒什么,不說這東西多余,至少也是可有可無的吧。
“我只談過一場戀愛,這場戀愛談了兩年多,當然也同居了將近兩年。雖然我心里一直對他不滿意,但還是在猶猶豫豫、患得患失的狀態中進入了談婚論嫁階段。為什么對他不滿意呢?也說不清楚,總之是各方面的吧!他的各方面在我看來只能算勉強及格,而你也知道,每個年輕人——特別是女孩子,都難免追求完美。仔細想想,困擾著我的主要有兩個因素。他給我整體上的感覺就是,平庸,沒有哪怕任何一點讓我足以傾心的地方,比如工作上、人格上、思想智慧上、生活習慣以及審美情趣上,等等,總之沒有任何過人之處,甚至在我們相處過程中,我享受不到多少激情——他缺少激情導致我也沒有了激情。我就想,真正的婚姻還沒有開始呢,而一輩子是如此漫長,我竟然要與如此平庸的一個男人廝守終生,是不是太不把自己的人生幸福當回事了?另有一個原因可能也很重要,在我們戀愛過程中,我的生命中出現了另一個男人,是我大學時期的一個同學,不久前他也向我表白過。我沒有告訴我的男朋友,當時,也沒有打算接受這個同學,但我不免暗中比較,覺得后來者各方面都優勝很多。這讓我更為糾結。但畢竟在一起兩年,我怎么也不忍心傷害眼前這個男人。后來我終于說服自己,不要見異思遷了,不管怎么說,我們在一起基本上沒有發生過爭吵,他也從未傷害過我,他雖然平庸,但平庸的人自有他平庸的生活,平庸的生活不容易發生變故,從這個意義上說,‘平庸’又何嘗不是幸福的代名詞呢?我想,與其這樣思前想后心猿意馬,不如早作決定,斷了自己的退路。
“于是我問他,我們是不是該訂婚了?他說好啊!我說那要各自作些準備了。他問準備什么?我笑道,不用你準備什么,你告訴你父母就行,讓他們為你準備啊!他說,哦,我想想。我覺得他實在是傻頭傻腦的,可笑極了。我說還想呢,想什么呀!難道你還不愿意了?這時,突然——我都不知這事是如何發生的,突然,他冒出一句話來:‘小馬,我們還是分手吧!’
“當時我腦子里一片空白,好半天沒能反應過來——這個在我心里連及格都算不上的男人,這個我一直想跟他說分手的男人,竟然嫌棄我?竟然拋棄——我?
“你知道嗎?我的災難來了。一開始,我冷笑,我一直冷笑,他眼睛躲開了不看我。然后我問他我哪里配不上他?他淡淡地說沒有什么配不配的,只是不合適。我又責問他是不是有了別的女人,他承認了,還說什么緣分天定,不能強求。后來我罵他狼心狗肺,他轉身要離開,我又瘋狂地抱住他,不讓他走。最后,我竟然跪下求他。他卻越來越不耐煩,一再請我‘自重’。最后我威脅他說,如果他一意孤行,我就死給他看。我當時心里只有一個想法,只要他改變想法,我就要在訂婚當天,找來那個追求過我的大學同學,在訂婚酒宴上宣布我有新的男朋友,同時宣布解除跟他的婚約,用這種極端的方式羞辱他,至于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我完全不在乎。
“你說我是不是瘋了呀!但我再也沒有機會了。他拋下我,一個人走了。第二天,為了‘言而有信’,我吞下了50片安定。可奇怪的是,吞下藥片后,我不但沒死,竟然沒睡著——也可能是藥品過期所致——你說可笑不可笑!
“事情還沒完。在那種極度失落的情況下,我給追求我的男同學發了一條信息,直接說我喜歡他。你猜怎么樣?他竟然沒回我的信息,再發,還是沒回。幾天后在路上遇見他,他跟另一個女孩手拉手走在一起,對我視而不見。
“后來我還是想明白了,不管是這一個還是那一個,或者隨便哪一個,傷害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時間問題。就像我的這場戀愛,雖然我沒說分手,但我心里說了;雖然我沒有事實上的移情別戀,但我心里有了。差別僅在于說和沒說,一個表于外,一個形于內。我常常想,看似偶然的情感挫折,其實是必然的,就算是結婚生子之后,這種互相的背叛和傷害也勢必會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如影隨形,要么你認命、妥協、麻木,要么糾結、爆發、撕裂,乃至粉碎。因為什么?就像你說的,因為這是個濫情的時代。”
“還有一種選擇,”春華說,“那就是,各自都在心里淡化這種傷害,讓它不能成其為傷害,但我知道,你和我都無法做到如此灑脫。”
說到這里,小馬發現春華已經摟住了自己,而她也已經把頭靠在春華肩上。她們互相看了一眼,都不由自主地站起來,朝臥室走去……
她們很快就進入了狀態……可就在這時,春華忽然覺得有點不對,感覺到這個房間多了個人。進房間之時,春華本來已經想到要把房門反鎖,只怪一時忘情,這個念頭像風吹過一樣,一下就沒了蹤影。現在,她忽然意識到不對,已經晚了——她一扭頭,就看見女兒珠珠站在床前,無比詫異地張大嘴巴,看著眼前兩個交纏在一起的一絲不掛的女人——媽媽和老師……
春華沒有向女兒解釋什么。待她穿好衣服,女兒早已跑回自己的房間。她走到女兒身后,說了句:“對不起!”
這次,她開車直接把小馬送到了家里,因為前次她答應小馬,要看她家的忘憂草。看了忘憂草她一分鐘也沒有停留,她得馬上回家,因為她不放心珠珠。
珠珠看上去很安靜,低著頭寫作業。見她進門,珠珠說:“媽媽,我的作業寫完了。”
暑假期間,教育部門如期舉辦了一次大規模的鋼琴大合奏——三百六十多臺鋼琴同時演奏《東方紅》,擬申報吉尼斯紀錄。春華替珠珠報了名。舉辦部門要求參演者自帶鋼琴,可是,就在活動舉行前三天,春華發現家里的鋼琴壞了——所有的琴弦一起斷了。
春華知道,珠珠不可能把所有的琴弦都彈斷。
珠珠沒有參加那次大演奏。春華把新買才幾個月的鋼琴,折半價轉讓給了一個親戚。此后,珠珠再也沒有接觸鋼琴。
春華看到的忘憂草,其實就是黃花菜。她查閱了有關資料,忘憂草又名宜男草,古代少婦常以它佩戴胸前,祈求早生男兒。唐朝有個叫于鵠的詩人寫過這樣一首詩:
秦女窺人不解羞,攀花趁蝶出墻頭。
胸前空帶宜男草,嫁得蕭郎愛遠游。
——為鋼琴獨奏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