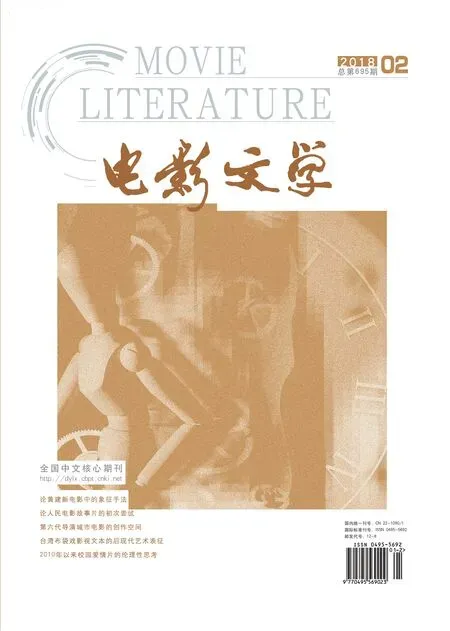電影產業價值鏈的環結功能及其在互聯網信息時代的重構與升級
李英睿
(澳門科技大學,澳門 999078;通化師范學院 美術學院,吉林 通化 134001)
電影產業價值鏈發源于美國好萊塢的制片廠制度(Studio System),是指由原創、制作、發行、映演四者環結構成的電影工業整體鏈條,它反映的是現代電影產業上下游各公司之間的一種共生經濟生態系統。大工業時代的電影生產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好萊塢電影產業巨頭們采取了以發行公司為核心垂直整合產業鏈上下游,將人才、資金、社會資源高度聚集,以流水線一樣的協同合作流程的高效率出產大資金投入、大明星團隊、高水平制作營銷、全球化發行映演的現代電影商業大片,并獲得了票房巨大成功和豐厚利潤回報。21世紀全球步入信息化嶄新時代,大型互聯網公司憑借互聯網信息平臺、傳播媒介創新等科技優勢將各類原本孤立的電影相關產業連接起來,甚至采取收購兼并、入股參投傳統電影制作公司等方式直接組建新的集團化“產業聯盟”新模式,力圖利用大數據分析、云計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全球移動互聯等新技術打破技術壁壘,以IP授權為核心將互聯網基因全面滲透到電影產業的原創、制作、宣發、映演等環節,并最終得以在電影產業價值鏈的拓展與延伸中實現價值增值的多元化、定制化、精準化、長尾化,這種趨向為誕生于大工業時代的電影產業在新世紀的重構與升級帶來新的機遇與挑戰。本文恰是針對此展開的研究分析。
一、 電影產業價值鏈的構成及其環結功能特點分析
(一)產業鏈的概念及其本質
在現代產業經濟學理論中,產業鏈是以產業深度合作為核心目標的區域性經濟合作載體,常被描述為一種具有鏈條式內在關聯關系的企業群生態構成形式,整個產業價值鏈鏈條式精確分工和價值交換系統的抽象建構形態則是一個產業組成單位關聯程度的體現。
(二)產業價值鏈的特點
經濟學家麥克·波特(Michael Porter)在其著作《競爭優勢》中首次提出用“價值鏈”(Value Chain)觀念來探討現代產業競爭,他認為產業價值鏈(Industrial Value Chain)就是構成產業鏈上下游各單位部門一系列有序的經濟活動及內部各環節價值不斷活動的總和。當價值鏈系統中的某個產業在確定了趨于合理的自身價值鏈關聯關系形態之后,就有助于該產業鏈中的各個組成企業之間的準確定位與策略擬定之間的有效整合,就能將人口、資源、信息、資金等資源高度聚集并效率最大化地分配至產業價值鏈各價值活動中,從而通過和其他競爭者相比較而不斷修正或重組其價值鏈,構建自身最為高效的經濟生態系統關聯方式,誘發產業價值鏈內部鏈條環節組成企業價值創造的產業鏈乘數增值效應,進而獲得市場競爭的相對優勢。
(三)電影產業價值鏈的構成及其特點
電影產業是指以作品版權的無形資產為核心的電影創意、制作、發行、放映以及電影衍生品開發,電影放映場所建設等一系列產業共生經濟生態系統的統稱。電影產業價值鏈則是電影產業各價值創造環節構成的整體環結鏈條的統稱,它反映的是電影產業上下游企業通過鏈條式關聯不斷高效集成整合電影創意人才、技術、資金等多項生產要素資源,以產業鏈上游的生產制作企業所創新相關電影產品或服務來不斷滿足產業鏈下游電影消費者日新月異的稀缺觀看需求,最終在實現電影產業共生經濟生態系統高文化附加值的經濟效益得以不斷增殖。電影產業是文化創意產業(版權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目前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支柱產業,所以在21世紀互聯網信息時代知識產權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研究電影產業價值鏈的特點及其升級對于推動中國電影業乃至整個文化產業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 大工業時代的好萊塢電影工業體系構成及演變
(一)好萊塢電影工業體系的形成
好萊塢的工業體系的形成源起于電影制片廠制度設立,為了更加高效地實現電影商品資金投入回報效益增殖,好萊塢幾大制片廠開始不斷垂直整合產業鏈上下游,在大工業時代以流水線一樣的制作流程高效率地出產大資金投入、大制作團隊、全球化發行的電影商品。在1919—1926年間的默片年代,好萊塢被稱為“造夢工廠”,無數的大明星大制作層出不窮。這時的好萊塢由六家主要的電影公司控制著,以派拉蒙為首的制片公司便相繼開始了對電影產業三個環節的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實現了由制片廠簽約作家創作劇本,制片人選擇拍攝劇本分發給簽約導演,選用制片廠自己的簽約演員,在自己的攝影棚內,使用自己的電影工人,在自己的院線完成電影放映。在有聲電影時代來臨之前,派拉蒙、米高梅、福克斯以及華納就已經完成了垂直整合,制片廠制度在20世紀30年代的好萊塢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而這個時代的電影產業中堅力量,就是好萊塢的各大電影制片廠。制片廠制度(Studio System)的盛行催生了好萊塢幾大制片公司的集團化,好萊塢幾大電影工廠巨頭通過利用自己制作、自己發行、自己放映的大工業時代電影生產模式壟斷了當時電影產業的生產、發行與放映管道。由于制片廠制度奉行著將電影視為工廠流水線上的產品,所以從題材選擇、場景布置、劇組人員一直到后期的剪輯等工作,統統由幾大電影公司控制在手。在這種曾經一度盛行的好萊塢電影工業模式下,電影在制片廠制作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都是獨立的、模式化的、工業化的,隨時可以更換與更新。與此同時,制片廠生產何種規模與類型的電影,全部由處于紐約華爾街的公司總部圍繞市場中的觀眾喜好進行分析與決策。電影完成后,首先發行到自己的電影院去放映,首輪利潤自己全部拿走,然后再賣給地方小劇院放映。盡管大工業時代的好萊塢電影產業奉行的制片廠中心制度,為電影產業發展帶來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和成熟的工作運作體系,但由于制片廠目標完全瞄準經濟效益,生產電影的目的只是期望電影作品在市場中獲得最大的利潤,所以導致導演的風格和演員的定位往往被迫消融于制片廠所需要的風格之中,越來越少有人愿意去尋找真正能夠打動人心的故事并進行個性化創作了,電影行業壟斷和產業鏈延伸度不夠的壞處開始顯現。
所以,現在的好萊塢電影產業中也開始涌現出很多獨立的電影制片人,他們已不再完全是大工業時代那幾大制片廠政策的被動執行者,而是在尊重電影作品自身藝術規律及傳播渠道多元化的基礎上,在新時代去探索電影產業價值鏈的變革。
(二)電影產業傳統工業體系在信息數字時代受到的沖擊
在21世紀信息時代新技術革命的引導下,移動互聯、萬物互聯后所帶來的巨大信息流,云計算和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展不僅改變了信息傳輸的速度成本,還顛覆了人們的許多傳統生活習慣與消費模式,引起了許多傳統產業的巨大變革。“互聯網+電影”時代,傳統的好萊塢電影產業價值鏈正受到信息數據系統化即時化、媒介傳播流量化虛擬化的巨大沖擊。新興的互聯網、金融公司不斷想要進入利潤豐厚的影視娛樂傳播行業,并希望借助互聯網徹底改變消費者最終消費電影的方式。產業鏈形成的動因在于產業鏈條內各組成單位整合后所實現的價值增值和創造,但任何產品只有通過最終消費才能實現,否則所有中間的生產就根本無法變現。如果未來電影產業價值鏈消費端在互聯網流媒體平臺的影響下,再沒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去電影院欣賞電影的話,那么好萊塢電影工業體系所建構起來的電影產業價值鏈的經濟效益增殖模式、產業共生經營運作模式都可能沒辦法持續下去。在21世紀這個新技術、新服務迅速迭代和取代的時代,來自消費市場的“倒逼”是一個產業鏈發展對障礙進行疏通的一種新形式,只有正視消費市場的需求倒逼并主動創新,以前瞻性的技術視野及更好的內容和服務滿足消費者的現實需求及潛在需求,才不會有被市場淘汰的風險。由此可以預想未來,互聯網時代對影視產業的影響將不僅局限于目前的終端票務在線支付領域,更將可能涉及內容生產、影片制作、版權分發、衍生品增值服務以及其他跨界資源整合等,并最終改造整個影視產業鏈與行業格局。
三、 互聯網信息時代對傳統電影產業價值鏈環節的影響與功能的重構
(一)互聯網重塑了電影產業鏈中的原創、制作流程及環節
隨著新世紀以互聯網信息技術平臺為載體的大數據分析、云端計算、人工智能等新一輪技術革命風暴的來臨,誕生于大工業時代的以幾大影視公司商業運作為主導,制片廠中心制、演員商業化明星制為核心的傳統電影工業制作模式正相應發生著變化。“互聯網+電影”通過互聯網技術對電影消費終端用戶采集數據并進行整理分析,可以將不同類型的觀影者有效信息和消費需求變化及時準確地反饋到產業上游,這種“以精準的受眾為中心”為互聯網時代影視項目的劇本題材選擇、主創陣容和演員的構成、電影宣發營銷受眾鎖定和策略制定、前后期制作流程優化、票房規模預估及風險防控等提供了必要的決策參考,并已在美國Netflix公司所出品的《紙牌屋》等一系列原創自制網劇取得極大成功的案例中得到印證。同時,在制作環節方面,“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不斷發展正在促使著電影制造向智能化、自動化進行逐漸轉型。2017年8月,美國恐怖片《摩根》發布了一段由IBM的人工智能機器系統“Watson(華生)”為其制作的1分25秒的電影預告片,“華生”首先分析了上百部恐怖和驚悚電影,了解了哪些東西最讓觀眾害怕,然后他從《摩根》中智能篩選出了最可怕的10個片段組合制作成一段預告片。在Watson的幫助下,原本應由一名工作人員花費10天到1個月的時間來完成制作的預告片縮減到了由人工智能輔助人、合作剪輯成片的短短的24小時,極大地提高了預告片的制作效率。相信在不遠的將來,由增材制造/3D打印、增強現實(AR)/虛擬現實(VR)、人工智能(AI)/人形機器人(HMI)等新技術的快速發展所引導的新技術革命風暴,勢必將使電影制作更加趨向“高智能、高效率、低成本、低風險”,并導致傳統電影工業產業鏈制作環節的升級改造。
(二)重塑電影產業鏈的宣發、映演環節
互聯網時代新媒體技術的應用使電影產業鏈的宣發、映演環節中的信息發布與傳播更加具有迅捷、實時、互動的特點,“互聯網+電影”顛覆了傳統電影產業鏈的宣發、映演環節的營銷模式,使其營銷渠道和中間環節被壓縮,逐漸趨向于傳統電影宣發營銷渠道,與以“移動性、實時性、互動性、私人化、平民化、自主化”等特點為主的社交軟件類媒體、自媒體的多元化傳播渠道并存的特征,把電影營銷推進一個多元、廣輻、互動、精準化的新的時代。同時,借助于互聯網的精準對接與優化配置功能,通過對互聯網用戶數據整理分析并將有效信息反饋到電影發行方及映演影院,產業價值鏈上游的投資方可以即時反饋提供受眾對不同類型影片的觀影喜好變化趨勢、科學預估防范電影票房黑洞、為影院增減不同影片場次安排及合理排片提供科學依據,從而提高整個產業鏈的經濟收益,不斷降低投資方投資的風險,引起電影投資市場的火熱。
(三)互聯網信息時代電影產業價值鏈自身功能的升級重構
1.互聯網信息時代電影產業價值鏈呈現“跨界一體化”特征。2015年之后以三大互聯網巨頭(BAT)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紛紛主動進軍電影界,謀求將其線上信息平臺的壟斷優勢延伸至線下實體,通過跨界經營實現自有IP的泛娛樂轉化。當然,虛擬網絡與傳統電影的結合、互聯網技術公司與傳統電影制作企業合作本身就是一種跨界,傳統電影制作企業面臨以怎樣的形式才能在保有自身優勢的前提下,借助互聯網連接線上線下建立統一的大數據平臺實現數據共享或信息關聯互通,從而依托“互聯網+電影”以達到進一步對影片進行準確預判,吸引優質資本、防范行業風險、降低運營成本、促進效率不斷提升、更好地實現電影產品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互聯網+”與傳統影視產業的融合與碰撞,有助于電影產業在新時代實現橫向跨界拓展、縱向整合重塑。當然這種融合與碰撞是機遇也是挑戰,它的某些不規范之處也不可避免地會給很多習慣于傳統電影產業價值鏈的電影制作、宣發及映演公司帶來陣痛。但同時這也是在互聯網信息時代推動下電影產業業界啟動市場淘汰機制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并為我國電影產業規模化、集團化、國際化發展奠定了基礎。在信息時代新技術的推動下,目前我國許多電影產業中的傳統企業也已開始不斷借助新技術打破傳統產業分工壁壘,改變產業原有內部上下游各自分工明確的獨立存在狀態,并不斷通過業務拓展和企業兼并收購優化、重組產業鏈中原有的優質資源,從單純在某一領域內從事生產或銷售的活動者逐漸延伸演變為產業鏈整體資源平臺的集成者和鏈條關聯的組織者,邁向“一體化”大型產業集團發展之路。
2.電影產業價值鏈呈現“全產業鏈”延伸特征。按照現代產業價值鏈理論,其價值增值效應的本質是實現其內部構成單位之間“1+1>2”所產生的產業鏈疊加增幅效應,即產業鏈整體生產效率因合理協作分工會大于其內部企業之生產效率總和,而其交易成本因集群網絡效應會小于產業鏈內部企業間的交易成本總和。所以,電影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跨界融合成為其延伸產業鏈、增加收益的重要形式。目前我國電影產業融合已涉及廣泛,主要包括IP授權與出版業融合后的電影主題系列圖書音像軟體、與電玩業融合后的電影主題游戲、與餐飲業融合后的電影主題餐廳、與旅游業融合后的電影主題游樂園、與制造業融合后開發的不同電影主題衍生品等,但產業鏈的合作深度還顯不足。在“互聯網+”語境下,電影產業價值鏈利用互聯網信息平臺技術有效地通過整合IP,將傳統電影產業和各行各業打造成不斷拓展延伸且相互融合的電影“全產業價值鏈”。“互聯網+電影”的模式快速有效地促進了電影產業與其他傳統產業的邊界滲透融合,將電影產業知名IP消費的“長尾效應”拓展延續到其他產業中,這種“全產業鏈”延伸不是對傳統電影產業的顛覆,而是借助移動互聯網技術服務催生出更多的商業增殖模式、更智能的交互式技術服務、更精準的用戶個性化體驗,從而在線上線下的全產業領域創造一種新的共生經濟生態圈,讓觀眾的光影記憶轉化為更為真實多元和豐富的用戶體驗,在促進傳統產業發展的同時實現了二者的雙贏。
四、結 語
21世紀是互聯網信息時代,誕生于大工業時代的好萊塢傳統電影產業價值鏈在創新科技和創新思維的推動下,逐漸發生著嶄新的升級與重構。但從全球電影價值鏈的升級模式來看,中國電影產業剛剛歷經完市場化“院線制”改革,目前仍處于粗放式經營和產業工業化初級階段,存在著電影產業鏈各核心環節條塊分割、產業上下游良性循環不夠、不良競爭嚴重、價值鏈一體化拓展乏力與其他相關行業深度合作不足等現象。在互聯網信息時代,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革命浪潮正在催促我國電影產業價值鏈的升級和戰略重組,如何使電影產業鏈集群企業間的關聯經濟生態關系趨向于良性演變創造價值增值,是當代中國電影產業持續有序發展、早日完成由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轉變的重要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