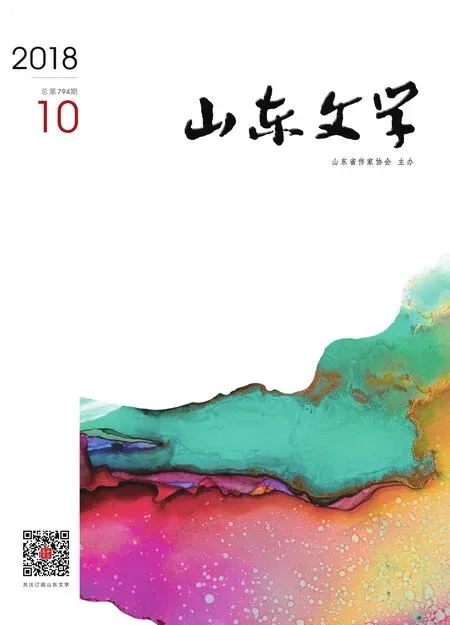新時期改革文學中的強人文化現象
房 默
改革文學是新時期以來最有特色、與社會共鳴最強的文學思潮之一,尤其是在上世紀80年代,曾經引發(fā)廣泛的社會反響,有的文學作品甚至成為了許多改革者必讀的“教科書”。但遺憾的是,當時關注度如此之高的這一文學現象,卻如一首歌所唱的那樣:“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并沒有結束,但改革文學卻逐漸消失在了文學史當中,這種現象值得我們探討。
改革文學是伴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政策的實施而迅速發(fā)展起來的。它形式多樣,囊括了從城市到鄉(xiāng)村的各個領域,但其中取得社會影響最大的一批作品,卻基本都是具有的明顯強人色彩,尤其是展現體制內變革的改革文學,幾乎都有一個強人的主人公,用自己獨特的人格魅力與強力手段,主導著改革事業(yè),將一個瀕臨崩潰的爛攤子改變?yōu)橐粋€最有“希望的田野”。最有代表性的是蔣子龍創(chuàng)造的“開拓者家族”,如《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樸、《開拓者》中的車篷寬、《赤橙黃綠青藍紫》中解凈、《燕趙悲歌》中的武耕新、《人事廠長》中的胡高盛五、《鍋碗瓢盆交響曲》中的牛宏。另外,張賢亮的《男人的風格》中的陳抱貼,李國文的《花園街5號》中的劉釗也都屬于這種類型的人物。
改革文學中的強人文化色彩,既是改革文學最大的亮點,也是改革文學最明顯的短板,但這并不完全是由創(chuàng)作者造成,更與改革文學本身及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息息相關。
首先,改革開放這個行為本身需要強人,至少需要有強人來推動。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們不僅對于舊有的國家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修改與完善,還在新形勢下創(chuàng)建、制定了大量新的法律與規(guī)范。這些改變和創(chuàng)新,不僅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反過來為新時代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制度本身缺乏自我變革的“動力”,在改革過程中依然存在應該建立的制度沒有建立,或者建立的制度背離了初衷,以及建立的制度無法落實等問題。尤其是當制度自身染上了利益色彩之后更是如此, 一些利益集團綁架個別部門,深度參與并主導制度設計,將自身利益合法化、制度化。這些問題一方面會阻礙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另一方面也會引起公眾對制度本身的質疑和反抗,人是一種趨利避害的生物,當公眾發(fā)現自己并不能從遵守制度來獲得改革的紅利,那么必然會引起整個社會重大的道德風險。因此,當制度陷于利益的漩渦無法自拔的時候,個人的價值就會凸現出來,一些強力改革者依靠他們自身的能力和威望,強行推動制度的落實和變革,就會受到社會廣泛層面的關注和支持,甚至讓人聯想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清官”“英雄”情結。事實上,這種現象不是中國獨有的存在,也是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即便是美國歷史上幾次重大的變革,也都是由關鍵的改革強人來推動的,例如廢奴運動、南北戰(zhàn)爭時期的林肯,大蕭條、二戰(zhàn)期間的羅斯福,上世紀80年代的里根,這些被公認的美國歷史上最優(yōu)秀的總統,都因為依靠個人政治智慧和手腕推動了美國社會的大變革而被人們所津津樂道,包括如今爭議不斷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是靠著強人和改革者的姿態(tài)入主了白宮。因此,就像塞萬提斯筆下沖向風車的堂·吉訶德一樣,當體制自身陷入泥潭的時候,改革強人的出場是有其現實合理性的。喬光樸等人物形象,在80年代之所以能夠由一個文學想象的人物成為社會上爭相盼望出現的英雄,顯然是因為當時的中國有著這樣非常豐厚的現實的、文化的與心理的土壤。
其次,文學作品的張力需要強人,強人是文學中最有藝術魅力的要素之一。文學是一種以塑造人物為主的藝術形式,這決定了文學的張力主要由人物和塑造人物的情節(jié)構成,文學作品要想有吸引力,人物性格就不能過分平庸,人物的身份可以平凡,人物的生活可以簡單,人物的命運可以庸常,但人物的性格必須有特點。改革文學盡管是與現實最為貼近的一種文學,也是能為社會改革鼓與呼最為直接的一種文學,但既然是文學,其人物的塑造也必然要遵循著性格化的原則,更何況無論是從公眾的現實認知還是從歷史規(guī)律的角度看,改革都是一個充滿了尖銳矛盾和斗爭的活動,很難想象改革可以通過大家坐下來,平心靜氣的談判來解決問題,因此改革與反改革往往呈現出尖銳的二元對立,甚至是一種你死我活的狀態(tài),這也符合讀者的一種心理預期和歷史常態(tài)。從實際的作品來看,改革文學中的改革者基本上都是處于一種四面受敵的狀態(tài),改革的推動必須使用非常規(guī)的強力手段才能進行,因此,改革文學中的改革者為了能夠推動改革的進行,往往具有明顯的英雄色彩,普遍都是性格堅定、能力超群、眼光深遠、極富個人魅力,如同盜火的普羅米修斯,補天的女媧,他們或成功或失敗,都能展現出一種具有傳奇色彩的藝術感染力。這一點我們依然可以與美國進行對比,客觀地說,美國的社會制度是比較完善和先進的,尤其注重程序,是一個程序正義的國家,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文學藝術作品同樣充斥著大量反體制英雄,這里確實存在一個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悖論,如果社會問題都能依靠體制按部就班來解決,那就沒有人物的發(fā)揮空間了,人物的平庸必然會影響文學作品的整體表現力,因此要想實現作品藝術張力的充分體現,強化作品中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則往往需要將個人的力量最大化,將矛盾沖突最大化,美國文學尤其是好萊塢電影中常見的一幕就是,法律永遠滯后,正義需要超級英雄來維護。因此,美國文學藝術作品,經常使用的范式就是強調體制的不完美性,強調體制對個人自由永恒的壓抑,這一方面體現了美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對政府權力有沒有被關進籠子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則體現了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本身的規(guī)律,讀者喜歡這樣的設定,強者拯救天下。經歷過80年代的讀者,或許對當時種種的現代派小說或者新潮小說已經了無印象,但對那時出現的許多改革小說依然記憶猶新,與改革小說比較好地在平凡的時代里,運用改革制造出了令人神往的社會沖突、思想沖突與心理沖突,并在這種激烈的沖突中塑造出了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的英雄性格是有極大關系的。
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從現實的真實需要還是文學的藝術要求上看,改革文學中的強人形象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但是為什么這種既符合中國改革發(fā)展的時代要求,也符合藝術內在規(guī)律且有著廣泛的讀者心理期待的文學現象,沒有能夠持續(xù)發(fā)展下去,成為“來去匆匆”的文學現象呢?我以為,其主要原因仍在于強人文化,而且這種強人文化仍然與現實與文學有關。
首先,改革文學的落潮與興起一樣,都與社會現實與改革發(fā)展的影響有著密切的關系。改革本身是一個艱巨的過程,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思想影響深遠、人口眾多、國情復雜的大國進行改革更是如此,很多時候,都是在試錯的過程中前行,隨著改革的進行,牽連到的各種利益就更是讓復雜程度以幾何倍數遞增,原來改革文學中那種單純的二元對立的模式無法承載這種復雜性了。文學創(chuàng)作中單純的改革強人也隨著現實中的原型逐漸失去了光環(huán)而變得缺乏信服力。對改革強人的企盼和認可,反映了相當一部分作者和讀者對民主政治現狀的不滿。民眾更習慣于接受改革強人來解決改革問題,控制改革方向,分享改革紅利。從一定的歷史階段看,改革強人的存在有利于民眾,能較為有效的解決一些發(fā)展的現實問題,但其弊端就在于其本身可能成為新的腐敗滋生的溫床和改革的壁壘。其一,改革強人往往也是政治強人,大權在握,大包大攬,往往形成一言堂式的獨裁性,隨著時間推移,改革成果容易被體制僵化,隨之可能滋生新一輪的社會和經濟問題,這一點,蔣子龍的小說《燕趙悲歌》中武耕新的原型天津大邱莊的禹作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禹作敏是天津市靜海縣大邱莊原黨支部書記,也是改革開放初期著名的改革強人,他一手把一個遠近聞名的窮村改造成盛極一時的中國“首富村”。但隨著個人的成功,外界的贊譽,權力的不受控制而逐漸膨脹腐化,成為土皇帝一樣的人物,后因犯窩藏罪妨害公務罪行賄罪等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99年10月,結束了自己站在時代潮頭的榮光。可以說,這種現實情況對于改革文學本身也是一種沉重的打擊。其二,改革強人往往靠自身的強人特質完成對重大困難和危機的應對,力挽狂瀾,因此,國家和制度不過是他們實現自己的改革理想的工具而已,這種改革往往不具備持續(xù)性和傳遞性,例如曾經名重一時的江蘇官員仇和,一方面依靠鐵腕、強權的執(zhí)政風格帶來了高效率,另一方面其專斷、任性式的為官之道也被人貼上了“酷吏”“血”的標簽并最終落馬。其三,再強悍的人,也需要周圍人的幫襯,才能成為真正的強人,因此改革文學中經常出現“小幫派”“小團體”和背后的“大領導”,他們圍繞在改革強人身邊,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對抗永遠存在的“保守”“消極”的改革敵人,而且,改革文學中還展現出了明顯的長官意志論,改革人物再強,最終決定其生死成敗的往往是上級領導是站臺還是拆臺,如《花園街五號》中的韓潮、《改革者》中的陳春柱、《新星》中的鄭達理。改革本身的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也使得大量改革文學的作者心有忌憚,不敢輕易觸碰。
其次,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文化生態(tài)的變化,以往那種宏大題材的文學作品逐漸失寵,以世俗化、底層化、個人化為代表的新文學潮流開始成為文學的主流,在這種文學環(huán)境下,展示普通人的命運、人生、悲歡離合、愛恨情仇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要方式,以往那種國家民族層面的英雄敘事逐漸消失了。文學也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百年以來捆綁在自己身上的枷鎖,實現了文學與意識形態(tài)的疏離,但這種疏離的代價則是文學逐漸退出了社會輿論的主舞臺,淪落為一種無人關注的邊緣文化,而這種變化,也恰恰是隨著改革文學的消退而開始的。此外,這種轉變,還與社會經濟文化發(fā)展,個人意識覺醒,大眾文化流行等社會經濟原因有關,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金錢也日益成為左右文學發(fā)展的新指揮棒,很多作家轉而開始創(chuàng)作更具經濟價值的文學作品,現實嚴肅題材作品的生存處境可以說是日益艱難,其實改革文學本來還有一條很有前景的發(fā)展道路,就是與影視藝術相結合,改革文學的情節(jié)相對簡單,強人形象和對立性故事結構倒是很符合影視藝術的表現方式,但相關部門對影視作品的嚴格監(jiān)管,也使得這類作品舉步維艱。
當下中國的現實是,沒有改革強人改革幾乎不可能實現,但強人模式也存在明顯的弊端,也使得改革帶有強烈的人治色彩。其中所存在的問題甚至直接影響到改革文學的創(chuàng)作。所以說,以強人模式進行創(chuàng)作的改革文學,雖然既有現實基礎,也有藝術基礎,但卻是一種戴著鐐銬舞蹈的作品,文學不是政治的傳聲筒,但改革文學與現實的太過于接近,讀者總會試圖找出作品中的現實原型,而這種尋找往往帶有強烈的現實和文化上的風險,改革文學的時效性遠遠大于流傳性。其實這種困境不僅影響著改革文學,也影響到近似的其他題材的作品,如反腐文學、官場文學。
誠然,如今更多的作品表現的是普通人的命運,他們在歷史大潮中的沉浮與無奈,這同樣能在某種層面上展現出改革對時代、對個體的影響,也能讓我們反思改革的進程和所付出的犧牲,從人文關懷角度看是值得肯定的。但文學需要多樣性,文學家也許需要多樣化的立場。直面改革本身,展現改革者形象的文學作品并不應該在我們這個時代缺席,因為這不僅能夠體現一個文學家、一個知識分子直面現實的勇氣,也能提升文學的社會價值和影響。
對于改革文學的前景,我個人認為,趨利避害這是人之常情,但對于真正的文學家,逆流行險方能體現英雄本色,不能因為改革文學會深入到改革的深水區(qū)就畏懼,甚至干脆繞過這一話題,中國的改革仍然在路上,也需要文學家以社會良知和人文關懷的眼光來關注改革,并為改革的順利進行發(fā)揮自己的一份力量。改革文學中的強人文化本身就是合理的,但改革文學應該注意的,不能因為存在即合理,不能因為迎合讀者就放棄了思考。我們首先必須明確的一點是,改革強人們之所以受到公眾的關注與支持,正是由于他們的改革行為本身順應了公眾對制度合理性與公平性的呼聲,在當今的中國,公眾之所以出現這種對英雄的歡呼,是希望這些英雄能帶領大家重新走上良政、善政的道路,讓制度充分發(fā)揮自己的作用。因此文學作品不應該單純地展示一種強人文化,而應當體現出公眾對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制,社會主義法治的極度渴望。做到這一點,或許以強人為核心的改革文學會重新呈現出曾經有過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