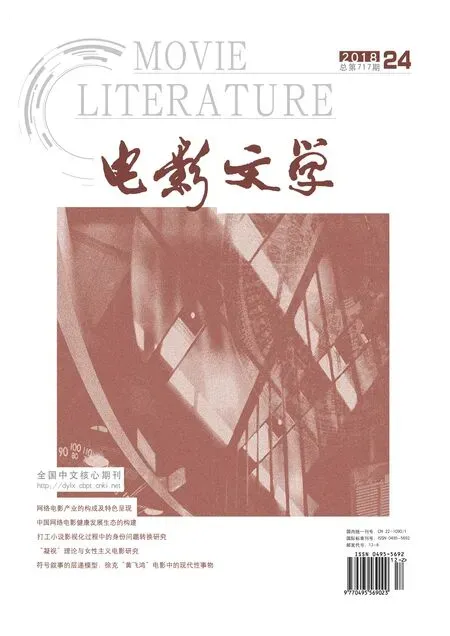《一出好戲》:世界盡頭的妄想
劉 勵
(武漢鐵路職業技術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
《一出好戲》上映時間是2018年8月,這是一個好戲連連的時節。前有25億元黑馬《西虹市首富》提前收割了大量票房,同期有《狄仁杰四大天王》和《愛情公寓》兩部國產大IP,還有好萊塢巨制《巨齒鯊》前后夾擊,可就在這般猛烈的攻擊下,導演處女作品、主打劇情和喜劇的小成本電影,最后竟然拼出了13億元的好成績,足以說明《一出好戲》本身的觀影價值。關于“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無論文學還是影視作品,都經常被討論。我們所有人都有對烏托邦的期望,但現實又是反烏托邦的失望,而當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相遇的時候,其話題性就自然暴露出來了。
一、烏托邦與反烏托邦
(一)烏托邦的美好愿景
烏托邦的原意是由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提出來的,而沿著烏托邦研究,最重大的發展自然是空想社會主義的產生。空想社會主義是英國托馬斯·莫爾教授的學說,又可以叫烏托邦社會主義。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兩本關于烏托邦的著作:《理想國》(柏拉圖)和《烏托邦》(托馬斯·莫爾)。理想國的提出正值古希臘雅典的鼎盛時期,但是柏拉圖偏偏在這個時候提出了烏托邦這種社會猜想。原因就是當時的柏拉圖很有政治想法,但雅典的政治現實非常殘酷,柏拉圖三次西西里之行都沒有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最終只能含恨寫下《理想國》。而托馬斯·莫爾本身是閱歷豐富的學院派,作為文藝復興的偉大思想家,托馬斯·莫爾同樣對16世紀的英國政治感到失望,在社會現實面前,他超前地認為柏拉圖的理想國應該到來,只有理想國才能拯救世界。
烏托邦最核心的內容就是美好與虛妄,有的人可能會從莫爾的《烏托邦》里看到絕對平等,但絕對平等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內容,并不是所有的烏托邦都是絕對平等的。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公民是有階層區別的,統治階層甚至可以為了國家安全穩定欺騙、對付敵人和公民。因為在柏拉圖看來,哲學家在世界上應該是統治者,而不是政治家。烏托邦,實際上就是人類美好愿望的寄托。
在《一出好戲》中,王寶強飾演的小王通過暴力建立了第一次“政權”,小王要求人人平等,“人人平等”是影片出現的第一次烏托邦。其后,由于和偉飾演的張總帶領黃渤飾演的馬進、張藝興飾演的小興兄弟建立的第二次“政權”,有了“交易平等”,交易的“絕對平等”是影片出現的第二次烏托邦。其三,由主角馬進、小興兄弟利用宗教思想和科技魅力建立的第三次“政權”,有了“信仰平等”,這便是影片出現的第三次烏托邦。三次烏托邦的出現都帶來了一次統治的繁榮。第一次出現烏托邦,大家適應了孤島,開始學習生存。第二次出現烏托邦,知識和權謀帶來了社會的穩定和平。第三次出現烏托邦,信仰給大家帶來了希望,有了共同目標,開始齊心協力解決各種難題。
黃渤的“孤島求生記”(《一出好戲》)實際上揭露了一個真相,烏托邦的出現可以帶來短暫的繁榮,它的出現一定不是無緣無故的。正如柏拉圖和莫爾的烏托邦一樣,影片中每一次烏托邦的出現都是因為孤島上出現了不可協調的混亂,這種混亂下的“社會成員”渴望一種全新的和諧,所以一旦烏托邦出現,大家愿意相信眼前的美好,愿意跟著領頭人走,這不僅是小王、張總、馬進三個“統治者”的能力表現,也是所有人愿意陪著相信這些美夢最終會成真的群體力量。
(二)反烏托邦的失望現實
反烏托邦,是指烏托邦的對立面,既然烏托邦的核心是美好與虛妄,那反烏托邦的核心就是丑惡與現實。作為一種文學手法,反烏托邦實際上更多被用于揭露社會的不良真相。比如在《動物世界》里的動物反人類革命,《1984》里的極權主義現實,《這完美的一天》里的最終真相。這些都是在刻畫社會和平安定下的丑惡現實與可怕人性。
我們說《一出好戲》里面的三次“政權”是三個烏托邦,是因為這三次統治不僅是三次美好愿景,而且最后都失敗了。第一次烏托邦,“人人平等”,大家齊心協力共渡難關,沒有問題。但是,小王光拿“溜猴”的經驗來管理團隊,忽略了人性與人格的作用,導致團隊里出現了“害群之馬”腐蝕了小王的“人人平等”。在這一刻,第一次烏托邦就出現了裂痕。而張總的一番人格呼吁,讓團隊的烏托邦徹底破碎。第一次烏托邦粉碎其實就是第一次反烏托邦誕生,它告訴我們,人性是理想國的黑洞,會吞滅一切美好與和諧。
第二次烏托邦很快就繁榮起來,其實大家都知道張總并沒有權利霸占大船,只要大家一起反抗,就能要求平均分配,但由于對小王的失望,大部分人選擇了相信第二次烏托邦,甚至忽略了船上物品的不可再生性,愿意用勞動來維護交易規則下的和平,反過來壓制小王和馬進。但“交易平等”這個烏托邦的核心在于“交易價值”。張總一開始說船上只有兩副牌,所以“貨幣”的價值是等價的,但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張總這個規則制定人可以提前私藏紙牌,導致“貨幣”貶值,不斷收割其他人的勞動成果。所以,“交易平等”從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第二次烏托邦在根上就埋下了反烏托邦的種子,后來由于馬進的介入、挑撥,導致第二次烏托邦流產。
第三次烏托邦的出現實際上是最穩定的也是最有發展力的,因為馬進很巧妙地給所有人植入了“希望”這個信仰,而小興的科技能力則為馬進的信仰綁上了一對翅膀,讓所有人都相信,自己就是“新哥倫布”。世界已經到了末日,目前的團隊就是新世界的開創者,所以,要和諧,就要共渡難關。本來這第三次烏托邦如無意外可以一直延續下去,但這次烏托邦的基礎就是“世界末日”。如果世界不是末日,孤島不是孤島,則烏托邦就只能是虛妄。所以,當馬進他們發現了被誤認為野獸的郵輪時,第三次烏托邦就已經宣告失敗了。雖然他們用計謀掩蓋了事實,但終究會被人發現,所以,第三次反烏托邦就是殘酷的現實。
二、世界盡頭的妄想
(一)世界盡頭的隱喻
關于末日言論,最甚囂塵上的當屬2012年的瑪雅末日預言,現在看來當屬謠言了。但是關于世界盡頭的猜想,人類社會從來也沒有間斷過。《圣經·創世記》中記載到,上帝為了清洗世界的罪惡,命諾亞制諾亞方舟,保留人世間最正義的種子,然后降下洪水,覆蓋大地,萬物重生。從電影中一開始的情節來看,“隕石”實際就是“上帝力量”,其落入海洋翻起巨浪,傾覆世界,而眾人正是有賴于一艘小小的方舟,才得以存活。可惜的是,眾人不是上帝口中的義人(來自《圣經》,正義之士),每個人都心懷鬼胎。張總擔心自己的公司,馬進擔心自己的彩票,小王不想老是被欺負……
《一出好戲》中的世界盡頭實際上并不等同于其他影視作品上的世界末日,誠如后來馬進的“洗腦式”演講中說的,青藏高原四五千米高的海拔不可能會被淹沒,孤島外面一定有新世界。這樣說來,其實一片望不見天際的海洋就是一塊扯不開的幕布,所有人被困在臺前,只能等待別人的援手,否則就要一直在臺上表演下去。好萊塢派拉蒙影業公司在1998年出品了一部巨作《楚門的世界》,楚門從出生就被選在一個巨大的攝影棚里長大,所有身邊的一切都是導演預設的情景,所有親人朋友都是演員。由于楚門根本不知道有外面的世界,所以可以全副身心地做自己,而外面世界的所有人也都在時刻觀看楚門的生活直播。而當楚門知道了自己原來是在一個虛構的世界里的時候,拼了命也要逃離出去,這就是人類的勇敢與力量。而《一出好戲》與《楚門》相類似的是,《好戲》中的幸存者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還存在,所以他們就當自己是世界盡頭的幸存者來活,也就是這樣,人性最根本、最原始的東西才能暴露出來。也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小人物才有了自己的舞臺。
所以,《一出好戲》的世界盡頭,不僅是世界毀滅,而且是隔絕舞臺與現實的一重幕布,幸存者在孤島這個舞臺上,盡情演繹自己,演繹人性,演繹人心,這才是一出好戲。
(二)人類力量:技術的發展
看完電影,最讓人心潮澎湃的并不是馬進和珊珊的愛情,也不是小王和張總兩派勢力的斗爭,或者馬進登上高臺、振臂一呼的洗腦演講,而是一盞燈。馬進在演講之前,打開了船上的一盞探照燈,燈光打下來的瞬間,所有人被震撼到了。后來馬進關了燈,問所有人想不想離開黑暗、見到光明,大家都喊想的時候,燈再次亮起。這一瞬間,好似《圣經》記載:“上帝說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馬進用一盞燈拔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從此,他轉變成了所有人的精神導師。但是,如果僅靠精神統治,很容易就會出現新的反烏托邦。借鑒了前兩任“統治者”的經驗,馬進牢牢抓住了一個新的制高點——技術。
小興擅長技術,但是馬進擅長精神統治,就好比劉邦治國,馬進捕獲了小興的跟隨,自然就捕獲了先進的技術優勢。在眾人還陷入鉆木取火、竭澤而漁的困境中的時候,馬進兄弟已經掌握了發電與存儲,并借助之前用魚換取的眾人的手機(島上無信號、無電,大家覺得沒用),利用手機里關于家人的視頻,成功捕獲了眾人的心。
在整個故事結構中,小王的第一次統治權力來源于武力和眾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張總的第二次統治權力得益于破船上的稀缺物品及張總的經濟管理頭腦、而馬進的第三次統治權力,主要得益于技術的加持。如果沒有小興的現代技術,馬進根本無法說服眾人跟隨他的腳步,因為在張總與馬進之間,張總更具管理才能,能輕易打破馬進的“希望信仰”。但是,張總也沒辦法對抗科技進步的力量,以至于后來還被小興用視頻威脅寫下財產轉讓承諾書。所以,三次烏托邦演變,實際是人類力量的升級與轉變。人類從只會用蠻力、武力解決問題的時代,進步到會用規則和經濟體系來管理世界,再到會用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科技來改變世界。人類的力量——技術的進步就是在不斷開啟新的人類紀元。
三、結 語
說到底,《一出好戲》還只是黃渤導演的處女作。劇本是好劇本,導演也是好導演,但是劇本想表達的東西太多,從烏托邦到反烏托邦,從世界盡頭到新紀元,從人性丑陋到為愛犧牲,從市井小民到老板智慧,從孤島求生到旅游開發,從鉆木取火到捕魚為生,一系列的情景情節設置,都非常合理,唯一不合理的就是時間太短了。一個人孤島求生已經可以拍一部電影,一群人的孤島求生就可以拍一部六季的美劇了,但導演試圖將一部美劇塞進130多分鐘的電影里,難免會有情節存在邏輯漏洞,也難免會有些凌亂。但當我們看到人性在善與惡之間徘徊的時候,我們難免會想到自己。假如世界有盡頭,自己是幸存者,又當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