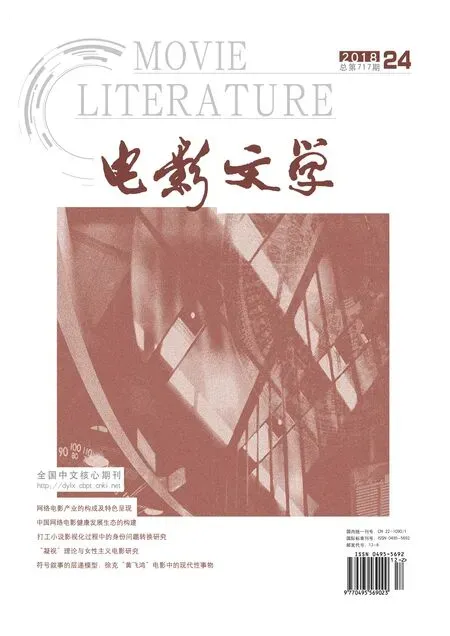《復仇者聯盟》與超級英雄電影語言系統
林立娜
(吉林師范大學,吉林 四平 136000)
最先將電影視為一種跟文學、舞臺戲劇全然不同的藝術類型,并認為這一藝術擁有屬于自己的語言系統的學者,是匈牙利的電影理論家貝拉·巴拉茲。其后法國電影理論家克里斯蒂安·麥茨又以第一和第二符號學來拓展電影語言系統理論,使人們普遍認同電影具有一套獨特的表達規則。漫威漫畫公司出品的一系列超級英雄電影,尤其是有集大成意義的《復仇者聯盟》系列,不僅是當代影像技術發展的翹楚,也是類型片進行影像表達的代表者。在漫威崛起的同時,同樣擁有深入人心的超級英雄角色的DC漫畫公司等巨頭,也亦步亦趨地開始了在超級英雄電影領域上的擴張,而漫威對它的引領作用,《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對于超英電影語言系統的定型,是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的。
一、超級英雄電影的視覺符號與表意
所指和能指之間建立對應關系,語言系統也就應運而生。在電影中,由于畫面和蒙太奇技巧的存在,所指和能指之間不僅表達溝壑被縮小,且往往新的對應關系被建構起來。尤其是對于類型電影而言,該類型電影的成熟過程,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視覺符號在能指上被固定、在所指上被深化,觀眾對視覺符號的理解越來越快捷順利的過程。如觀眾在目睹了鋼鐵俠托尼·斯塔克貼合肌膚的高科技戰衣,以及瞬間穿脫戰衣的神奇過程時,就能將這一視覺符號與力量、責任感的深層含義聯系起來。而如果說托尼的盔甲依然以一種堅硬質感提示著觀眾他的凡人身份,那么在《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元》(Avengers
:Age
of
Ultron
,2015)中登場的,被奧創以振金制造出身體的“人造人”幻視,他則身穿更為服帖柔軟的緊身衣而同樣能刀槍不入,以示他和擁有人類局限的托尼的區別。《復仇者聯盟》系列中的視覺符號是具有審美性的,即相對于常規語言,更具審美效果,更容易激發出接受者的審美感知。以《復仇者聯盟3:無限戰爭》(Avengers
:Infinity
War
,2018)中的獵鷹山姆·威爾遜為例,他的戰衣擁有吸引人眼球的碩大翅膀,這是黑豹運用高科技為其制作而成的。當山姆要作戰時,翼展長達十五米的翅膀便會伸展開來,輕盈靈動地翱翔,而其鉤住對手的爪子這一靈感也顯然是來自鳥。山姆作為復仇者聯盟中頂級空戰專家的符號得以在可視的武備中成立。這一符號偏離和觸犯了現實的科學規律(如飛機等飛行器并不依靠機翼的扇動飛行),但是極能打動與感染觀眾,它強化了獵鷹的像鳥,能與鳥溝通的特征。與之類似的還有如《復仇者聯盟3》中的化身為鋼鐵蜘蛛俠的彼得、火箭浣熊等,而反派滅霸、紅骷髏等則面部丑陋怪異,在形式層面上加劇觀眾對他們的厭惡,在此不贅。同時,這些視覺符號在表意時還具有曲指性,即語義和符號之間的關系并不確定。“電影語言是沒有完善的表意系統的,它利用了與語言的類似原則,是一種類似的能指與所指關系。而電影語言也沒有規定的結構單元,是不具有自然語言那種強烈的離散性的,即在電影中單獨的鏡頭畫面是不能表現整部影片的含義的。”例如在導演喬斯·韋登表示自己拍攝的是一部“私人電影”的《復仇者聯盟2》中,就有著大量難以瞬間明白,承載了主創情感情緒流動的鏡頭。身為人類的希爾特工接受訊問,她提出了一個問題:“當一個人活在神明與怪物的年代,他的價值究竟幾何呢?”隨后鏡頭轉向雷神托爾,電影以一個仰拍鏡頭,讓托爾的臉模糊不清,占據觀眾視野中心位置的,是托爾巨大的錘子,而錘子上正滴落兩行鮮血。這就是一個含義模糊的、需要觀眾自行解讀的單獨鏡頭畫面。這個疑惑出自希爾特工之口,卻是神盾局的想法,原話為神盾局局長尼克·弗瑞所說,同時也是整個《復仇者聯盟》系列都在回答的問題。活生生地行走在地球之上,雖然“強龍不壓地頭蛇”,但畢竟有巨大破壞力的托爾就是“神明”,如果不是簡·福斯特,托爾與地球人的敵友關系還很難說,而他的弟弟洛基則是一個絕非良善的反派,而諸多反派則是“怪物”。在這樣的情況下,人類唯一能與之抗衡的只有高科技,如鋼鐵俠、美國隊長、黑寡婦、冬兵等無不是憑借高科技才能與神明怪物分庭抗禮,而這些高科技的研發也正是由許許多多如斯塔克工業集團中的普通人完成的,原本只是普通護士的簡對于托爾的愛、凡人的科研,都表明人類是自己的拯救者。此時托爾和他的流血錘子的表意就是含混的,有著較大解讀空間的。
二、從常規語言系統中脫胎的段落表達
如果說視覺符號是電影特有的技術與審美的結晶,是專屬于電影自己語言系統的,那么就段落表達而言,電影則與傳統的表意形式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尤其是對于旨在爭取盡可能多觀眾的商業電影來說,其整體敘事基本上可以被認為是脫胎于常規語言系統的。觀眾如果對漫威超級英雄電影的敘事進行提煉,就不難發現它與其他藝術類型,或它內部的各影片之間,都有著高度的相似性。
以《復仇者聯盟》系列而言,電影可以被認為是古希臘和中世紀神話傳說被改造過了的現代形態。在電影中,我們不難發現,人物的處境、經歷等往往可以在根植于西方民眾記憶中的《荷馬史詩》《埃涅阿斯紀》和《貝奧武甫》等經典中找到類似之處,回應著當代人呼喚參與偉大冒險的英雄,期待英雄干涉生活的集體無意識:在《復仇者聯盟》中,超級英雄是集體登場,各顯其能的。在《復仇者聯盟2》中,托尼·斯塔克原本是為了創造更好的世界才開啟了奧創計劃,未料奧創在擁有心靈之石后產生了自己的意識,認為威脅世界和平的是人類,斯塔克不得不與其他超級英雄們一起糾正自己的這個錯誤,而奧創也利用了快銀皮特羅與緋紅女巫旺達·馬克西莫夫來分裂復仇者們,直到最終快銀和緋紅女巫倒戈投入正義一方,奧創才被挫敗。這種激烈的對抗敘事為超級英雄們順利登場,相互配合,大放異彩提供了條件。
同樣,和古希臘神話一樣,《復仇者聯盟》中的英雄們一方面具有神性,但也有著極多的凡人特質,觀眾因此而對超級英雄們產生親近之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復仇者聯盟2》。在電影中,超級英雄們要面對奧創這一強大的敵人,而一心要滅絕人類的奧創最有力的武器則是“恐懼”。超級英雄們無論是身為神的雷神托爾,抑或是肉體凡胎的托尼,都不能完全戰勝自己內心的恐懼與憂慮。正如阿喀琉斯的傲慢與脆弱的腳踵,俄耳甫斯對妻子歐里蒂絲的情愛牽絆,最終都使得這些流淌著神的血液,擁有過人天賦和力量的英雄死于非命一樣,超級英雄們也都有著各自的致命弱點。在《復仇者聯盟2》中,旺達對諸位英雄實施了蠱惑,托爾在遭遇蠱惑后警告其他英雄對旺達小心提防,但他們還是一一中招:托爾去到英靈殿看到諸神黃昏,史蒂夫則看到了七十年前自己曾經許諾給心愛的女人一支舞蹈,然而兩人最終陰差陽錯地生生分離。娜塔莎則想起了自己在訓練營的畢業典禮上被強迫進行絕育手術的凄慘畫面,一直不能很好控制自己超能力的班納更是直接變身發狂,游走于城市中到處作亂。電影有意強調緋紅女巫的心理魔法而不是混沌魔法,正是為了給觀眾展現超級英雄們的恐懼回憶。展現英雄神力——暴露英雄弱點(電影中即恐懼本源)——表現英雄對弱點的戰勝或失敗,從而獲得悲壯、震撼的崇高美,這正是古希臘神話常見的段落表達,而這完全為《復仇者聯盟2》所靈活運用。觀眾通過電影能感悟到,超級英雄也會恐懼,也有弱小和無知的一面,他們也會面對巨大的威脅。如班納之所以會成為自己都嫌棄是“怪物”的綠巨人,是由于一場事故,這猶如古希臘神話中的神魔詛咒,是班納無力對抗的命運,而直到《復仇者聯盟3》中,他還因為在緊急時刻不能隨心所欲地變身而被戰友嘲笑。然而班納始終在努力,一邊馴服自己內心的野獸,一邊在科技上設計“反浩克重甲”以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這些段落表達都是文學語言系統的變形,都讓觀眾感到人物可愛可親。
三、超級英雄電影語言系統與精神文化
電影語言系統的構建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為影像技術,一幀幀影像是電影進行表意的基礎,而影像剪輯則是這種表意的主要構建形式;二則是更為抽象的意識形態。語言是具有社會屬性的,藝術語言也不例外。超級英雄電影所誕生的美國擁有的特定的精神文化,這是電影語言提取、總結與有意宣傳的對象,電影人所觀察、思考的社會現實,則是電影語言反映的對象。超級英雄電影對于目標觀眾而言,它是現實生活的一種替代品,它為觀眾提供了一個有超級英雄存在,并為普通人的生活做出巨大貢獻的世界,這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逼真模仿,電影語言勢必是人類精神意識的一種反映。
以美國隊長史蒂夫為例,電影中史蒂夫被塑造為一個心懷正義、為人正直、勇敢善良的幾近完美之人,他甚至可以拿起雷神之錘。而在史蒂夫成為具有獨特意味的、代表美國國家形象的角色后,他也就完成了美式價值觀和美國文化等意識形態的傳達。史蒂夫身上的種種美好品格,也在電影對觀眾的潛移默化之中提升了美國的國家形象,這在好萊塢業已形成文化霸權的當下表現得更為明顯。在《復仇者聯盟》系列中,史蒂夫永遠身著由紅藍白三色組成的戰衣,其配色與美國的星條旗相同,而史蒂夫最重要的武器——由振金做成的盾牌中間則有一個巨大的白色五角星,這也顯然是來自美國國旗上代表美利堅各州的星星(DC對超級英雄中最為“高大全”的神奇女俠的造型打造顯然也有著向美國國旗靠攏的傾向)。史蒂夫早已成為美國的品牌形象之一,而他在《復仇者聯盟》中的地位、行為等也自然而然地強化著美國積極、正面的形象。例如在《復仇者聯盟》(The
Avengers
,2012)中,電影以閃回的方式讓觀眾回憶起史蒂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歷,而在當代,史蒂夫已經是復聯當仁不讓的團隊領袖和精神內核,他作戰經驗豐富,指揮沉著鎮定,娜塔莎和克林特都心甘情愿地聽他調遣,在紐約街頭被狂轟濫炸時,是史蒂夫指揮市民疏散,為其他超級英雄布置任務。而閃回鏡頭則提醒著觀眾史蒂夫依然是《美國隊長》中騎著機車在槍林彈雨中依然毫不猶豫沖向納粹的那個堅毅沉著、代表絕對正義的美國隊長。在時代飛速進步,人們的價值觀也不斷被沖擊的七十年后,史蒂夫依然是讓整個團隊能力最大化的美國隊長,正是美國崇尚最大化展現個人價值,不向現實妥協的奮斗精神,英雄主義、保守主義等社會價值觀的反映,也是美國世界中心和領導者,正義維護者這種自我標榜的體現。而離開蘇聯陣營的娜塔莎(代表“冷戰”的另一方)、來自非洲小國瓦坎達的王子特查拉(代表第三世界)這些被復仇者聯盟攬入麾下,但都服膺史蒂夫,愿意和史蒂夫并肩作戰的超級英雄們,也都是這一“美國是救贖者”言說的參與者。電影同樣是一種通信方式,電影人和觀眾就是信息的發送者和接受者,二者順暢、愉快的交流過程,是電影獲得高度評價與票房回饋的前提之一。電影人在創作中,遵照不同的范式構建起電影語言系統,在《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的問世過程中,超級英雄的語言系統被漫威規則化,在其建立的視覺符號、段落表達以及映射的精神文化等方面,都獨特且為觀眾所認可,儼然成為這一類型片的標桿和顯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