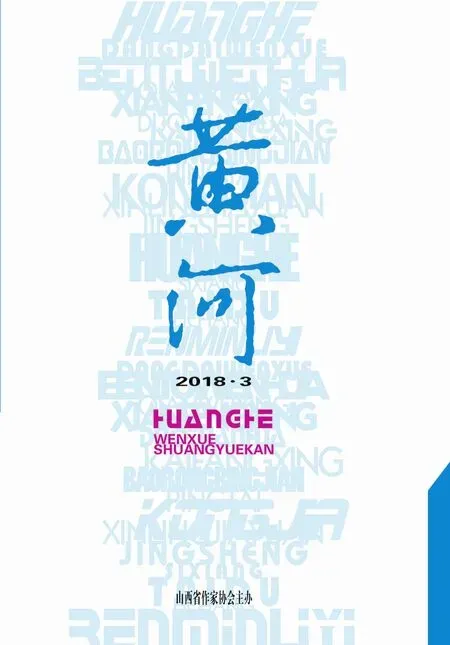一個終結時代的神話
楊晉生
從第一次拜謁雁門關,到最近一次再登雁門關,我始終懷著對雄關的崇敬。目睹它那蒼老的容顏,觸摸它那不朽的靈魂,我總是激動不已。如果說我對雁門關有一種無法抗拒和割舍的情感,那么很大一部分是緣自它開創歷史的悲壯和頑強。
雄厚的關墻已消失在歷史深處,破敗的城門像一個孤獨的老人一樣桀驁地挺立在風雨中。但一段城墻、一座關卡,只要它站在這里,就有或悲或喜的劇目上演。因此,我的尋覓格外虔敬,我的感悟也十分深刻。
雁門關為戰爭而生,為戰爭而損。雁門關前,除了刀槍劍戟的碰撞,就是血雨腥風的聚集。一個王朝倒下去,馬上就會有另一個王朝站起來。只有那冷峻的朔風在這里亙古不變。
“一人臨塞北,萬里息邊烽。”站在雄偉壯觀的城樓旁邊,如同走進遠古的歲月,整個身心都和歷史風云融為一體。舉目四望,群山連綿,古道悠長,威嚴肅穆的古長城猶如一道黑色的林帶,從遙遠的天際蜿蜒而來,然后又躍上山崗蜿蜒而去。朔風順著山勢迅疾而過,在山脊上形成強勁的力量,與邊墻不斷撞擊,如戰鼓擂響,似萬馬奔騰。
曾幾何時,雁門關如同一道生命的屏障,不可逾越。它把兩個不同生態的世界分割得無限遙遠,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存在凝固在縹緲的音符中,個體生命則像大漠深處夢幻般的溪流。在一幕又一幕歷史的大背景下演繹又消失著。
雁門關最終在滾滾烽煙中歸于荒蕪和沉寂,但作為一段塵封的記憶,一段擁有夢想與光榮的輝煌歲月,它將永存于歷史,傲然聳立于十萬大山中。
雁門關,終結了一個時代的神話,留下了一個游蕩于蒼茫天地、代代相沿的不朽絕響!
在黃褐色的蒼茫中,仰視巍然聳峙的關樓,它依然是那樣雄偉奇特、堅韌古樸。盡管風沙雷雨年復一年地打磨剝蝕,卻為它平添了更加震撼人心的魅力。
我用手輕輕撫摸著古老的城臺,觸到的是時間的流淌和歷史的厚重。
長城的修筑,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
然而,無論長城修筑得多么高大堅固,畢竟只是一種磚石構筑的防線,是一座無生命的建筑。長城的意志,需要將士同心、勇猛善戰的部隊來體現。可是,僅有這些就足夠嗎?
我不忍也不愿打開雁門關那厚重的歷史,更不愿翻動那一頁頁沉重的記載;我不忍也不愿看到殘忍的廝殺、刀砍的斷肢、槍刺的殘軀和殷紅的鮮血,更不愿看到鎮守雁門關將士的悲慘命運。因為,無論什么樣的戰爭,帶給廣大民眾的只能是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和無盡的心靈創傷、無邊的精神痛楚。
清靜加上荒涼,配上蒼勁的朔風、搖曳的衰草,雁門關黯然神傷。
長城是什么?對于北方的游牧者,長城就是目標。長城越長,越堅固,越能刺激他們的占領欲。這是修筑長城的人的悲劇,也是長城自己的尷尬。
盡管如此,歷史上的君王大多懷著解不開、割不斷的長城情結,只有康熙皇帝是個例外。他說:“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峙險阻。秦筑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是也。他還說:“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
康熙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國祚的延長,皇權的鞏固,絕非在于長城是否延袤萬里,堅不可摧,而在于能否輕徭薄賦,得道多助。
在康熙眼中,長城根本不是一種有效的軍事防御物,更多體現的是一種精神狀態。
縱觀歷史,游牧于漠南、漠北的蒙古部落,竄邊入塞而行燒殺搶掠者,歷朝歷代不絕于書。
雁門關見證了許許多多的人間悲劇,因此它一直沉默無語。
我崇拜英雄,我敬仰陽剛之氣。
雁門關的歷史是用男兒的血性書寫的,雁門關是一座充滿陽剛之氣的雄關,雁門關上演繹了無數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雁門關前造就了許多名垂千古的英雄人物。
但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雁門傳奇的背后有著太多的血腥,有著無邊的慘烈,有著難言的悲壯。
張秉忠 《雁門關懷古》:“趙國將軍同羨李,宋家名宦獨稱楊。塞垣紫色仍依舊,留得英風萬古長。”朱彝尊《雁門關》:“抗跡懷古人,千載誠多賢。郅都守長城,烽火靜居延。劉琨發廣莫,吟嘯扶風篇。偉哉廣與牧,勇略天下傳。”李牧、李廣、郅都、劉琨、楊業……這一個個光耀史書、彪炳千秋的大英雄最后的結局,不能不讓我們這些后人扼腕嘆息、捶胸頓足。
雁門關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在它巨大的背景下涌動著一連串感人至深的故事,這故事時不時透露出一種悲悒的美學色彩。
我深深地叩拜雁門,也深深地追懷英烈。
雁門關閱盡了世間滄桑,飽覽了人世更迭。如今,他靜靜地注視著每一個前來瞻仰的不速之客,像一個睿智的哲人,用目光讓人品悟生命的含義。
在充滿清涼氣息的城門洞內,腳下是光滑平坦的石板路,它那鐵青色的面容投射著時間和空間的不朽。兩道深深的車轍是那樣清晰分明。
遠逝的歲月里,十幾位中原女性先后乘車由雁門出塞,將中華文明之光照到了遼闊荒涼的塞北大漠。
正如那首詩所寫:“漢武雄圖載史篇,長城萬里遍烽煙。何如一曲琵琶好,鳴鏑無聲五十年。”在雁門關之上,女人是一只劃過天空的和平鴿。
就是這些平凡而偉大的女性,犧牲自己,帶來了短暫的和平,打通了國際貿易商路。
車轔轔,馬蕭蕭。一車車綢緞、瓷器經古關雁門運到了塞外,一車車皮毛、鹿茸又經古關雁門運回了中原,深深的車轍見證了雁門關當年的興盛景象。
古關轍痕,往來通行。
歲月的風塵掩得住古道,但掩不住古道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