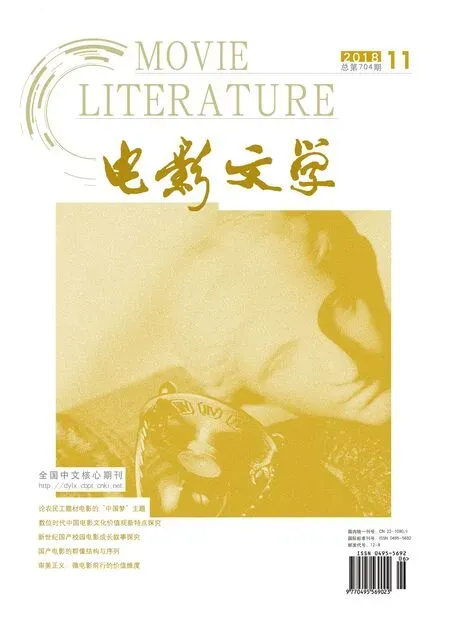《一次別離》的敘事張力:網狀節點設計
徐 燕
(平頂山學院 文學院,河南 平頂山 467000)
阿斯哈·法哈蒂畢業于德黑蘭大學戲劇藝術碩士專業,戲劇專業的學習底蘊使他能嫻熟地運用戲劇創作的技巧來創作電影劇本,他說:“首先,我喜歡戲劇的復雜性,在我拍攝電影的時候,我會假設我的觀眾們足夠聰明,能夠追隨戲劇作家創作的復雜性;其次,我從沖突出發構建故事。我電影的張力往往是來自角色間的沖突。”《一次別離》在外在結構上屬于閉鎖式結構,電影以納德與西敏在離婚法庭上第一次訴訟開始,以二人最終在離婚法庭離婚為結局,完整講述了一對夫妻離婚的始末。同時又在劇本內部設置了復雜的網狀結構,在故事的展開過程中,以二人離婚為起點,西敏搬出家庭,納德為了照顧患阿爾茨海默癥的父親莫爾塔扎,雇用鐘點工拉齊埃,拉齊埃在照顧莫爾塔扎的過程中產生了與宗教的沖突,又因為拉齊埃流產的突發事件,納德與拉齊埃、拉齊埃的丈夫霍賈特在不同的立場上產生了不同階層之間的沖突……多重人物關系之間都被精心設置了不同的矛盾沖突,電影中每一位人物都具有他所處境遇的那一類人的概括性特征,整個劇本呈現出多節點的復雜網狀結構,網狀的層層糾葛產生了極大的敘事張力,電影的內涵容量得到最大化的豐富,這也讓觀眾可以對《一次別離》進行多重化、多角度的解讀。
《一次別離》復雜的網狀結構形成了一個個矛盾節點,每一個矛盾節點都有力地糾結在一起,我們無法將這些矛盾節點輕易地解開理順,不能對矛盾雙方進行此對彼錯的簡單判斷。網狀結構中的所有矛盾節點置于激烈的糾葛當中,彼此力量相當,在雙方激烈的撕扯之中讓受眾感受到生活與人性的復雜,這種網狀結構矛盾節點的構思方法對劇本創作具有較強的指導價值。
矛盾節點之一:女性與男性之間的隔膜
女性在伊朗社會所遭受的困境是阿斯哈·法哈蒂電影始終關注的主題之一, 自1979年伊斯蘭教什葉派重新確立宗教、政治統治地位之后,在此之前賦予女性的一些權力被視為不符合伊斯蘭教律例而被取消。《古蘭經》規定 :“男人是維護女人的,因為真主使他們比她們更優越……”女性被置于毋庸置疑的第二性地位,男性對女性具有宗教、法律上的優越權力。但是阿斯哈·法哈蒂對女性的詮釋不是從女性主義角度進行表達,在對女性的處境予以理解同情之余,他更關注的是不同性別的人物如何從自己的性別立場出發,對同一事物的認知角度、處理方式的差異。
首先,男女之間由于身處社會環境的感受不同,兩個性別之間對生存狀態的認識具有迥然不同的感受,男性認為這個社會對于男女地位的定位是可以接受的,而具有較開闊視野的女性卻感受到這個社會對女性待遇的不公正。《一次別離》的女主人公西敏是語言學院的教師,男主人公納德是銀行管理人員,二人圍繞著是否應當帶著女兒泰爾梅移民的問題在離婚法庭上針鋒相對。西敏質問納德:“你女兒的前途對你來說就無足輕重嗎?”男性法官立刻反駁西敏:“那么所有生活在這個國家的孩子都沒有前途嗎?”納德同樣愛自己的女兒,他會在妻子離家出走后給女兒聽寫單詞,接送女兒放學,注重與女兒的溝通,他并不認為女兒生活在這個社會里有什么不好,西敏堅持帶女兒移民,她告訴納德:“我擔心自己的孩子。”但納德卻認為:“你的孩子想生活在此地,在這個社會里。她必須留在這里完成學業。”兩人都是在討論孩子的前途問題,西敏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對女兒的生存環境表示擔憂,而無論是法官還是泰德,他們將孩子這個概念僅僅理解為廣義的“孩子”,并不認為這個社會對女性的生存發展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
其次,男性與女性出于不同的慣性思維,雙方關注的角度與解決問題的方式截然不同,由此帶來了雙方溝通的隔膜。當納德與照顧父親的鐘點工拉齊埃發生沖突后,拉齊埃流產,霍賈特將納德告上法庭,并不停地到泰爾梅的學校吵鬧,終日在學校附近徘徊,西敏擔心女兒的人身安全,與霍賈特達成協議,愿意賠償金錢讓霍賈特撤訴,但納德卻認為西敏沒有權力這么做,他認為:“如果我付錢,那就意味著我承認這是我的責任。他不會放過我們的。”兩人看似在討論同一個問題,但西敏認為納德是否導致拉齊埃流產不重要,重要的是霍賈特以此為發泄的理由,女兒的人身安全沒有保障;而納德卻認為,一旦同意付錢給對方,就等于承認了確實是自己導致拉齊埃的流產,這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也是懦夫的行為。納德不讓西敏帶走泰爾梅,也是基于同樣的看法:“我不想讓她跟你學成一個懦夫,每次別人一嚷嚷你就害怕。他知道這招對誰管用,他干嗎不來威脅我?”
納德與西敏之間的婚姻矛盾是阿斯哈·法哈蒂設置的網狀結構中的樞紐性節點,夫妻雙方從各自不同的性別角度進行認知,不同的性別視角遮蔽了事件的一部分真相,從而產生無法溝通的隔膜。
矛盾節點之二:傳統文化與現代意識的沖突
《一次別離》產生敘事張力的矛盾豐富性在于,電影并不是簡單地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意識對立起來褒此貶彼,而是辯證地表達了二者存在的合理性與局限性。電影既表現傳統宗教對人性自由的限制,也肯定宗教信仰對危害他人行為的有力約束;既有對現代意識合理性的認可,也呈現出現代意識與傳統人倫規范的沖突。
對自由的追求是人類的天性,但作為社會群體中的一員,個體對自由的無限追求必然會影響到其他個體的自由,那么國家、宗教、他人的要求就會使個體的自由形成阻礙,人類不得不在順從群體要求的前提下讓自己獲得更高的自由度,因此,在面臨不同的壓力之時,人類既要抵抗這種壓力,又要為自己的抵抗行為尋求合乎社會群體規范的合理解釋。“自由是充滿了痛苦的抉擇,因為一個人的情感和需求會與國家、宗教以及其他人的情感和需求相背離。”在電影中,幾乎每一個成年人都表示自己是虔誠的教徒,有著堅定的信仰,但是當他們面臨的境遇與教義發生沖突時,是順應教義壓抑個人的理性認知,還是違背教義聽從自己內心的選擇,這種突如其來的壓力給人物帶來了兩難境遇。拉齊埃是一位虔誠的教徒,她在納德家發現納德的父親大小便失禁,教義規定非夫妻的成年異性之間不得進行身體接觸,但是從人性角度出發,拉齊埃又不忍心讓老人受罪,最終還是幫助老人清洗了身體,拉齊埃這件違背教義的行為,讓人們看到了傳統宗教的局限性。當納德同意花錢消災,他讓拉齊埃將手放在《古蘭經》上發誓,確實是他導致拉齊埃摔倒流產。拉齊埃面臨丈夫失業、欠下大筆債務的窘境,雖然丈夫央求她隱瞞真相,但信仰讓她說出事實,她擔心接受不合教義的錢財,罪孽會將災難降臨在女兒身上。在這里,我們又看到宗教信仰對遏制人類自私本性的強大力量,信仰能夠讓人類產生顧忌,遏制惡行的發生。
西敏急于帶著女兒移民,是追求女性獨立自主的現代意識的體現,她希望讓女兒有更廣闊自由的生存空間,不再承受不平等的人生桎梏。電影非常精彩地用細節呈現了女性在這個社會中所遭受的沉重壓力,雖然西敏是一位職業女性,但是觀眾通過劇情呈現,知道在西敏離家出走之前,這個家庭的家務、照顧老人的重擔都是西敏在承擔,患阿爾茨海默癥的納德父親已經不認識兒子,但是他認識西敏,在西敏跟納德爭吵的多個場景中,老人像孩子一樣依賴西敏;當西敏離家出走,納德因為不會使用洗衣機不得不求教于女兒,因為不會使用洗碗機而心煩意亂。很顯然,納德在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并沒有參與到沉重的家務勞動之中。女性生存的壓力與權利的不對等,使觀眾能夠理解西敏急于帶女兒離開的行為。
而納德不想離開伊朗的原因是患阿爾茨海默癥的父親需要照顧,這是傳統文化對人們倫理道德的規范,也是兒子應當照顧不能自理的父親的責任。兩個人去留的原因都出于親情的考慮,一個是為了下一代,一個是顧慮上一代,他們執著于自己的立場,堅信自己的行為是正確的。恰是這種沒有對錯卻互不妥協、劍拔弩張的境況,讓觀眾感受到撕裂般的選擇疼痛。
矛盾節點之三:貧富階層之間的誤認
在《一次別離》中,阿斯哈·法哈蒂設置的網狀結構的矛盾節點還有不同社會階層人物之間的沖突與誤認。無論是中產階級的納德與西敏夫婦,還是貧民階層的霍賈特與拉齊埃夫婦,他們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好人。但由于雙方不同的階層差距,使得他們無形中都將對方賦予了原罪性的認知,不同階層的人物從自己的角度去揣度其他階層的人物,被遮蔽的視角使事情真相也被遮蔽,從而產生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
在以納德等為代表的富裕階層的認知中,貧困便是貧民階層的原罪,在他們的潛意識里,貧民階層為了謀生會借助不法手段牟取金錢,也會預設他們由于貧困而導致缺乏教養、性情粗野。納德回家發現拉齊埃將父親綁在床上擅自出門后,暴怒的他發現抽屜里少了一些錢,便自然而然認為是拉齊埃偷拿了這些錢,而觀眾知道抽屜里少的錢是西敏之前付給了搬運工。西敏愿意賠償霍賈特,并不是真的認為納德導致了拉齊埃的流產,而是為了女兒的安全,寧愿花錢買平安,霍賈特一針見血地指出:“我難過就難過在這里。夫人,你憑什么認為我是為了錢才打官司的?……我心里明白!沒人瞧得起我們這種人。”拉齊埃流產的原因是她去街上尋找出走的納德父親,不小心被汽車撞了一下,而泰爾梅的老師加赫拉艾太太愿意為納德做證,是由于看了拉齊埃女兒的畫,猜測拉齊埃流產是霍賈特毆打所致,因此霍賈特質問加赫拉艾太太:“你憑什么認為我這種人就會像禽獸一樣打老婆孩子?我以《古蘭經》發誓,我們是像你一樣的人。”
而在以霍賈特為代表的貧民階層人們的潛意識里,有錢人是為富不仁、缺乏信仰的,是彼此包庇瞧不起窮人的。霍賈特曾經是一個勤快的鞋匠,但他在為老板工作十多年后被解雇,這讓他認為有錢階層都是冷酷無情的人,霍賈特起訴納德后,因為加赫拉艾太太和鄰居們的證詞對他不利,霍賈特便認為是這些有錢人串通好了欺負自己,甚至認為法官也偏袒有錢人,對富裕階層的偏頗認知以及對生活的絕望,使他以趨于極端的方式進行對抗,甚至在法庭上宣稱要自焚來捍衛自己的權利。電影對霍賈特這個陷于極度貧困人物的描繪,表現出橫亙在貧富階層之間巨大的鴻溝,也對由于貧富階層的矛盾而可能引起的社會問題提出警示。
伊朗是公認的電影審查極其嚴苛的國家之一,《一次別離》的攝制成本僅僅花費了30萬美元,在創作自由受限、低成本預算的限制下,電影憑借細膩而富有張力的劇情呈現,喚起了受眾的情感共鳴。在電影中,沒有絕對的好人與壞人,男性與女性、中產階級與貧民階層、宗教與人性、傳統文化與現代意識等多種矛盾碰撞、拉扯,每個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對發生的事件進行解讀,評判事情的對錯,阿斯哈·法哈蒂在敘述故事時隱藏了個人的價值判斷,使受眾對電影中的每個人物都予以理解同情。這種多節點網狀結構的矛盾設置、零度敘事方式所帶來的敘事張力,讓電影具備了豐富的闡釋空間,也讓不同的受眾在各自的認知體系中對電影中的人物產生不同的情感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