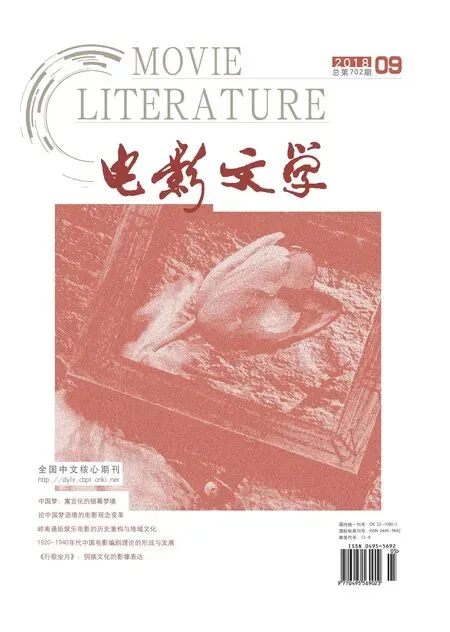美國主流電影的景觀化與文化隱喻
王紅麗
(河南工程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3)
景觀電影的大行其道,已經成為當前人們的共識。在電影的景觀化方面,美國好萊塢的各大電影巨頭拍攝的,代表了其社會主流文化和價值觀的主流電影,可以說起著舉足輕重、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在人們討論景觀電影的精神、理念與技術時,美國主流電影都是不可回避的范例。但景觀化并不能改變電影作為生活之“窗”與“鏡”的屬性。在美國主流電影中,文化隱喻依然是其魅力之一,觀眾在欣賞美國主流電影時,并不能單純被動地接受影像,而不對影像進行主動性的意識建構。
一、影像的景觀化
當人們提及“好萊塢大片”這一美國主流電影的代名詞時,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影片的視覺沖擊力。毫無疑問,在給觀眾制造新奇影像,以視覺沖擊力吸引觀眾方面,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拍攝出了轟動全球的《星球大戰》(Star
Wars
,1977)的美國走在了世界的前頭,并且隨著時代的發展,電影在商業運作和數字技術上的成熟,這種景觀化終于從盧卡斯的一枝獨秀,成為美國電影的整體創作傾向。我們只要選取早年的美國主流電影與當下主流電影進行比較就不難發現這種景觀化發展。如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由弗朗西斯·科波拉執導的《教父》(The
Godfather
,1972)稱得上是一部典型的傳統敘事電影,電影的魅力也正是在于其中的故事情節、人物形象。在電影中,美國黑手黨家族之間存在復雜的矛盾,“教父”柯里昂身陷于各種矛盾當中。電影的故事高度完整,邏輯關系與時間關系清楚且微妙,事件與事件之間存在嚴格的秩序規定,讓觀眾津津樂道,而有著深層性格的,在一個個事件中面貌逐漸清晰的柯里昂也讓觀眾印象深刻。這樣的電影對于劇本的依賴性是極大的。但是在景觀化之后,電影追求的是讓觀眾目不轉睛而非對情節的思考,對人物的慨嘆。提供故事、邏輯的劇本的地位下降了。隨著景觀越來越重要,甚至敘事也可以對景觀做出讓步。這種讓步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弱化情節結構,即觀眾接受到的是一個高度簡單的故事。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便是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達》(Avatar
,2009)。電影本身的敘事不僅簡單,且完全沒有脫離好萊塢電影個人英雄主義的藩籬和“英雄救美(或美救英雄)”的俗套。而這種不能免俗很大程度上在于卡梅隆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完成了劇本的創作:傷殘的退伍兵杰克代替自己的弟弟參加了去潘多拉星球與納美人接觸的計劃,從而在健康軀體的誘惑以及對被殖民的納美人的同情中加入了納美人一方,反抗前來采伐的人類,并取得了最終的勝利。而在后來的十余年中,卡梅隆則投入到以技術來打造這個故事上。最終,電影也憑借著一個美輪美奐、五彩斑斕,擁有各種奇怪華麗動植物的外星世界,以及藍色、優雅的納美人形象贏得了觀眾的贊許和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而與卡梅隆自己的,沒有使用3D技術的《泰坦尼克號》(Titanic
,1997)相比,電影在場面上也更為恢宏壯闊、驚心動魄,但是無論是愛情線上男女主人公的分分合合,抑或是在生死問題上主人公與死神的幾番對抗,《阿凡達》都要明顯弱于《泰坦尼克號》。二則是為電影加入大量缺乏敘事意義的場面,換言之,盡管電影給觀眾提供的依然是曲折、精彩或豐富的情節,但是電影的亮點卻在部分具有視覺效果的場面上,且這些場面有“為景觀而景觀”之嫌,電影在景觀和敘事上出現了一種割裂。例如,在沃卓斯基姐妹的《黑客帝國》(The
Matrix
,1999)中,電影的背景設置是有趣且富有哲思的,所謂的現實世界實際上是人工智能設計的一個矩陣,而人則是人工智能豢養的動物,專門為人工智能提供能量。整部電影中人類對自由自主的追尋就是一種反“異化”的追求。而電影留給人們印象最深刻的卻是在袁和平指導下的打斗場面,古老的中式武術被融入一個西方的、未來的場景中。如尼奧在躲避子彈時,子彈的速度降低,槍林彈雨宛如凝固,在360°旋轉的鏡頭中,尼奧以“鐵板橋”招式向后仰天斜倚,子彈無一打中。這打斗本身的敘事意義是極少的,但是它完全超出了自然常識和觀眾的想象,成為觀眾最津津樂道,最能吸引人們反復觀看的內容。與之類似的還有如羅伯·馬歇爾的《加勒比海盜4:驚濤怪浪》(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On
Stranger
Tides
,2011)。由于演員的缺席,在前三部電影中極為重要的威爾·特納和伊麗莎白的愛情線被刪除,電影不得不把敘事集中在以杰克·斯派羅船長為首的海盜們身上。而這并不意味著這個架空的電影情節是平淡的,杰克船長尋找“不老泉”,并在途中遭遇了舊情人安吉莉卡和她的父親,即臭名昭著的海盜“黑胡子”。但電影依然使景觀喧賓奪主。電影中出現了美麗而又危險的美人魚,不僅有令觀眾屏住呼吸的人魚大戰,美人魚還和人發生了一段戀情。這無疑是正如勞拉·穆爾維指出的,性感的、美艷萬方的美人魚在視覺形象上是一個被觀眾凝視的對象,電影在這里完成了一種啟動觀眾身體快感機制的色情編碼,對觀眾的窺淫癖和自戀癖進行了滿足。這也是為何《加勒比海盜4》被人們戲稱為一部靠美人魚拯救的影片的原因。但是美人魚本身與斯派羅船長的個性是關聯不大的,如果將美人魚置換為其他與女性身體客體化無關的元素,整個歷險故事也是可以進行的,但這顯然不是馬歇爾會選擇的操作。一言以蔽之,景觀化造成了電影雖然依然離不開故事性元素,但是敘事越來越像景觀的背景,是景觀被打造的必要的框架。觀眾和電影之間的關系從原先的“理解電影”越來越向著“體驗電影”的方向發展。
二、電影的隱喻性
景觀化帶來的影響無疑是深刻的,在一場場視覺盛宴中,美國主流電影有著被詬病為藝術淪為商業和技術奴隸的嫌疑,觀眾則被認為“失去了自我意識和自我判斷,對電影的觀看已經不是一種文化行為,而僅僅是一種可以把思維關掉的娛樂行為”。但這并不意味著電影人與觀眾都統一只有對絢麗震撼的奇觀畫面“驚顫效果”的追求,反之,就主流來說,美國電影依然是保留了意識深度、批判精神和文化個性的,這才是美國主流電影能夠長期在世界電影中占有不可撼動地位,向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文化輸出的根本原因。
而這種意識深度、批判精神和文化個性,很大程度就體現在電影的文化隱喻中。在美國主流電影中,隱喻的存在是多方面、多種形式的。
(一)圖像與文化隱喻
在圖像中包含隱喻是電影中較為常見的一種修辭方式。圖像包括人物形象、道具等。這種隱喻有可能是較為顯豁的,如《V字仇殺隊》(V
for
Vendetta
,2005)中大獨裁者蘇特勒隱喻了希特勒等,也有可能是較為晦澀的。以蒂姆·伯頓的奇幻影片《剪刀手愛德華》(Edward
Scissorhands
,1990)為例,電影中主人公愛德華是一個長相奇特的機器人,他的命運悲劇很大程度上就與他的這一身份有關。而愛德華的形象以及他問世的過程,其實與德國20世紀20年代具有表現主義色彩的科幻電影《大都會》(1927)中的機器人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在表現未來社會的《大都會》中,科學理性成為魔鬼,機器站在了普通人的對立面。飽受剝削的工人們在瑪利亞的煽動之下瘋狂地搗毀機器。機器人因電影而成為一種具有邪惡義的象征,而愛德華則在后者的象征義基礎上,在另外一個語境中成為一個隱喻性的符號。在《大都會》中機器代表了人類恐懼、排斥和批判的科技,而在《剪刀手愛德華》中,愛德華卻是善良、純真的化身,邪惡的、需要被批判的反而是人類自己,因為人類相比起愛德華有著嚴重的道德缺陷。這種隱喻是高度晦澀的,如果觀眾并不了解《大都會》的話,就有可能單純將愛德華視為一個怪異丑陋、和人類格格不入的機器人,掌握不到伯頓在這個形象上投入的深意。(二)敘事與文化隱喻
敘事要完成隱喻通常需要一個眾所周知的傳說、傳奇故事抑或是現實中發生過的真實事件作為本體(并且在這種本體中,傳說、傳奇等往往已經構成一套經典隱喻模式,如灰姑娘和王子最終必然在一起的“灰姑娘”故事等),而電影中的故事則充當喻體,在比喻過程中,電影則會制造一定的位移或差異,以給觀眾新鮮感。例如,蓋瑞·馬歇爾的《風月俏佳人》(Pretty
Woman
,1990)中,灰姑娘和王子之間因灰姑娘的自我包裝而在誤會中發展愛情的敘事被位移為紅燈區的妓女薇薇安和百萬富翁愛德華·劉易斯之間克服身份等差異終成眷屬的故事,并最終將王子公主式童話落到“只要有夢想和真心就可以獲得真摯愛情”的“美國夢”文化宣講上來。而以現實事件為本體的則有如安德魯·亞當森的《納尼亞傳奇:獅子、女巫和魔衣櫥》(2005)中,衣柜將電影中的空間分成了兩個世界,而納尼亞世界中發生的一切,露西等孩子幫助阿斯蘭戰勝邪惡的白女巫的故事,實際上是對另一個世界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隱喻。盡管在現實生活中,孩子們是被保護的對象,正是因為躲避戰亂他們才會住進有魔衣櫥的屋子,但是他們在納尼亞卻是扭轉形勢的英雄,因為孩子代表了純真、正義。電影通過這一奇幻歷險故事表明正義的力量盡管有時看起來孱弱,但是它必然取得二戰最終的勝利。這是一種典型的邪不勝正文化的隱喻。(三)類型與文化隱喻
美國主流電影的類型隱喻是較少人注意到的,然而也正是因為美國在類型片制作上的成熟,電影人們不斷遵循類型又突破類型,因此美國主流電影中同樣存在靈性飛舞的隱喻。以雷德利·斯科特的《末路狂花》(Thelma
&Louise
,1991)為例,電影中的女性主義文化已經為人們所共知,但是人們卻很容易忽視,這一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電影的西部片類型隱喻上表達出來的。電影中的兩位女性塞爾瑪和露易絲的周末逃亡之旅,有著如沙漠等西部片和公路片的類型元素。個性強悍的露易絲始終穿著牛仔裝,而從柔弱的家庭主婦逐漸變得堅強的塞爾瑪的著裝也從連衣裙變為牛仔裝,甚至在打爆了油罐卡車后她戴上了牛仔帽。兩位女性化身為快意恩仇、沖向自由的“牛仔”。這正是一種對于美國早年西部片以及牛仔文化的反撥:在西部片中,女性幾乎都是男性拯救的客體,而在《末路狂花》中,女性拒絕了男性的拯救,要自己解救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角。當她們走投無路之際,寧可選擇開車跳崖自殺也不愿意再繼續接受男性伸來的援助之手。當從西部片的角度來審視這部電影的時候,我們就不難發現其中的女性主義光芒更為耀眼。美國電影是確鑿無疑的當代電影景觀化的領導者。在科幻、災難、魔幻等類型片具有領導性地位,不斷給觀眾制造虛擬世界或虛擬體驗,讓觀眾在視聽感官中獲得如夢似幻的感受方面,美國主流電影的成就和影響力是不可否認的。而另一方面,在展示千姿百態的景觀的同時,美國電影并未忘記使銀幕之像具有文化隱喻意義,在圖像、敘事和類型等方面使形式具有表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