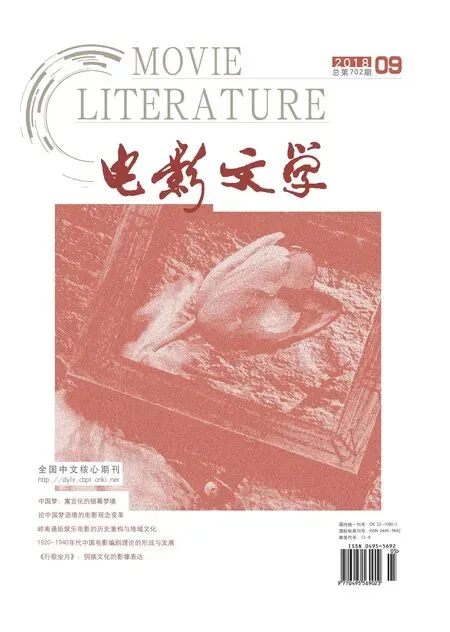詮釋與結構:電影《芳華》解讀
余 宏
(中共銅陵市委黨校 管理教研室,安徽 銅陵 244000)
電影《芳華》由馮小剛執導,根據嚴歌苓同名小說改編,以20世紀七八十年代為背景,講述了在充滿理想和激情的軍隊文工團,一群正值芳華的青春少年,經歷著成長中的愛情萌發與充斥著變數的人生命運故事。該片于2017年12月15日上映后,影片口碑不斷發酵,不僅吸引了大批年長的觀眾,也引發了年輕群體的熱議。這股“芳華熱”的背后既有影片中對青春年華的生動側寫,也有對時代和人性的洞察入微。從理解的層面來探討“芳華熱”,我們會發現有兩種不同的理解路徑推動著大眾的認知升級。
一、從詮釋路徑理解《芳華》的作者意圖
詮釋學的發展可以追溯到德國哲學家弗雷德里克·施萊爾馬赫和威廉·狄爾泰的研究,他們兩人都堅持,“對人類活動的理解必須抓住行為背后的主觀意識來進行”。也就是說,他們都強調對于人類的藝術活動的理解,先是要對藝術作品背后的藝術家的發現,必須仔細研究這位藝術家而非他的作品。這樣的思想對詮釋學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在面對如何理解視覺文化時,理解變成了如何掌握具體的編劇和導演在視覺作品中所表達的意圖的問題。這些意圖可以被理解成想法和觀念,它是編劇和導演關于周遭世界的所思所想以及自己的信仰。這些所思所想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會隨著時代或生活空間的變化而變化。理解過程就是對編劇和導演意圖的探究過程,這個過程存在一個歷史距離,即詮釋者和作者的生活之間存在歷史距離。理解者自己所處的時空與作者所處的時空不一致,造成誤解的產生。因此,理解者必須超越自身所處的環境,跨越歷史鴻溝,抵達作者的時空,認知作者意圖。正如林格所說:“要求我們克服我們自身現實存在的任何關于理解的理想。”
用這樣的詮釋理論來理解電影《芳華》時,理解者首先需要理解編劇嚴歌苓的人生,以此為出發點才能理解嚴歌苓在劇本中所要表達的所思所想。嚴歌苓在12歲時,報考了部隊文工團,成為一名芭蕾舞文藝兵。影片《芳華》中所表現的部隊文工團生活可謂是作者生活的一個真實寫照。在部隊文工團工作生活的8年里,她多次赴邊疆進行演出,舞蹈在那段時間成為她生命里的靈魂。15歲時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次愛情,她愛上了比她大好幾歲的排長。短短6個月,寫出了160封情書。當時在部隊,戀愛是明確禁止的,兩人只能通過眉目傳情。沒想到的是,他們之間的戀情被上級發現,排長為了保全自己居然主動拿出情書,檢舉揭發了嚴歌苓。嚴歌苓被懲罰,一遍一遍寫檢查。寫完一遍,領導說寫得不夠細不夠真誠,打回重寫,嚴歌苓只好寫細節。戀愛是美好的私人情感,在制度和權力的逼迫下不得不從心事走向公事,從美好走向罪惡,可想而知,當時的她是多么的屈辱。這一真實事件也被反映在電影當中,劉峰向林丁丁表達愛意之后,被林丁丁揭發,在部隊領導的逼迫下,一遍一遍寫檢查,還被要求承認猥褻罪,劉峰不同意還打了領導,然后被發配邊境。嚴歌苓和劉峰對美好愛情的向往都被殘酷的現實所擊垮,所擊垮的不僅是身體更是精神。結果是,20歲的嚴歌苓自愿參加了對越自衛反擊戰。身為女兵,嚴歌苓在后方負責傷員包扎任務。當一個個傷員被送進包扎所里,嚴歌苓才意識到戰爭是救贖不了靈魂的。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失去了自己的肢體,恐懼和絕望包裹著她。電影中最不受文工團待見的何小萍因以發燒39℃為名,拒絕高原獨舞,被發配到中越邊境做戰地護士后,她對這個冷漠的集體徹底失望,生出了只求一死的意念。這個角色正是將嚴歌苓本人的戰地生活融入進來,在靈魂受到創傷的背景下,沒有任何尊嚴地活著,這種活著反而不如死去。劉峰和何小萍其實是作者兩段經歷的復合體,劉峰代表著懵懂中的愛、純潔的愛,代表著人類最純真的心理底色。何小萍代表著殘酷中的愛,在人類靈魂遭受巨大創傷時,生命是可以放棄的,但我們不能放棄的是對愛的憧憬。這一點在影片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槍林彈雨中,何小萍守在一名16歲即被燒傷致死的小戰士床邊本能地陪伴,彰顯了殘酷現實中的愛。通過對作者兩段經歷的梳理,我們可以理解影片中所傳遞的人文關懷和人性善的側寫。
二、從結構路徑理解《芳華》的價值體系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將結構主義稱為:”無意識的價值體系或表征系統,這個體系使社會生活的任何一個層面都井然有序,而且個體意識的行為和事件都據此而產生并且可以理解。”他的意思是說,個體及其行為和意圖不是理解的根源,反而是理解的結果。受眾并不需要通過理解作者的意圖來理解作品,受眾想要達成理解就必須回歸到價值體系和表征系統中去探求。在詮釋學看來,意義是個體意圖的產物,讀者只能到個體意圖那里去尋找意義。而在結構主義看來,意義是被建構的東西,是一個永恒結構中的某一階段產物,是一系列有組織的要素中的一個部分。這是兩者之間最根本的區別。這一理解方法的集大成者是列維·斯特勞斯,他在《野性思維》一書中認為人類的認識活動是通過差異和對立來進行的。例如,在我們通過語言賦予自然界以差異、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等。這種差異對立在我們的文化系統中比比皆是,我們的文化系統也正是由一組組差異和對立構成的。從本質上說,結構就是一個差異系統。一個符號以兩種方式與其他符號相聯系和相區別。符號學稱為橫組合和縱聚合。“橫組合差異是事物、符號之間前后出現的差異。縱聚合則是事物、符號之間能夠相互替換的差異。”比如我們在請客時會選擇先喝酒吃菜然后上主食,這就是橫組合。我們可以喝白酒、黃酒和紅酒,我們可以吃米飯、面條和大饃,這之間具有替代關系,這就是縱聚合。只有對文藝作品中符號之間的組合和聚合關系掌握之后,我們才能有效地理解文藝作品。
用這樣的結構理論來理解《芳華》時,理解者首先要把握電影的敘事結構。該部影片圍繞劉峰、何小萍、蕭穗子、林丁丁、郝淑雯和陳燦這六位主角的工作生活來展開敘事的。在這六位主角中,他們之間也構成了差異和對立。劉峰和何小萍構成了故事中的另類,一個是活雷鋒,一個是飽受排斥的女兵。兩個人的聯系從影片一開始劉峰去北京接何小萍來文工團就展開了。當沒有人愿意和何小萍搭檔跳舞時,劉峰不顧腰傷與她共舞時,兩人的關系得到升華。正如影片中的旁白所說,一個始終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識得善良,也最能珍視善良。在當時集體主義價值觀盛行的年代,他們兩人的行為可以理解為時代(集體主義)的邊緣者。一方面他們嘗試各種途徑想融入集體,另一方面集體總是那么的排斥他們。郝淑雯與陳燦,是第二對,郝淑雯是干部子弟出身,性格直爽,特長是手風琴,在文工團里擔任報幕員、舍長,而陳燦也是干部子弟出身,樂隊號手。“號手和報幕員都是西方攝影意象中最經典的紅色隱喻——中國革命的領路人,同時也是預言人。”這背后都暗示著,他們在權力所構建的系統中處于一個優勢地位。郝淑雯的命運軌跡是由文工團大姐嫁入豪門成為全職富太太。陳燦的命運軌跡是文工團之草娶了高干子女最后成為地產商。這與劉峰和何小萍的人生軌跡完全不一樣,劉峰和何小萍都從戰斗英雄跌落為底層民眾,這種差異正昭示了集體主義得利者與集體主義邊緣人的差異。蕭穗子和林丁丁是第三對。蕭穗子是文工團的領舞,經常負責出黑板報,命運軌跡由文工團活躍分子到上大學成為城市書店老板。林丁丁是文工團獨唱演員、第一美女,最大的夢想是嫁給軍隊高官做兒媳婦,命運軌跡由文工團之花嫁入豪門成為富太太。她們二人體現了典型的時代型人格,隨波逐流。只能充當時代的傳聲筒,不能對時代有所反思,其實也是社會中的大多數。這三對分別構成了那個時代的邊緣者、得利者和從眾者,他們的差異是非常明顯的。在各自三對的縱聚合里,他們之間也是可以相互替換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三、結 語
奧登(Ogden)與理查茲(Richards)在他們合著的《意義的意義》一書中,嘗試對意義進行區分,羅列了關于意義的16種解釋,如下:“1.一種內在的屬性。2.一種與他事物之間的、獨特的、無法析解的聯系。3.附加在辭典中某個詞之上的另外一些詞。4.一個詞的內涵。5.一種本質。6.投射于某對象的一種活動。7.某一意向中的事件或某種意愿。8.某物在一個系統中的特定位置。9.對某一事物在我們未來的經驗中的可行的推斷。10.由某一個陳述所包含或暗指的理論推斷。11.被某事物所激起的情感。12.按照特定的關系,與某個符號實際相關的東西。13.與某一事物的記憶效果相應的某些其他事件。14.某一象征符號的使用者應當具有的指涉。15.某一符號的使用者自己所相信的指涉。16.某一符號的解釋者自己所確信的指涉。”
從這個定義我們可以看出,意義本身往往比意義所依附的載體更加具有復雜性,因為意義可以不斷地在載體中流動和變換。一部影視作品的意義是多元的,不僅僅因為影視作品的符號所呈現的固有意義序列,還在于它和不同主體之間的復雜信息編解碼關系。它能夠將自身投射到人們的觀影活動中,它能夠激起觀眾的情感反應,它能夠將過去所有已經成為文化符號的積淀一次性地展陳出來,它能夠將自身作為一個符號置于整個文化符號系統中獲得象征與功能,它能夠讓無數的影評人對它進行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歷史、心理和倫理的多元理解……在這里存在的唯一界限可能就是沒有界限,但沒有界限不是意味著價值層面的缺失。恰恰因為理解的多元和意義的多元,在當前影視作品的解讀中更需要樹立價值層面的標桿,這樣才能更好地以符合人類價值標準的意義理解來引領文本意義領域的混亂。
對于《芳華》的理解,不管是詮釋的方法還是結構的方法,對于理解該部影視作品都是必要的。一方面,我們可以將作者意圖作為理解的終極目標;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將作品中內在的價值體系作為理解的終極目標。每一種方法都能夠在自己的理論視域內自圓其說,能夠通過理論自身的支持得出新穎的理解成果。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具有一致性,因為他們都贊成影視作品是一個意義的場域,值得觀眾去深度挖掘的意義大地。人們掌握越多的理解方法,就越能從對象中認識和理解人本身的復雜性和意識形態的復雜性。人創造了文化,又被文化所改造,我們既構建了理解自身以及本質力量對象化的工具和體系,這些工具和體系又反過來建構了我們。構建和建構之間的核心即具有人的屬性的意義。在這種互動關系中,主體不僅處于意義網絡中,同時對意義之網還需要進行理性批判,什么意義對人來說在價值序列上是更加重要的。這一結果加深了在理解中對價值判斷的需求。不管對象如何復雜,理解對象的方法如何眾多,意義的創造、理解和傳遞如何紛繁,都需要肯定人文關懷這個終極價值對我們的作用。所有的理解都必須有對人的生存狀況的關懷、對人的尊嚴以及符合人性生活的肯定。否則,理解或詮釋將變得不再具有人的屬性,墮入異化的牢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