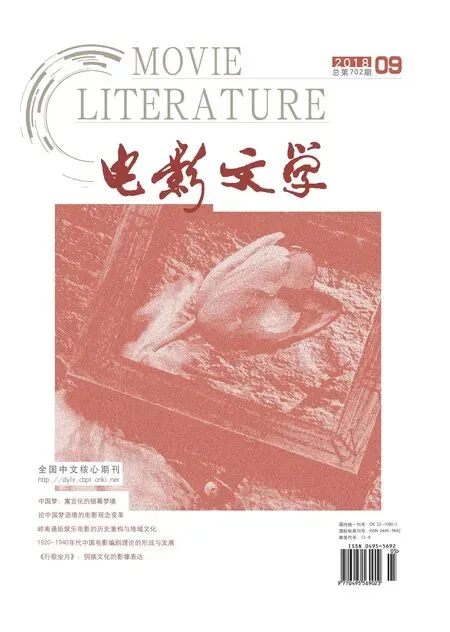《芳華》中否定之否定的新傷痕敘事
干瑞青
(山東政法學院 傳媒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中國內地的傷痕敘事肇始于粉碎“四人幫”之后,主要敘述極“左”政治運動對人的肉體和精神傷害。由于創傷涉及領域廣泛,戰爭、災難、倫理等都可能產生創傷記憶,這使得傷痕敘事空間不斷拓殖。馮小剛導演就是一名擅長傷痕敘事的導演,《集結號》中的英雄傷痕、《一九四二》中的歷史傷痕、《唐山大地震》中的親情傷痕、《我不是潘金蓮》中的制度傷痕等。近期上映的《芳華》則展現了一種雜糅的新傷痕,這種新傷痕有關青春成長,因為“有關青春、青少年和青春期成長的問題是人類文化精神層面的問題,它是歷史性文化的存在”。但作品在暴露傷痕,進行創傷傾訴中雜糅了青春成長中的愛情、追求、理想,更可貴的是這種新傷痕在“肯定—否定”的循環中完成了一個時代的隱語。
一、愛情傷痕中的否定之否定
《芳華》中設定了三對愛情關系,蕭穗子追求陳燦,而陳燦和郝淑雯卻成了夫妻;劉峰追求林丁丁,卻最終因觸摸事件被調離;何小萍一直關注著劉峰,他們最后在相依相偎中變老。其實,這三對愛情關系是在黑格爾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展開的,愛情被時代默許,不代表被承認,但真正的愛情最終會戰勝一切障礙。
(一)被肯定或默許的愛情
愛情在部隊文工團中是一種自我成長、自我展開的存在,沒有任何人阻止或壓制。《芳華》中的領導或權威人物,無論政委還是分隊長都沒有對其中的愛情進行任何染指,它只在戰友間默默進行,這種肯定行為造成人物關系的平衡狀態。蕭穗子看著陳燦,郝淑雯調侃說:“(他)配不上你”,其中蘊含的隱語是在那個時代愛情或暗戀是可以被公開、被肯定的。在接下來的敘述中,攝影干事在角落里偷吻林丁丁、劉峰向林丁丁表白、蕭穗子給陳燦的情書,都證明了青春愛情不限于單相思,男女之間親密的行為或舉止是被默許的,即使愛情沖動也是可以被理解的。另外,腰部受傷的劉峰為了能夠繼續默默的守護林丁丁,守護自己那欲言又止的、無私的愛情,寧可放棄了人人都想要獲得的,到大學進修的集會,更是從另一個角度和側面反映了那個時代和環境下愛情的魄力和勇氣。
(二)被否定的愛情
否定是對肯定的一種改變,是推動事物發展的一種動力。從敘事的角度看,否定構成了沖突,表現為對人物或行為的一種拒斥或打壓,造成人物關系的失衡。影片中的愛情又是被否定的,保衛處對劉峰的審問充斥著階級斗爭話語,流氓、下流等臺詞是對當時愛情的一種定義;像劉峰這樣的好人是一個雷鋒式的人物,是大家的道德楷模,是被模仿的對象。以蕭穗子的旁白為證,劉峰只能是一個干盡好事、占盡美德的人、一個一點人間煙火味也沒有的人。他怎么可以談戀愛、追求女孩子?因之劉峰讓林丁丁感到驚悚、惡心、辜負和幻滅。其實是對劉峰愛的能力的一種否定,是“文革”道德話語對那個時代愛情行為的一種否定。蕭穗子真摯的付出沒有換來愛情。陳燦與郝淑雯的戀愛其實埋伏著門當戶對的隱語,因為他倆都是軍區高干子弟,這也是對自由戀愛的一種否定。因此,階級斗爭的時代背景、扭曲的“文革”道德話語以及門第觀念使得被否定的愛情傷痕累累。
(三)否定之否定的愛情
在黑格爾的學說中,事物經歷了一次否定后走向了否定之否定,實現再一次的否定,使得事物發生質變。在敘事中,對前一次否定的再否定就是對前一個矛盾沖突的否定,從而實現人物關系的再平衡。多年后,恢復健康的何小萍向劉峰訴說著隱藏十多年的話:“能抱抱我嗎?”是對那個年代被否定的愛情話語的否定,對扭曲愛情言行的一種否定,更是對否定活雷鋒式人物劉峰愛情行為的一次否定。郝淑雯來看蕭穗子,她和陳燦已經有了愛情的結晶兒子豆豆;林丁丁嫁到了澳洲,蕭穗子在2016年為孩子舉辦婚禮等,這些都證明她們擁有了屬于自己的愛情。
《芳華》中的愛情經歷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雖然曾被扭曲和傷害,青春與年華的美好消逝了,但留給觀眾的是一種成熟和穩重,這也許是影片所要揭示的愛情本質。《芳華》中的愛情是一種青春萌動的體現,不是一種生離死別的山盟海誓,也沒有對極左行徑的控訴,因此它是一種新傷痕,讓人緬懷,而不是痛徹心扉。
二、被傷害的理想中的否定之否定
“理想是個體依據客觀現實條件對未來美好狀態期望的心理狀態”,理想對人的生活具有引領和激勵價值。影片中被傷害的理想主要包含藝術理想和生活理想。藝術理想主要體現在何小萍對舞蹈的藝術追求;生活理想既有何小萍對部隊生活的期待,也有劉峰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但正如否定之否定規律中的否定是自我否定,事物發展的動力是因為本身存在否定因素。同樣,敘事中人物內心沖突能夠導致情節新的走向。何小萍與劉峰都是在內心沖突的推動下改變了自己的生活軌跡。
(一)何小萍曲折的舞蹈之路
逃離了家庭鄙視的何小萍參加了文工團。入伍的第一天,分隊長要求她做幾個動作給大家看一下,她興奮地開始空翻,即使平轉時摔倒也努力爭取表現的機會;雨夜,何小萍自己在努力地練功,折腰、平轉的畫面不僅是她刻苦的表現,更是對舞蹈藝術的強烈愛好的體現。即使面對眾多戰友的嘲諷,何小萍和劉峰依然在默默地練習舞蹈動作。何小萍的刻苦、忍耐隱含著她對自己舞蹈才藝的肯定。可是,當她拒絕出演草原民兵小戰士時,又表現出對舞蹈之路的否定。頭疼、掉包體溫計等都是何小萍拒絕為文工團服務的掩飾,她以放棄藝術理想來抗議。從肯定到否定,何小萍經歷強烈的內心掙扎,可即使有了精神疾患,她也沒有放棄舞蹈夢想,在空曠的草坪上獨自翩翩起舞,欣慰的表情應是她舞蹈生涯的再生。在大量的傷痕文藝作品中,我們看到主角在藝術理想追求中的一種不舍和被迫,各種阻礙力量斬斷了他們的藝術生活。然而,《芳華》中何小萍是主動地放棄,通過放棄表明一種反抗,這是新傷痕敘事一種的體現。
(二)何小萍的生活理想
何小萍兩次主動敬禮、可以天天洗澡、當兵太幸福了、偷偷借用林丁丁軍服拍照都表現她對軍營生活滿滿的期待;撕毀的軍裝照、巡演的經歷和對舞蹈角色的拒絕也折射出何小萍對軍營生活熱情的降低;野戰醫院搶救傷員使她成為英雄,但強烈的刺激造成的疾患把她隔離在了精神病院。何小萍的生活理想中包含慈祥的父親、幸福的軍營生活,可是父親去世了,她也成了精神病人。因此,影片肯定的是一個姑娘對幸福生活的追求,軍營的經歷又否定了這種生活理想,片尾何小萍與劉峰依偎在長條凳上是對軍營生活美好的追憶,畢竟他們在軍營中相知相伴過。傷痕文藝作品中,大多角色命運坎坷,物質的匱乏,尤其是戰爭、社會動亂或他人造成的身體或精神殘疾給主角造成了極大的生活困難。因此,血淚式控訴成為煽情的主要手段,而《芳華》中何小萍的精神疾患是緣于榮譽或英雄的稱號的刺激,這也成為新傷痕敘事的一個特點。
(三)劉峰的生活理想
劉峰的生活狀態是做文工團的“萬金油”,也是他的生活理想。廚師班的豬跑了,第一個要幫忙的是他;每次從北京回來,給每個人捎帶物品;他是文工團的修理工;他可以幫新婚夫婦打制沙發……他的生活理想是踏踏實實地為文工團服務,做一個雷鋒式的人物,可是觸摸事件使他被下放到伐木連。當劉峰離開文工團時,他告訴何小萍把印有“全軍學雷鋒標兵獎”的皮包和眾多的獎狀都扔掉時,而且用“印上字了怎么用”“難看”等形容這些獎品,其實質是對以前雷鋒式生活的一種否定。可是影片又以戰爭的方式恢復了劉峰的萬金油角色,他帶領部隊的任務是保護馱隊的安全,給前線部隊運送彈藥。即使身受重傷,他依然選擇留下來守護戰友的遺體。因此,劉峰的生活理想就是踏踏實實、安安穩穩地生活,無論是文工團的修理工作,抑或被稱為活雷鋒,還是戰爭的后勤保障,即使有過放棄,他都默默地承擔著。與傳統傷痕敘事中主要角色背負的宏大生活理想相比,劉峰的生活理想是那么簡單、普通,雖有活雷鋒的時代話語的命名,但劉峰可以放棄,這不是對時代話語的一種完全否定,而是對時代責任的更清晰的一種認定。如畫外音所述,他犧牲了,才可能被寫成一個英雄的故事……劉峰作為一個普通人,他只是偶然承擔了一項重任,在時代賦予的責任中夾雜更多的是一種個人化的理想。因此,新傷痕敘事中角色缺乏艱辛、困苦,缺少了那種苦大仇深的悲情,他們只是努力地生活著,沒有更多的苦澀可以渲染,只有更多的堅強和奮斗。
三、幽微人性的否定之否定
《芳華》小說的原名為《你觸摸了我》,“觸摸”這個詞直接點名人性的否定之否定的真核,因為“在這個詞背后,我們似乎能夠讀出經由肌膚碰觸而帶來戰栗、觸及靈魂的溝通、深入內心的連接……”影片角色之間的關系中都有觸摸的行為,尤其是核心情節“軍裝事件”“觸摸事件”中的觸摸行為直接推動了情節發展。影片中的觸摸在肯定與否定的循環中直指人性的幽微。
(一)集體嘲笑下的人性消失
人性主要指的是人的道德屬性,具有道德價值的人才可以稱之為人。孟子在《孟子·公孫丑上》中對人的道德價值觀進行了定義,即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芳華》中文工團的大部分成員都缺少惻隱之心和是非之心,他們對何小萍及劉峰的一次次的嘲笑表明了人性的消失。
首先,嘲笑何小萍身上的“臭”。郝淑雯形容她“身上餿的像從泔水缸里撈出來似的”;某男兵用“你聞聞那軍裝有沒有臭味,不就知道是不是她偷的了嗎”來定義何小萍;朱克以何小萍身上的“餿味”為托詞拒絕為之伴舞;朱克用“臭活”來命名劉峰幫何小萍練舞的行為。他們以集體狂歡的形式嘲笑著何小萍。其次,被嘲笑的隱私。一件帶有海綿的女性襯衫成為引發文工團群體嘲諷的由頭,不要臉、女兵的敗類、假大空等侮辱性詞匯成為他們肆意調侃別人隱私的明證。為了證明何小萍是“假大空”,她們竟然動手搜身,以集體的威勢侵犯著何小萍的尊嚴。文工團集體對何小萍的嘲笑成為一種人格的侮辱,他們沒有對何小萍有過任何的憐憫或惻隱,或給予一個孤獨無助的農村姑娘關懷和慰藉。也許,影片敘事中的隱語是動亂年代對人性的摧毀,甚至是對人性的弱點一種揭示,只是在那個時代更放肆一些。
(二)風雨洗禮中的人性
文工團集體中幽暗的人性讓人感覺寒冷是一種否定,然而林丁丁對《英雄贊歌》的深情歌唱似乎是對負傷的劉峰的一種贊頌,也是對其污蔑劉峰行為的一次否定。尤其當文工團被解散時《駝鈴》的合唱又在進行一種傳統的贊揚和肯定,“一樣分別兩樣情,戰友啊戰友,親愛的弟兄,當心夜半,北風寒,一路多保重”的歌詞才能激發大家對文工團是一個家的認同,戰友的情誼才能被認可。可是,這種肯定中沒有他們的戰友劉峰、何小萍的位置。多年后,面對被城管毆打的劉峰,郝淑雯的國罵才真正實現了一種人性的復歸,是對戰友之情的切身體認,完成了影片中人性的否定之否定。《芳華》中延續了傷痕文藝作品中敘事設置,只是把施暴者由政治機構或掌權者變成了受害者存在的群體,加害的行徑變成了言語戕害,雖有人體的侵犯但有所節制。但是影片卻突破了傷痕敘述的邏輯,拋棄了邪惡與正義,更深層次地分析了人性的困境。
四、結 語
影片《芳華》的導演馮小剛試圖擺脫一種集體化的政治敘述。文工團中女兵裸露的軀體和柔美的身姿在消解革命舞蹈中的嚴肅和莊重,《繡金匾》的歌唱中缺失了對領袖的緬懷,這些體現了導演在努力抽空集體語境中的政治話語。另外,文工團群體確實成為一個空泛的符號,無論政委還是分隊長都沒有給予孤單的何小萍任何溫暖,即使面對裝病的何小萍,政委在慰問演出結束后馬上把何小萍處理到野戰醫院,這是對權力話語的嘲諷,也是對集體主義話語的否定。影片似乎在歌頌那樣一個物質匱乏的時代,文工團除了排練和慰問演出,沒有沉浸于又紅又專的階級斗爭的旋渦中,他們的愛情糾葛則成為敘述的主題。因此,導演在試圖用現代話語去勾勒那個青春的時代語境,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循環中講述著愛情、生活、理想,試圖去完成一種社會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