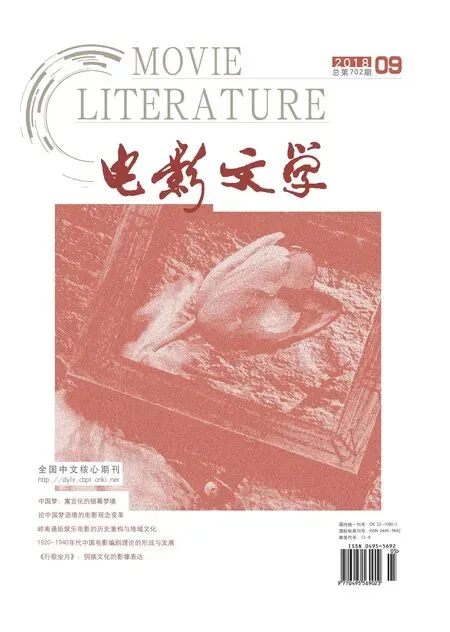電影《芳華》的時代美學意蘊
王 瑜
(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吉林 長春 130000)
電影《芳華》從回憶中講述著歷史,雖然以小人物的命運起伏為線索,但其敘述的卻是時代的青春和蒼茫,而非只屬于個人的記憶。從紅樓到南疆炮火再到改革前沿和那一排排肅穆的墓碑,詮釋的主旋律簡單又復雜,簡單為聽從時代召喚的信仰,復雜到人性深處的“理想”。馮小剛通過嚴歌苓的敘述用個人的反思檢討著時代背景的遺憾,反省人性蒼涼如水,頌揚愛就是單純的一次時間停頓。劉峰的愛停頓在紅沙發前那單純目光,何小萍的愛停在陽光下劉峰那一箱單純的履歷上,而蕭穗子的愛停停走走,有青春張揚的笑容,也有人到中年的一笑而過。幾個簡單的人物歷史,構筑復雜的社會生活,讓人們一遍遍反思,時間都去了哪里?我們度過的好時光究竟有多好?
一、《芳華》中時代背景下的敘事結構美
嚴歌苓的《芳華》是一個毛線團,蕭穗子用她的方式抽出線頭;馮小剛的《芳華》把這個毛線團解開,且剪成三段:一段捏在蕭穗子的手里,一段捏在何小萍和劉峰手里,另一段扔給觀眾和不斷出現的畫外音。畫外音不是蕭穗子,而是蕭穗子的靈魂游走在40年的光陰里踩出的回音。雙主角的使用雖然使得影片出現了過多的支線,卻把宏大的集體主義敘事分解為個人主義敘事單元,在畫外音的支撐下,敘事現場顯得更加真實。
《芳華》敘事結構的繁復性呈現和零距離情感再現的釋放,呈現兩個字——善良。嚴歌苓的《芳華》沒有回避她所書寫時代的假惡丑,而馮小剛也沒有在敘事結構中回避真善美。電影《芳華》的內核還是嚴歌苓的,但因為敘事結構的不同而呈現出來的對時代記憶的理解有了分歧,電影《芳華》更多的是用個人記憶烘托集體主義的美好,排斥以往經驗中對集體主義回憶的假大空,文工團里并不都是虛偽情感的聚集地,這在文工團解散的那天和郝淑雯為劉峰在海口的那一聲怒吼中已經得到了驗證,尤其是政委對于何小萍慰問演出后的安排上,集體主義中也有美好的私人情感的柔軟性。
三重敘事結構呈現的是過去時、現在時和進行時,又具備現實主義青春記憶和超現實主義青春記憶的錯位。每個人的回憶都會有個人主觀判斷的附加性,當很多人的回憶糾結在一起時,回憶就會出現多種情感、情緒錯位而出現回憶真空。《芳華》的畫外音糾正了某些記憶錯位和真空地帶的冥想,就像何小萍在草地上的獨舞,她的記憶就完全是主觀判斷后的結果,那里面有她的理想與現實。《芳華》并不是簡單地用后現代方式解構了現代敘事語境,而是用后現代思維重新建構了現實語境的真實性,從何小萍進入文工團那一天開始,就建構著現實世界人性本善的張力:善良的化身劉峰,雖然在戰場上用蕭穗子的敘述表達著他渴望戰死,但是最后他守著戰友尸體表現出對生命的態度;有善良的、不想傷害任何人的、渴望被集體接受的何小萍,她的善良和劉峰對比又散發出母性的光芒;蕭穗子和郝淑雯的善良有時候很模糊,但是有其自己的善良底線不容觸碰;政委和指導的善良兼具集體主義大家長的庇護和出于對集體主義的負責感;而林丁丁和小芭蕾的善良是自私的,有著各種彈性尺度的對自我的善良。《芳華》的敘事結構支撐著時代的變遷,是懷舊傷懷,是非邏輯性情感的歷史文獻。
二、《芳華》中時代背景下的音韻色彩美
電影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色彩和音樂已經是電影里不能缺少的重要情感支撐的元素。色彩和音樂一個是具象的,一個是抽象的,但都是思想外在的敘事方式。《芳華》是個體青春對集體青春以及還原個體青春的記憶,雖然是回憶式的敘述,但記憶沒有長短和時間界限的疊加性滿足《芳華》飽滿、亮麗的色調和純情音樂的成功條件。
大塊的統一色調為《芳華》的紅樓和集體記憶的青春提供了厚重的歷史感,卻有別于“文革”時代的背景色,是印象派對記憶不添加濾鏡的視覺還原。文工團在“文革”時代具有烏托邦式的象征地位,那些正值芳華的女團員們在排練廳展示出來的舞姿,給那個時代注入了柔美的一面。文工團門口影墻上偉人和背景的紅旗凸顯出時代特色,紅得熱烈、激揚,暗喻了戰場上劉峰等的帽徽和領章在鮮血的洗禮下厚重的思想來源背景,而那種黃色溫暖和諧,與影片結尾劉峰和何小萍依偎在一起時已經褪色的黃顏色疊加出歷史的蒼茫感,以及魂有所依的夕陽無限好。青春的萌動和中年的成熟,在紅黃兩色的使用上給觀眾帶來心靈的安慰,也是馮小剛對青春的交代。馮小剛對文工團的記憶是溫暖的,滿懷向往的,所以《芳華》里的色彩針對“文革”就顯得美得離譜。在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年代,湖畔以及樹林還有音樂是充滿了資產階級味道的事物,但文工團明顯是個例外,即使去高山哨所慰問演出,雪山白也是印象派純潔的化身,雖然有何小萍被文工團舍棄到野戰醫院,卻滿足了何小萍逃避虛偽現實的理想,這種白冷,冷得銜接出戰爭和紅得刺眼的鮮血。電影在這里一分為二,前面的理想主義幻滅了,隨之而來的是更加殘酷的現實。
文工團自然少不了吹拉彈唱,唱的、彈的都是那個年代的主旋律,卻與印象中的“文革”時代有區別,《芳華》里的音樂多了一絲人情味,當何小萍在草地上翩然起舞時,這部戲充滿了理想與現實交織的五味雜陳,里面有大多數人的夢和不能實現的現實,美得讓人心碎的痛,與何小萍初到文工團沐浴時的心態截然不同,陽光燦爛的日子也有悲涼,冰冷的月光也會充滿溫情。《草原女民兵》《駝鈴》、影片結尾的《絨花》不是煽情卻在諸多肢體語言和天籟般的音樂下,把天地煽得動容變色,是時代記憶的寬慰,也是時代記憶的悲涼,當影片中劉峰在海口與蕭穗子和郝淑雯重逢在書店時,劉峰重返“文革”的衣著色調與所處時代又形成了二元對立的沖突,當郝淑雯一句粗口爆出的時候,他們的魂又回到了文工團的紅樓:“世上有朵美麗的花,那是青春吐芳華。錚錚硬骨綻花開,滴滴鮮血染紅它。”何小萍站在文工團緊閉的大門外送別劉峰,《送別》的長亭、短亭又是印象派對于悲劇的伏筆,而何小萍的軍禮是她心里最美的舞蹈,已經超越了她渴望的《草原女民兵》中的A角。《芳華》的色彩和音樂充滿了詩情畫意,但在詩情畫意的細節處卻處處展示著情境悖論,優美抒情的音樂背后是人情冷暖,明媚色調的背后是冰冷的現實,這是記憶對回憶的排斥,美得觸目驚心,畫外音是蕭穗子的靈魂,但卻是馮小剛的記憶,他調用了印象派的色調敘事,調用了尼采的日神和酒神的精神:走向內心,期望超越。
三、《芳華》中時代背景下的語言臺詞美
“我們在最好時代虛度光陰,他們在最壞的時代洗盡鉛華。”這是《芳華》的精華所在。而這句臺詞也讓人聯想起保爾那句:“……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嚴歌苓用她女性的柔美鍛造出《芳華》的臺詞,貼近生活本身,又在生活的繁復拖墜中提煉著不帶煙火氣息的詞語珠鏈。《芳華》用蕭穗子的眼睛作為鏡頭,用她的口吻講述著40年的歷史。她同情何小萍,并且用帶著失落傷感又略帶崇拜的口吻講述著劉峰,講述中,她既是旁觀者又是參與者:從不需要想起,也從來不會忘記。是的,這就是生活的本來面目,記憶沒有長短也沒有時間限制,它是潛意識里最真誠的正在休眠的人生。
紅樓里的人生有諸多蒼涼,紅樓外的人生更多了份蒼茫,當劉峰用唯一的手拿起林丁丁的照片,淡淡的一笑,他在文工團對林丁丁的一抱就襯托出“孤單、疲倦和寒冷能使五分鐘變成一輩子”這句話在當時語境下的悲涼。嚴歌苓并沒有煽情,她用近乎殘酷的現實解析著人生,戰斗英雄出自小人物又回到小人物,而精英家庭延續著精英的生活。她并沒有去批判,但通過她的臺詞,已經傳遞出她的社會立場。充滿人生哲理的優美臺詞,反映的現實卻是那么讓人無語,甚至是無助:為何總是對好人苛刻,對壞人寬容?
一代人用他們的芳華演繹著歷史,從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的釋放,40年間,中國大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善良卻還在爍爍發光。當個人被整個集體排斥時,他所經歷的那些故事在以后的時間里,注定會打動很多聽故事人的良心:一個始終不被善待的人,最能識得善良,也最能珍視善良。這就是何小萍為什么會獨自一人送劉峰去伐木連,緊閉的鐵門成為他們離別的背景,這是他們芳華的傷,閉合性的心理創傷,注定了他們的命運走向,合乎時代人性走向,他們互相溫暖了對方,卻用現實把傷感傳遞了出來。《芳華》里的這句臺詞能夠很好地詮釋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和善良:哪怕沒有轟轟烈烈,但有個人時刻在你身邊相依為命,那種長相廝守才是讓人羨慕的神仙眷侶。
四、《芳華》中時代背景下的人性美
《芳華》詮釋了人性在時代背景下的各種表演和展現,表演是個人利益的追求,展現的是對個人情懷的追求,兩種方式在一個背景下產生了二元對立的沖突。似乎這種人性的沖突不可調和,似乎這種沖突貼上了時代產物的標簽。但劉峰的“雷又峰”與何小萍的真誠善良卻突破了時代的束縛,“人之初性本善”貫穿始終。從何小萍踏入文工團大門那一刻開始,她生命中逃離沒有溫情家庭的“人之初”開始了,當她穿上白服那一刻,她的“人之初”有了和劉峰一樣的滄桑之美,而她在草地上的獨舞是她獲得新生命后的“人之初”,與劉峰傷愈踏入文工團宿舍又一次修理地板時的“我本善良”有了異曲同工的意味,當她靠在劉峰的肩膀上,享受著片刻的寧靜時光,她與劉峰之間情感的升華,卻是她回歸到“人之初”的時刻。當蕭穗子的畫外音響起,他們重新聚首的時候,人性在人間的重量有了答案,簡單從容。
“文革”時代的人性是被異化的人性,有它的極端性,戰爭時期的人性最忠實,它忠實著時代人物的內心,改革后的人性同樣是被異化的人性,但都具有時代特色的美丑標準。蕭穗子時時刻刻充當著時代人性的展示者和詮釋者,影片中她沒有主觀上的道德評價,但是畫外音卻做著客觀的陳述,她的美在于她忠實地還原著各個情境,盡力去還原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之間的關系。如果說她的人性異化,那么就在于她在每個時代中扮演的角色都對何小萍和劉峰沒有做主觀上的選邊站。她把她的眼睛和耳朵交給了時代,當郝淑雯的怒吼完成了她的人性芳華之旅后,她的眼睛和耳朵也對落井下石的林丁丁做了道德批判:“用假手都不會摸啊。”
用人性去定義時代是不準確的,用時代去定義人性是殘缺的,什么樣的時代背景,人性都會被異化,歷史如鏡,《芳華》里的政委和指導雖然著墨不多,但他們能夠代表那個時代的部分特征,而政治部的又能代表另一部分,就像戰后經商的劉峰與聯防隊和郝淑雯以及蕭穗子都具備時代性的部分癥候,有美就會有丑,不然就不會有美這個字的產生。那么時代背景下會不會出現第三種、第四種人性?有,一定會有,就像那個16歲的小戰士,他在人間意識中最后的美定格在什么是果丹皮上,如此透明的人性至純至善,卻是在戰爭中展示出來的,這是時間的悖論也是人性的悖論。
五、結 語
馮小剛電影《芳華》所體現的時代文化特性被簡約成個體特質,運用大量鮮艷色彩的服裝、優美的音樂旋律和符合時代特色的舞蹈,在斷裂、矛盾、悖論的電影敘事中釋放更廣闊的美學意蘊空間。同時,結尾柔和,劉峰和何小萍在長椅上的暖暖擁抱,更加突出主旨思想:美好與青春在“善良”中完結一個時代留下“芳華”,這種無法節制的懷舊情緒使得電影本身遠遠超出馮小剛、嚴歌苓本人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