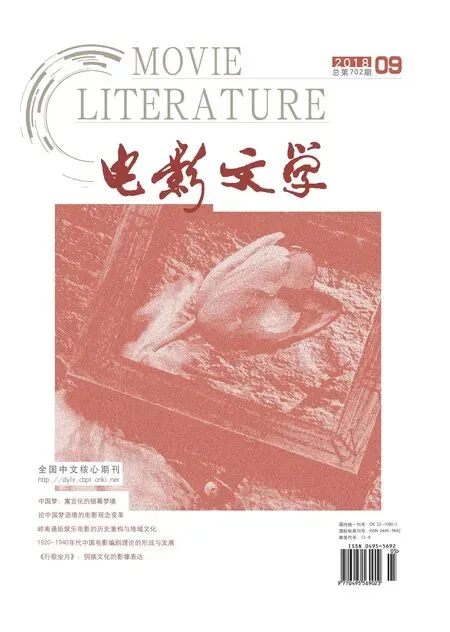《摔跤吧!爸爸》:男性話語下的女性解放
孟智慧
(天津師范大學 文學院,天津 300387;天津理工大學 漢語言文化學院,天津 300384)
曾在印度創下最高票房紀錄的《摔跤吧!爸爸》被引進中國后,在原本不被看好的情況下憑借超高的口碑成功實現了逆襲,成為2017年中國電影票房的“黑馬”。這部電影取材于真人真事,講述曾是全國摔跤冠軍的馬哈維亞為了實現自己的世界冠軍夢想,培養和訓練兩個具有摔跤天賦的女兒,最終使大女兒贏得了寶貴的世界金牌。它不僅是一部成功勵志、鼓舞人心的體育電影,而且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反映了印度當代社會存在的一些問題。其中父親馬哈維亞對女兒的態度則引起了觀眾對于父權和女權的討論:一部分人認為他逼女兒練摔跤是強勢的父權制家長作風;另一部分人則認為他對女兒的培養是出于對女兒深深的愛,讓身為女性地位低下的她們獲得解放。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爭論?筆者認為這與影片采取的敘事方式有一定的關系。
一、沿用傳統的男性敘事方式
與其他敘事藝術一樣,電影在進行敘事時會與某種社會權利結構保持一定的關系,并利用相應的策略和技巧對這種社會結構進行呈現。而社會權利話語結構的呈現,主要通過分配占有人物間不平等的話語權或者剝奪一類人物的話語權來達到的。敘事視點是電影敘事結構的重要支點,“視點、視點鏡頭的占有與否成為話語權的擁有與剝奪的視覺對應物”。《摔跤吧!爸爸》之所以被一些人認為是“男權主義的產物”,就是因為影片在表現主題時體現了男性與女性權力話語的不平等,女性的話語權利被剝奪,無論是敘事視角還是視點鏡頭的占有都是沿用傳統的男性敘事。
《摔跤吧!爸爸》的敘述人是馬哈維亞的侄兒奧姆卡,故事情節以他的第一人稱的方式展開敘述。按照電影敘事學的理論,“當‘我’者敘述人以敘述者和畫內人的雙重身份出現時,攝影機的視點基本上是作為人物的敘述視角出現的”。因此,這部影片的鏡頭視點基本上與敘述人物視角一致。在采訪中,制片人兼主演阿米爾·汗認為《摔跤吧!爸爸》向觀眾傳遞的最為核心的價值觀就是:“女人并不比男人差,男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女人同樣可以。”按照主創方的意圖,這是一部追求性別平等的電影,但影片在敘事視角上并沒有采用兩個女兒中任何一人的女性視角來展開,而是采用男性視角進行敘事。讓一個故事的參與者與旁觀者擔當敘述的功能,表面上看似客觀,但在這樣一部探討女性解放主題的電影中,敘述人的男性身份更具有敏感性。觀眾在影片中看到和聽到的一切基本上是以奧姆卡爾的視角為出發點,盡管這個人物被設定成對女性具有開明態度的新一代印度男性的象征,但敘述過程中仍帶有男性意識的主觀色彩,如他對馬哈維亞訓練女兒態度的潛在認同。而且由于男性敘事視角和第一人稱敘述方式的限制,觀眾看不到身為女性的吉塔和巴比塔的自主意識和主體精神,看不到她們深層的內在世界。她們的形象是在男性敘述者的外部敘述中完成的,兩人處于一種“失語”的狀態,無法自我呈現、自我言說。雖然影片也表現了她們對于父親強權的反抗,但表現浮于面上,并沒有通過女性自己的口來講述自己內在的真實狀態,更何況這種反抗的正確性在男性話語的敘述中很快消解。在男性敘述者看來,如果她們幼時不接受父親摔跤的安排就會落得與早婚的女同學一樣的下場,而長大后不接受父親的訓練方式則會在賽場上屢次失敗。
影片除了采用男性敘事者對女性進行敘述外,更重要的是視點鏡頭的占有主要在男性形象父親身上。“對電影來說,視點不僅呈現在敘事結構中,它同時呈現在電影視覺語言的各要素之中。”從技術層面來講,電影敘事的講述方式主要由視覺因素構成的,一般占據視覺敘事中心的應是影片的主人公,鏡頭視點的設定、攝影機機位的選取、構圖與運動方式應取決于主人公。因此,作為表現主題的關鍵性人物,兩個女兒才應該是《摔跤吧!爸爸》的敘事中心人物,是主人公。但是,就影片的視覺呈現來看,主人公卻是父親馬哈維亞,他占據了大量的視點鏡頭。電影一開始的鏡頭就是父親以壓倒性勝利戰勝本地最有名的摔跤手同事,贏得周圍人的敬佩,其偉岸的形象就建構起來。而后,這種形象通過男性敘述人的敘述延續下來,馬哈維亞完全是敘述的中心,影片用眾多的鏡頭表現他對女兒們的摔跤訓練。在這些鏡頭中,我們看到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兩個女兒,采取幾乎苛刻的手段對她們進行高強度的訓練。雖然是出于女兒前途的考量,但他體現出來的卻是一種絕對的男性權威和父權制的力量。他沒有把女兒作為具有獨立意識的主體來對待,在一定程度上她們只是他進行規訓的客體。而女兒們短暫反抗的失敗,更凸顯了父親形象的正確性。最后吉塔在賽場上拿到了世界冠軍,似乎是女性獲得了勝利,其實還是男性的勝利,因為這樣的成功是在男性——父親的指導下完成的,即便決賽時馬哈維亞缺席,但吉塔決勝的過肩摔仍離不開父親的精心指導。影片最后一幕是吉塔眼含淚水激動地把金牌交到父親手中,結合男性敘述人此時的旁白:“最后叔叔實現了他拿金牌的夢想,那是他10年前許下的諾言”,就更不難看出這場勝利的真正含義——男性夢想的實現。從最開始一幕到最后一幕,影片自始至終都把鏡頭聚焦在父親的身上,女性形象被邊緣化,其主體性被消解。
二、基于印度國情的女性解放
由于《摔跤吧!爸爸》采用傳統的男性敘事方式,忽略了女性自身的主體精神以及自我敘述的可能,按照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標準來看,這并不是一部真正的女性主義電影。但是我們不可否認這是一部反映女性解放、追求性別平等的電影。
談到女性解放、性別平等,應該說在各個國家發展的程度并不均衡。西方發達國家的女性在很多方面幾乎可以享有與男性一樣的權利。女性主義產生于西方,其理論觀點多是表達西方女性對于自身地位的思考和觀察,并不具有一種統一性和普遍性。而且隨著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女性主義內部也“開始質疑是否存在一種統一化的女性和本質化的女性文化,以及統一的平等追求,繼而審視不同女性之間的差異,包括民族差異,以及同一民族內不同的階級、種族、種姓、性別等方面的差異”。因而,在分析這部電影時,就不能完全按照西方女性主義的觀點來進行評判,而是要深入到印度女性的實際狀況來探討電影所具有的意義。
印度是世界上重男輕女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其文化傳統就認為女子天生比男子低劣,印度教的教義和經典就有大量歧視女性的規定:“女子必須幼年從父,成年從夫,夫死從子;女子不得享有自主地位。”在現實生活中,女性的地位遠遠低于男性,女孩一出生就得不到社會的認可,“嫁妝制”“童婚制”“薩蒂制”更是壓在印度女性身上的沉重枷鎖。雖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印度現代女性的地位逐漸得到了提高,但受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和男尊女卑傳統觀念的影響,印度女性仍是弱勢群體,經濟和社會地位低下,在很多方面仍不能實現與男性完全一樣的平等,特別在傳統觀念強大的農村地區,生育女孩仍被視為恥辱的事情,虐殺女嬰的現象屢見不鮮,更不要說讓女性享有其他的權利。
受這種男尊女卑的觀念影響,以女性為主人公,探討女性地位和性別平等的電影在印度并不多見。印度很多電影按照傳統觀念對女性的規范來塑造女性形象,被贊美的女性往往具有自我犧牲、自我奉獻的精神,她們結婚后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囿于家庭生活之中,成為賢妻良母。而《摔跤吧!爸爸》對女性的塑造并不是這樣程式化,明顯體現出對女性的尊重和對印度女性如何改變地位低下命運的思考。
《摔跤吧!爸爸》的故事發生在印度北部的一個偏僻的農村,在那里重男輕女的思想依然強大,這從全村人獻計獻策為父親謀劃生男孩的情節中可見一斑。而從充滿輕松、幽默的獻策生子的鏡頭,不難看出主創方對于這種重男輕女觀念的諷刺與揶揄。影片也借助父親馬哈維亞這一形象,表達出對女性的一些尊重與理解。雖然馬哈維亞因為沒有兒子來實現夢想顯得有些失落,但面對為此愧疚的妻子卻說:“這不怪你,你也不要感到內疚,我都很愛她們。”從這句話,我們看到了他并像其他男性那樣把生女孩的責任歸咎到女性身上,也沒有因為女兒不是男孩而進行歧視。雖然在他身上還存在一些父權意識,但他對女性的尊重和男女平等意識,是周圍許多印度男性不具備的。當妻子擔心女兒們因練摔跤而沒人娶時,他卻認為自己將培養出非常偉大的女兒,“他們沒有資格來挑選我女兒,而是我女兒來挑選他們”。
馬哈維亞讓女兒們練習摔跤,既是為了圓自己的世界冠軍夢,又是出于對女兒的地位、前途的思考,更是對傳統男權觀念的一種突破。按照印度傳統觀念,摔跤是只有男性才能從事的運動,與女性似乎無緣,因為印度女性主要的活動范圍是家庭,做好家務才是她們的本職工作。馬哈維亞在看到兩個女兒因打架而表現出來的摔跤天賦時,毅然決定訓練她們,這在男尊女卑觀念強大的印度農村簡直不可思議,因而遭到村民們的冷嘲熱諷。但他的這一決定,卻是作為女性的兩個女兒邁向解放最關鍵的一步,她們從此擺脫了繁重的家務勞動和像女同學那樣早婚的命運,在摔跤中找到了自己的尊嚴和價值,成為能夠主宰自己命運的職業女性。而女性從事摔跤運動,對顛覆傳統的男權意識更具有一種深層意義:女性不比男性差,甚至還要比男性做得更好。電影中多次出現大女兒吉塔打敗男摔跤手的鏡頭就有這層含義。特別是吉塔為印度獲得了第一枚世界級摔跤金牌,就代表了女性從私人領域進入了公共領域——國家層面。“由于民族主義和國家一般被當作公共領域的一部分,而女性又是被排斥在公共領域之外的,也使她們被排斥在民族主義和國家這些話語之外。”而吉塔的奪冠,就代表了女性不只是圍著家庭轉的妻子、母親,她可以像男子那樣甚至超越男子成為國家的象征。就像父親所說的,吉塔在賽場上不僅是在與對手作戰,還是與所有歧視女性的人作戰,而她的勝利也將使很多印度女孩以她為榜樣,一起反抗那些性別歧視的人。影片也展示了這種女性榜樣的力量,在千里迢迢來看吉塔比賽的家鄉小女孩身上,我們便看到了印度下一代女性崛起的希望。這也是影片所要表達的積極意義。
三、結 語
綜上所述, 在《摔跤吧!爸爸》中,由于采用男性的敘事視角以及男性角色對視點鏡頭的絕對占有,使女性無法進行自我表述,成為具有主體意識的個體,容易導致觀眾給這部作品貼上男權主義或父權主義的標簽;但是,如果結合印度的文化傳統和現實中印度女性的實際狀況,我們也應該看到影片通過父親對女兒的培養和訓練背后所要表達的女性解放的進步主張,這樣就不會拿著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對其進行苛責,就會有更多一些的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