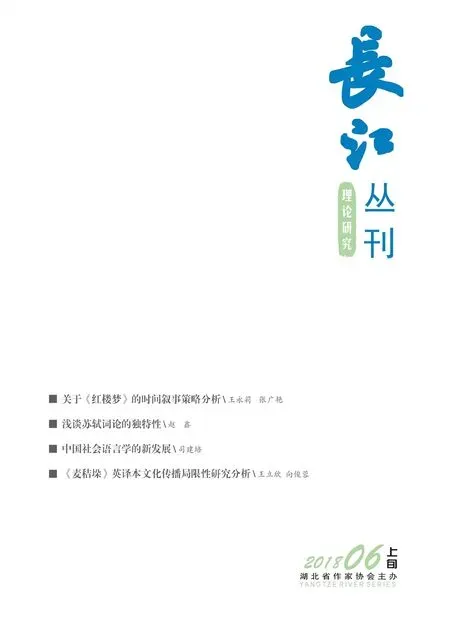對內地媒介批評理論研究的再思考
■/
重慶大學
一、前言
中國內地學術界開始對“媒介批評”領域展開學術研究,至今已有20年歷史。以“媒介批評”為關鍵詞,在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中搜索可得到相關論文共90篇,時間跨度從1998年至2016年5月。
一方面,內地媒介批評發展已呈不容忽視之勢,但另一方面,在當下內地媒介批評表面熱鬧的背后,除部分問題(如媒介批評的歷史緣起)已有學者進行過仔細考究外,還有更多的問題并未得到澄清。
二、媒介批評理論研究的主要爭議及回應
就內地媒介批評的基本理論研究而言,在媒介批評的定義、批評對象、批評主體等基本理論問題上均未達成基本的學術共識。
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視角,運用不同的理論、方法觀察媒介批評現象,研究媒介批評問題,提出了各自有關媒介批評的定義。但統而觀之,現有定義大都突出了大眾媒介,并肯定媒介批評為一種價值判斷活動。但又在媒介批評主體即展開對象方面甚至存在著較大分歧。實際上,批評主體及媒介批評的對象也有不同學者表達過不同看法。除此之外,關于媒介批評的對象如何界定,以及如何界定,學術界也頗具爭議。
本文認為學界關于媒介批評定義、主體及批評對象定位展開的討論,反映的是不同學者的作為一種反思性的活動,媒介批評諸多爭議的背后其實各學者是關于社會生態、媒介生態的不同設計。而若要做好這種設計規劃,是須要從媒介現實出發的,關注當下媒介及社會問題。因此,本文將不采用“本質主義”的方式,對已有定義進行邏輯上修正,而是從時代語境出發,探索媒介批評理論研究的可能路徑。
三、媒介批評理論研究的時代語境:媒介化、社會轉型、全球化
從國外看,媒介批評實踐既是美國新聞媒體所恪守的專業主義的重要形成因素,但又因專業主義而遭受挫折。至今,不少聲音還會以“不客觀”、“不專業”來表達對媒體行為的意見。這種情況在內地媒介批評的醞釀與生發階段也可窺見。但自始至今,媒介批評始終導向一種秩序,更加科學的媒介批評則作為一種話語實踐既可以產生振聾發聵的效果,也有可能推動社會及媒體的認同,倒逼媒體甚至社會主動調整或進行改革。這恰是倡導學理性媒介批評的原因所在。
理論對媒介批評實踐的獨特作用已得到大部分學者的贊同,但當由此出發重新審視內地媒介批評關于基本理論的研究時,可發現其理論資源的相對匱乏。一方面,已有學者對西方媒介批評的具體理論進行過深入引進和介紹。但同時,由于國情以及媒介、社會輿論環境的差異,更由于時代背景的不同,這些理論的適用性值得重新商榷。
與以往相比,中國社會及媒介生態變得尤為復雜。老問題尚未解決,就又迎來了由市場經濟帶來的傳播理念與全球化及新媒介技術帶來的新問題,媒介批評理論的滯后顯而易見。在此語境下,本文認為內地媒介批評研究有必要且有使命加強對基礎理論的探討,面對紛繁復雜變化多端的中國社會,從追求“真”開始,進而上升到對“善與美”的要求。
四、媒介批評理論建構的三條路徑
(1)從歷史研究中獲取思想養分。如李紅提出老子思想中的自然主義思想、“自然無為思想”以及女性主義傾向,便是珍貴的思想資源。從現實出發關照歷史,尤其是中國傳統歷史,即便可能面臨過于強調人文精神而忽略科學性的質疑,但在思想資源相對匱乏的當下,仍是一條必經的探索之路。
(2)挖掘曾被忽視的理論資源。如,除“公共領域”外,哈貝馬斯所提出的“溝通理性”概念對于思考檢驗當代媒介同樣具有價值。在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之外,哈貝馬斯大膽假設存在“溝通理想”。他認為任何一項成功有效的溝通行為均需滿足4項有效聲稱。而這一思想亦可用于指導媒體實踐。
(3)對媒體格局做理論設想。與另外兩條路徑相比,設想媒體格局或發展是對當今媒介之于個人,之于國家,之于社會的重新定位。這并非單純的文本分析或現成理論的直接運用,其本質是對現代問題的直接解構,因此,這一路徑可能具有更具探索價值,即更具建設性。發展新聞學與發展傳播學或為媒介批評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思考方式。當然,不論是發展傳播學還是發展新聞學,都與得到認可的“社會公器”、“客觀”的媒介定位有著明顯矛盾。而兩種理論哪種更具適用性,還需要更多的理論探討及實踐檢驗。簡言之,中國社會的復雜性日益凸顯,致使越有建設性的媒介批評可能價值也會愈高。在一切混沌、共識尚未達成之時,不妨先立再破。
:
[1]劉建明.西方媒介批評的流派[J].當代傳播,2012(01):64~66,70.
[2]董天策,胡丹.中國內地媒介批評論著十年掃描[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版),2011(02):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