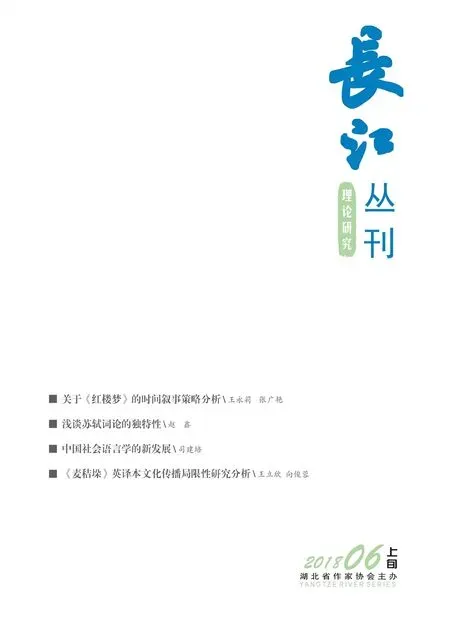公共事件中網絡輿論的理性回歸
■ /
江蘇大學
一、公共事件與網絡輿論
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開啟了信息交流傳播的新時代。網絡給公共事件帶來了一個開放的傳播平臺的同時,也給網絡輿論的極端化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所謂公共事件就是指大范圍的、群體性的、在社會在造成了廣泛影響的事件。不久前,紅黃藍事件一度成為熱搜。一些家長上傳了孩子被針扎的照片,說幼兒園老師虐待兒童,同時衍生出院長伙同“老虎團”性侵兒童的事件。將矛頭指向了幼兒園和政府,一時間鋪天蓋地的網絡輿論撲面而來。那究竟何為網絡輿論?網絡輿論即社會上的特定群體(網民)以網絡為平臺,針對某一特定事件所表達的有一定影響力、具有傾向性的意見。
二、網絡輿論極端化現象及成因
網絡輿論為何會極端化呢?我們通過查閱大量文獻發現網絡輿論極端化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相關法律機制不夠完善。網絡交流平臺具有匿名性、虛擬性、開放性,多元性、草根性等特點。它是一個大眾平臺,任何人、任何組織都可以在這樣一個虛擬的空間盡情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因為太過讓人“盡情”,同時相關法律也不夠全面,網絡環境因而越來越難以控制。長此以往,終將推動網絡實名制的到來。
第二,網絡媒體引導不當。網絡媒體不斷地追逐利益,而利益的關鍵在于網民。為此,一些網站媒體使出渾身解數去迎合網民大眾的獵奇需求,因而在各種媒體平臺上都充斥著“明星緋聞”等各種不實報道。不僅如此,對于一些類似“紅黃藍”等的公共事件,媒體在未有證據的情況下,就發表帶有傾向性的言論,將大眾往錯誤的方向引導,引發群眾的關注,從而賺取所謂的“流量”。
第三,網民自身的認知偏差。凱斯·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一書中曾提到過這樣一個詞“群體極化”,他認為:群體成員一開始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簡單來說就是,人是一種會產生偏見,擁護偏見的動物。當我們接收到的新事物與我們原本的認知不相符時,我們的第一選擇是拒絕它,或者是扭曲它以適應我們原本的認知。而在網絡上,我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信息,發表自己認同的觀點,這樣兩種情況結合起來時,就形成了不同的認知群體,各個群體“同仇敵愾”,漸漸演變成“群體極化”的局面。
三、網絡輿論的對策
我們綜合各方面的因素,針對網絡輿論,得出以下對策:
第一,建立健全相關法律體系。首先,政府要有一定的法律,確保網民有法可依,依法管網是依法治國的組成部分之一且必須要有“法”可依。我國目前有關網絡輿論的法律的不完善造成了一些人打擦邊球的行為。政府需要將法律變得更具防范性。政府在規范我國公民網絡參與秩序的同時,既要保障網民自由言論的權利,又要管制那些影響網絡風氣的網民,從而創建良好的網絡環境。
第二,適當引導網絡媒體。政府可以在該領域,建立優秀的網絡輿論領袖組織,引入非政府組織參與網絡輿論管理。政府需要一支專業的“網絡輿論發言人“,面對熱點事件能及時回應,堅定政治立場;能及時發布權威信息,避免虛假信息的傳播。在輿論事件中占據主導,不讓其他為博眼球的媒體搶占上風。
第三,提高網民及網絡媒體從業人員素質。一方面是上文所說的通過法律來管理網民,一方面是要加強網絡道德倫理教育。通過一些正能量文章或影片,加強我國網民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意識,避免在平時的網絡輿論中出現不當言行的行為。同時也要加強對網絡媒體從業人員的培訓,加強對網民的管理,必要時制止一些網民的不當行為,凈化網絡環境。
四、結語
輿論是社會意識的一種,也是反映民眾呼喚、感受社會冷暖的“皮膚”。在經濟飛速發展的現代,網絡輿論一直游離在理性與不理性之間,它體現的是公眾對社會公共問題發出的聲音和民意的表達,但是在政府、媒體、網民三者的共同努力之下,終會為社會創造一個良好的輿論環境,并且讓網絡輿論回歸理性。
:
[1]張志安,晏齊宏.網絡輿論的概念認知、分析層次與引導策略[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6(05):20~29.
[2]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M].王維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
[3]左丹.網絡輿論對政府行為的影響及對策研究[D].長春:長春工業大學,2017.
[4]Noelle-Neumann E.The Spiral of Silence: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6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