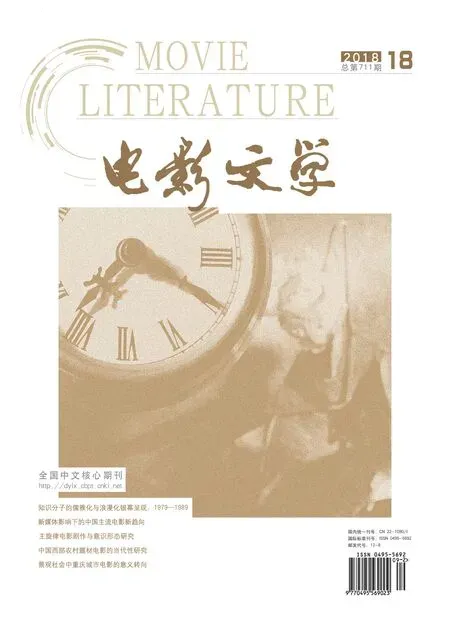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經典文本—影像表達”創作間縫隙
——以《東方快車謀殺案》小說與電影為例
田嘉輝
(上海戲劇學院,上海 200040)
蘇珊·朗格認為藝術是人類情感符號的創造,卡希爾說人是符號的動物。“審美經驗則是無可比擬地豐富,它孕育著在普通感覺經驗中永遠不可能實現的無限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成了現實性:它們被顯露出來并且有了明確的形態,展示事物各個方面的這種不可窮盡性就是藝術的最大特權之一和最強的魅力之一。”經典藝術的文學性與其擱淺案頭悅目,不如以具有獨特生命感的藝術樣式,懷著“小心翼翼”的情愫再詮釋與演繹,得其別樣的審美體驗,延伸與最后完成藝術本體文學性的審美形式的表達。審美具有持久無限延展的跳動靈性,藝術家對其時代風貌的生命疤痕與情感漩渦以獨特藝術方式表達,貫穿、交織與凝聚于這一個充滿巨大能量與力量的支點所處的縫隙空間,探索其內,生發出情感交融的無窮盡性的意蘊呈現,不同創作者探索同一部作品的創作欲望盡可能賦予個人審美色彩。《東方列車謀殺案》(下文簡稱《東快》)是以赫爾克里·波洛偵探為中心人物的系列小說之一,與日本松本清張和英國阿瑟·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不同,在日常生活推理過程中注重人性直覺表達與理性思考,具有深刻的人文現實內涵,以“謀殺案”敘事解構、戲劇性品質及“復仇”中解讀人性,探索小說到同名改編創作的更多可能性與審美意義。
一、“謀殺案”敘事的解構
小說或劇作的核心是故事結構,結構(Struct)將某些東西集結在一起,整體與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羅伯特·麥基認為結構是對人物生活故事中一系列事件的選擇,這種選擇將事件合成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序列,以激發特定而具體的情感,并表達一種特定而具體的人生觀。解構(Deconstruction)譯為解構主義,一種文本閱讀方法,雅克·德里達關于整體論的結構主義使用“解構”,摧毀、拆解傳統認知模式、閱讀方式與習慣等。“最突出的是它常用于文本閱讀模式,是一種可以在理論層面上用于任何學科和文化產品的方法。”解構是一種具有曖昧性與復雜性的內涵進行“解讀”(Interpretation)與“建構”(Construction)藝術審美理念與實踐方法。創作者在原藝術本體敘事結構基礎上進行多樣性解讀,撕毀或尊重原著精神內核,建構獨特審美樣式表達其創作風格與理念。
(一)藝術創作是賦予生活自然形態以鮮活生命感的情感外化形式
阿加莎根據1929年威尼斯辛普朗東方快車曾被大雪困住若干天的一個真實事件;另一個1932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命名并偵查“林德伯格法案”的事件,1934年合并解構成《東快》小說中敘事欲望之一。“林德伯格法案”綁匪是一個非法移民的紐約木匠豪普曼,綁走著名飛行員林德伯格的兒子,林支付贖金71天,發現兒子尸體在他家附近的灌木叢中,保姆貝蒂·格羅是清白的,而女傭維奧萊特·夏普含糊其辭被懷疑,選擇自殺不說實情,因她之前與男子有染并在案發當晚鬼混在一家地下酒吧,在庭審中豪拒絕認罪并上訴被駁回,被送上電椅。但這個事件一直風波未平,或他是無辜的,因拒絕坦白以換取終身監禁的裁決,或是林妻子的姐姐殺死孩子,但豪的妻子安娜一直呼吁還他清白。
1928年阿加莎與第一任丈夫離婚,重創她異常敏感的身心,脆弱易碎的生活狀態,數月后第一次登上東快,重開一段強烈生命感的旅程,共三次領略與熟知熱情洋溢而安詳淳樸的東方文明,細心考究當地各色人等與異域風貌。小說保留法案中罪犯綁架并殺害孩子和保姆自殺的事件,添其孩子父親與正懷孕母親都因這事而故,賦予戲劇性拓展與豐滿故事的內核。綁架案后12人,在東快上“謀殺”罪犯引發一系列錯綜復雜懸疑的事件,赫爾克里·波洛偵探揭開這個謎底。
(二)順應時代潮流與風貌,滿足當下觀眾的內心訴求,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20世紀90年代隨蘇聯解體,資本與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結束,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開啟新世界秩序,亦輸出西方文化——時尚娛樂、體育、電影等,及美國基本價值觀:民主、自由、個人主義與迷戀賺錢欲。全球化進程加劇達到鼎盛,代表標志是高科技、無國界經濟與高速信息化,美國計算機產業迅速發展并帶領全球進入嶄新的產業革命,大眾希冀藝術反映當下生活狀態。卡爾·申克爾執導的2001版《東快》解構史蒂夫·阿姆斯特朗是一名電腦設計,制造并銷售軟件的天才大亨,與阿布斯諾是大學室友,一起創建著名的獵豹操作系統,兩人產生分歧,分道揚鑣。阿布創建迪吉索斯,阿姆創建威史邦,她夫人是索尼婭·阿姆斯斯特朗是紐約的一個土地開發商的女兒、知名女影星,女兒被帶有文身的罪犯卡塞蒂綁架并殺害,但罪犯一夜暴富,雇傭最好的辯護律師。由于證據不足,無罪釋放對外媒體稱為雷切特,洗掉胸前文身,但留有疤痕,波洛在阿布電腦里的錄像入手一步步探知謀殺案的真相,遠離原著中波洛憑借直覺思維的人性解讀。
二、戲劇性品質
戲劇性是戲劇之為戲劇一種獨特品質,或延伸人物內心深處的內戲劇性,或人物之間外在張力的戲劇性,或荒誕派中反戲劇性。內與外戲劇性相得益彰,顯現最深處強烈情感與最深刻哲理的具象外化。戲劇性是一種藝術創作理論與實踐方式與方法,使藝術作品具有完整、貫穿集中與層次鮮明的生命力。戲劇性也是藝術縱橫交錯空間中散發無數線條凝聚一個中心點,愈拓展縱深且遠廣的敘事,愈集中于這一氣質。譚霈生認為戲劇性是戲劇的特性在作品中的具體體現,主要是在假定情境中人物心理的直觀外現,從廣義上講,他是美學的范疇。“戲劇性是人物關系和情節發展中的產生的合乎情理的有機的不可逆轉的‘突變’,導致舞臺上發生使觀眾產生更大興趣的戲劇情境。”從而形成特定的情境—特定的心理內容—特定的動作,具有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因果性鏈條,貫穿動作與反貫穿動作不斷相互交織的力量,構造且解決作品最高任務的一系列的行動方法。
《東快》在真實案件基礎加一個伊斯坦布爾—加萊車廂封閉空間中敘事,被德拉戈米羅夫公主稱“命中注定”的波洛打亂12人謀殺雷切特的完美計劃,殺人后列車由于遭遇暴風雪而停滯,勢必進行新計劃。制造兇手已翻窗逃脫的假象,但窗外無腳印,留有一塊繡著H手帕,罪犯身上12個刀口深淺不一,燒焦紙上 “記住小黛西·阿姆斯特朗(member little Daisy Armstrong)”,在赫伯德夫人的包里發現帶血匕首,與瑪麗·德本漢小姐對峙后,斷定她的真實身份,掩蓋真相的假象與波洛的直覺思維不斷的戲劇性碰撞,持續疊加式向前推動,直到波洛提出簡單和復雜的兩個答案,波洛客觀中立審視,最后裁決交給布克,賦予鮮明人性化人物設定,波洛:“這正是舞臺上一個手腳都捆住的人關進一只箱子,然后再打開箱子,那人忽然杳無蹤影時,觀眾提問題。”《東快》不是注重傳統理性邏輯推理小說,波洛細致觀察人物的微小舉止與動作,用頭腦中微小灰白細胞,躺在椅子上思考,以直覺思維“猜”出真相,表達人性多樣化。
肯尼思·布拉納主演兼導演新版《東快》解構經典力度較大,戲劇性張力貫穿與豐滿于人物之間的外在關系,刪除原著中康斯坦丁醫生,雷切特的秘書麥克奎恩的父親是一名新澤西州檢察官——當年阿姆斯特朗案的公認人,由于找不到罪犯,矛頭指向保姆蘇珊,后抓到罪犯,父親成眾矢之的;蘇珊是列車員米歇爾的姐姐,愛上哈德曼先生,哈德曼曾拒接去做雷切特的美國偵探。阿布斯諾是一名非洲裔醫生,當兵服役時做狙擊手,軍官阿姆斯特朗賞識并資助他完成學業。片頭波洛反復測量與觀察,必吃兩個同等大小和體積的雞蛋才滿足,右腳不小心踩中一糞便,保持內心平衡感左腳使勁踩一下,顯然是強迫癥患者的生活作風,配以“兩撇雪白濃重的八字胡”,不是小說描述一個像雞蛋樣的腦袋且具有致命潔癖卻充滿幽默感的小個子形象,片中波洛說:“即使是很小的瑕疵都會變得特別顯眼,這會讓生活變得無法忍受不管人們說了什么,要么是對的,要么是錯的,沒有灰色地帶”,凸顯是一個有理性嚴謹、嚴肅刻板且有武術功底的“另版福爾摩斯”硬漢形象。面對著一個愛過的女人照片作內心獨白,渲染無法解開破案困境的情緒,著實“淺嘗輒止”的力量不足以表達這種內心深處的孤獨而濃烈的情感,再以戲劇舞臺調度延展快車封閉外的敘事空間,波洛下車拿著槍并扣動扳機:“是時候結束這一切!”波洛像法官似得居高臨下去審視12個“謀殺者”,宣教式陳述謀殺事實。他認為,若12人堅持謀殺“雷切特”是正義,必須再多殺一個他,哈伯德夫人拿著槍對準自己頭部,是空槍!波洛最后回到列車宣布“通過這個案子我意識到正義的天平未必永遠都能保持平衡,接受這個世界的不平衡,車上沒有殺人犯,只有需要重生的人!”最終活生生塑造一個美國式個人英雄主義形象,改編原著中言簡意賅的結尾——“既然已經把我的答案提供了你們,我就要榮幸地退出這樁案了……”
新版波洛是一種“妥協”態度,不是著力刻畫人物內心與人性的復雜,而重墨渲染一場波洛一人對峙“12謀殺者”的正義相對辯論,但波洛與其他人物關系之間,建構的內在戲劇性撐不起“人性的破碎與重建”的主題,波洛人物形象單一與起承轉合貫穿力不足。“戲劇性”定義為“那些強烈的、凝結成意志和行動的內心活動”,“也就是一個人從萌生一種感覺到發生激烈的欲望和行動所經歷的內心過程”。不是表現一個事件本身的外部形式,而是呈現這個事件對人物心靈深處產生真實刺激與影響的整個復雜過程。
三、“復仇”中解讀人性
人性是人的本性。人性具有復雜性、多樣性的審美特征,在舞臺表演中人性是支配舞臺行動最強烈與最根本的原動力,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與“人生來有罪”,這兩個涇渭分明的極端表達。“藝術使我們看到的是人的靈魂最深沉和最多樣化的運動。我們在藝術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種單純的或單一的情感性質,而是生命本身的動態過程,是在相反的兩極——快樂與悲傷、希望與恐懼、狂喜與絕望——之間的持續搖擺過程”。波洛說“我懂得人的本性,我可以告訴你,即使是最無辜的人,在突然面臨被謀殺罪而受審的可能性時,也會失去理智而做出最荒唐的蠢事來的”。人性弱點之間的對抗,舔舐于自身傷口同時傷害他人,互相揭示對方傷疤的私密地方,情與理、善與惡、道德與法義、愧疚與良知來回搖擺的過程,淋漓盡致地表現人性之間精彩博弈的過程,多么撼人心魄的力量!
由大衛·蘇切特主演2010英劇版《東快》,雷切特邀請始終背對著他的波洛做私人保鏢,被果斷拒絕后,回到房間看到恐嚇信,憤怒責罵秘書與男傭,運用平行蒙太奇兩個不斷交叉畫面:
波洛:主啊,感謝您讓我成為天主教徒!
雷切特:請原諒我,今天犯下的罪行!
波洛:若我有做什么善事,請您接受,阿門 !
雷切特:在我休息時請照顧好我,讓我免遭危險,阿門!
一聲慘叫響徹于列車中,畫面表現雷切特懺悔與愧疚的氣氛,波洛許愿他一直所做善良之事是忠于靈魂,堅守法律信仰,追隨上帝旨意。虔誠祈禱時表達一種共通的人文情懷——對理想生活的急切渴望,慰藉自身靈魂深處的安全感與歸屬感,影片傳達上帝是仁慈博愛的偉大情懷。由12人自封陪審團組成的“復仇者聯盟”,宣判并親自執行雷切特的死刑,“謀殺場面”在74版本渲染理性審視的基調,殺死罪犯雷切以一種祭奠亡靈儀式精神,超度他們的靈魂,自我贖回人性的善良,因被逼無奈走上聯盟復仇之路;01版與新版《東快》中處理成復仇的果斷與堅決,殺死雷切特具有勢在必行的正義感;10版是卡塞蒂由于藥性作用致使無法作出任何反應,但還醒著,一個個拿起刀于心不忍的刺向他的身體,需讓他眼睜睜看著并感受著——這是一場他自食其惡果的正義判決,12人承受罪犯殺害小女兒后的一系列非人性巨大的身心傷害,何等殘酷的人性掙扎!
赫伯德:我們需要伸張正義,但法律讓我們失望了!
波洛:如果法律的秩序墮落了應該將它推到更高的高度啊!如果法律被破壞了,所有社會、所有文明人都失去庇護,有高于法律的正義,那就讓上帝來處理,而非你!
瑪麗·德本汗飽含淚水:耶穌說過,讓無罪之人投出第一塊石子吧!我們就曾經無罪啊!當你被正義拒絕,會感到不完整,就像是上帝將你拋棄了,我想我們都問過上帝應該怎么做?他說做應該做的事!
德本漢小姐以為策劃謀殺12人該做的事,就會感到完整,最后說出所做之事是錯的,實指靈魂深處更加不完整性,但是罪犯誰來處置?波洛沉痛地穿過一群兩眼深情渴望等待他答復的人們,把制服交到警察手里:“在犯罪過程中,他落下了一顆紐扣!”痛咽著淚水并轉身離開,雖是風淡云清的結尾,凸顯意味深長的哲理內涵,表達波洛內心深處情與理、道德與法義以及堅守信仰在靈魂深處的掙扎。雪花意象始終貫穿影片,人物心理不斷地向前推進復雜性,波洛的“哭”不是一種妥協與哀怨,表現出善良與正義、情感與理智、道義與法律及靈魂的殘缺與完整,在殘酷現實面前難以抉擇的掙扎痛苦,無處安放的靈魂深處接受人性拷問,堅守信仰的強大力量。12人看著波洛遠去的背影,在這個過程中展現出人性光輝與精神力量,久久回蕩于漫天飛雪中,給予觀眾一種撼動心扉的審美體驗。
該死的惡魔是被12個好人在不合法情境中謀殺的,當一個好人動手殺死壞人時這本身該怎么解釋?該有誰負責?靈魂中有不安愧疚時,他還是一個具有完整靈魂的完整好人?是法律制度的不完整性?人靈魂的不完整性?一個人類未能解決的問題還是由上帝解決?一旦自身遭受非人性極端情境中,怎樣做出選擇,這是一個關于“人性的終極命題”。在善與惡、道德與法義、情與理的行為來回拉扯中體現人性多樣化的運動,人性上賦予神性光芒,解決人類困境,神性上滿足人性訴求,這是一個完整人向往的理想世界,但現實生活中是殘酷的。“人比上帝低一點,但比野獸要稍高一點。亞當和野獸都曾受到過上帝的祝福,我們的實存在獸性和神性之間搖擺:下面是幻滅、悲觀;上面是大門敞開的圣庫,在這里買我們貯存了用虔誠和靈性(即我們垂死的生命的不朽遺留物)鑄成的銀幣。我們總是處在死亡的過程中,但我們也與上帝同時存在。”如《威尼斯商人》鮑西婭勸說夏洛克人性點:“慈悲可以調劑公道!”
四、余 論
74版本基本遵從小說原著精神作為中規中矩的建構影像表達的空間,呈現波洛推理過程占影片總長72%的敘事;新版傾向于拉開封閉空間經緯度中解構并豐滿人物之間的外在關系,人物心靈深處并未發生戲劇性激變;10版《東快》在簡單直接敘事線上廣而深之的探索與挖掘人物內心及人物之間的情感與精神,并重墨濃彩而渲染其復雜過程。最近口碑較佳的《三塊廣告牌》通過豎起三塊廣告牌與警察局對峙,孤獨、無望與憤怒情緒不斷的戲劇性推進母親復雜化的心靈深處,激起更強烈意志與情感構成互相交錯的視覺空間,這是直指人心的人性表達。瑞士劇作家迪倫馬特的《貴婦還鄉》原著結尾貴婦克萊爾用錢殺死前夫伊兒,李建平導演的甬劇《風雨祠堂》在原著基礎上解構:未死的程家傳和女兒反而用錢救了夫人,而夫人將地上麻繩拿起來,絕望中拽著青石板步履沉重地向祠堂大門走去,幕漸閉。“使得全劇在揭露金錢面前人的靈魂有多么丑陋的同時,也留下一絲希望,展現了人性的光芒。”給予欣賞者探索更多可能性的哲理內涵,多么富有意味的形式!經典之為經典是具有細膩與復雜的人物關系、闡釋生活的完整性、飽含悲憫之情、深刻的洞悉人性,善良的溫暖全人類的人文情懷,給予欣賞者提出更多問題去探索,不負責解決問題,具有超越所有時空的魅力,給予人類生命中各式各樣的時間漣漪,在人們審美心中激起一層層創造與探索,常常具有多義性、模糊性與復雜性,“經典文本—影像表達”之間縫隙空間激發著創作者無盡的想象力與創造力,每個創作者以其人生經歷、情感認知,民族文化心理特征進行解構經典,以獨特審美樣式再創造與演繹,只能無限接近,而無法窮盡她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