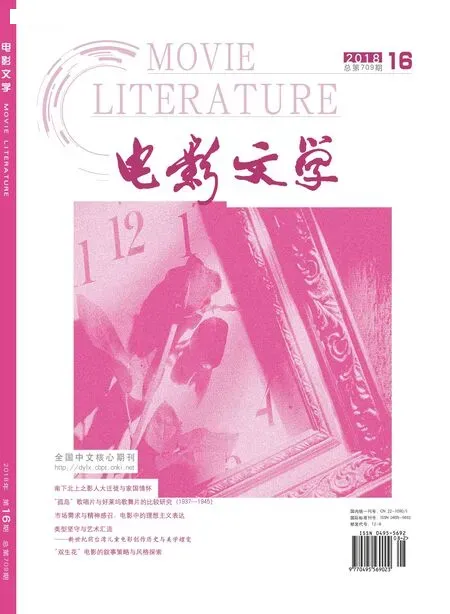南下北上之影人大遷徙與家國情懷
呂少勇 魏媛媛
(1.北京電影學院,北京 100088;2.南昌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江西 南昌 330031)
電影作為藝術總是受到時代氛圍的影響,正如法國理論家丹納所言:“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件藝術作品,我們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處的時代和風俗概況。”他認為藝術是時代和環境的產物。抗戰時期很多影人由于戰爭進行了大遷徙。這種電影人才的流動也帶來了電影創作風格的變化。“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特別是上海淪陷后,一部分電影工作者南下,促進了香港電影業的變化。”在整個抗戰期間,前后有三批影人南下香港,對香港電影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這么說戰亂環境造就了那個時期的香港電影。這恰恰是丹納所謂的時代和環境造就了當時的電影創作。這一時期因時局動蕩不安,上海影人南下香港拍攝電影,爾后,常往返于兩地拍攝的影人逐漸增多,直至1945年后到達頂峰,20世紀50年代后“香港制造”的影片中可以看到諸多南下影人的身影。本次“南下”遷徙使得香港國語片得到繁榮,南下影人進步的電影思想和美學觀念提升了香港電影圈的整體制作水平。自1979年改革開放,國內拓寬了兩地合拍片的限制后,出現了不少到內地取景拍攝的電影。2003年,在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簽訂CEPA協定后,大量香港影人北上拍片,使得內地的商業片市場得到蓬勃發展,延續了港片在20世紀90年代的輝煌。兩撥影人的大遷徙都不同程度上促進了兩地電影市場的發展。為了能夠吸引更多的觀眾走進電影院,幾位導演都把視野聚焦到了歷史題材片上。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運用這一題材,避免了影人初來乍到的水土不服。因此,“如何剪裁出以一個合乎中國想象的電影場景,但同時又不會掉失了寄語香港故事的基調”,是上海“南下”影人和香港“北上”影人的探索之道。
“家國情懷,是主體對共同體的一種認同,并促使其發展的思想和理念”。在電影創作中主要指電影制作方對“家國”共同體的認同并在影視作品中得以體現。無論是“南下”影人還是“北上”影人將歷史題材通過影像的形式把這種家國情懷呈現出來。本文中所探討的四位導演朱石麟、張徹、陳可辛和許鞍華都憑借著自身對中華倫理文化的獨特見解,完美詮釋了家國同構的敘事特征,自發地將個人、家庭、國家聯系起來,以此來表達導演們心中的家國想象。
朱石麟在1946年離開上海前往香港拍攝電影,其作為香港電影業的首批開拓者之一,為香港電影貢獻了不少的經典之作。在《清宮秘史》中,朱石麟延續了他在上海拍片時的一貫風格,把“家”與“國”融合在一起,秉承了朱石麟一貫的以家庭倫理為主的敘事傳統,將中華文化作為影片根基,有效地構成其對“家國”的想象。朱石麟作為南下影人,在創作生涯中始終把中原文化作為電影的根基所在。雖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香港的發展使得其想重新進行身份定位,但大中華的歷史文化仍作為故事的元素在朱石麟的影片中呈現。這也是1945年后南下影人在創作國語電影時所保留的共同認知。
張徹雖差不多與朱石麟同時期離開上海,但他卻沒有直接到香港,而是跟隨國民黨在臺灣拍攝電影,1957年后才到香港。20世紀50年代后,由于中英關系惡化,少有香港拍攝的電影能夠進入內地市場,加上香港經濟飛速發展,電影商業市場逐步擴大,影人將目光更多地聚焦于香港本土市場。相較于朱石麟仍停留在尋找兩地共同文化,張徹轉戰到香港后則一直跟隨時代的潮流,拍攝香港人的電影。張徹開啟了香港的彩色武俠國語電影的時代,在其代表作《刺馬》中他跳出了上海老套的武俠片模式,追求緊張刺激的逼真打斗動作片,雖沒有徹底擺脫程序化的功夫表演模式,但是憑借其巧妙的剪輯手法、精彩的場面渲染,仍創造了獨特的“陽剛美學”的電影風格。雖電影商業市場此時已完全針對香港本土,但是張徹作為南下的影人,身上仍有不少內地的影子。張徹的歷史武打片既跳出了傳統武打程序化的表演場面,又保留了中國自古以來的俠義精神并將其豐富內涵化,將現代流行元素和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有機融合。
相比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南下影人“被迫”在香港拍片,1978年改革開放后內地和香港就已經開始共同開發影片,振興內地和香港的電影市場。兩地合作拍片的歷史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形成風潮,內地為影片提供風景優美的拍攝地和廉價勞動力,借此吸引大量投資方北上,降低香港電影業的投資成本。加之東南亞電影市場的飽和,香港影人進軍內地電影市場則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自2003年CEPA簽訂十幾年后,大量香港影人“北上”摸索新出路,使內地和香港的合拍片成為“大中華電影圈”的主流走向。而陳可辛是其中的佼佼者,2005年憑借《如果·愛》進入內地電影市場后,橫跨了內地同香港幾十年的文化差異,精準定位市場需求,探索出一條“陳可辛”式的成功之路。2007年投資四千萬美元由陳可辛執導的電影《投名狀》斬獲8座金像獎、4座金馬獎獎杯。票房雖不及《英雄》,但仍得到巨大的成功。陳可辛選擇《投名狀》為進軍內地的第二部電影,其中可以看到香港電影幾十年的發展歷程,從簡單的善惡觀到剖析人性的多變,從《刺馬》到《投名狀》,也呈現出“南下”和“北上”影人的時代差異和定位取舍。陳可辛把香港現有的電影觀念,融合進“大中華”的歷史文化之中,并加以全新的詮釋,試圖在內地與香港文化中尋找到平衡點,當然陳可辛也做到了。其在之后的《中國合伙人》《親愛的》等電影中細膩地講述中國故事,構建兩地的文化認同感,更好地針對內地與香港的商業市場,都獲得了不俗的成績。
許鞍華作為香港電影新浪潮的領軍人物,也早早地加入影人北上的浪潮之中,曾拍攝過《玉觀音》《姨媽的后現代生活》等以內地為故事背景的電影,雖在其“北上”時期回到香港拍攝了《天水圍的日與夜》《天水圍的夜與霧》《得閑炒飯》以及《桃姐》,經過一番徘徊之后,仍再次進軍內地,創作了電影《黃金時代》和《明月幾時有》。許鞍華的電影擁有獨特的女性視角,將女性的柔情與細膩納入時空的鴻溝之中,但其視角又很冷靜,常常以旁觀者的姿態審視整個環境。許鞍華導演的新片《明有幾時有》雖票房失利,且口碑兩極分化,但影片作為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的獻禮,仍是上乘之作。北上的香港影人拍攝主旋律電影早已不是新鮮事,許鞍華導演在70歲的高齡還擁有一顆向前沖的赤子之心,為觀眾展現抗戰期間香港無數英雄的抗日場面。華語電影圈的聚焦點越來越向北京靠攏,導演許鞍華仍會把香港情懷與內地背景有機融合,講述更多真誠動人的家國故事。
幾位影人在影片題材上都選擇了20世紀前后中國國家動亂的時代背景,國家的動亂使小家庭的生活瓦解,政治變革、民不聊生成為影片的主要前提依據,在家庭與國家變為矛盾雙方的過程中,國家對于家庭和個人的擠壓日益加重,在傳統倫理約束中,人物命運也愈加悲慘。
朱石麟導演的《清宮秘史》與張徹的《刺馬》、陳可辛的《投名狀》年代相近,《清宮秘史》展現了1889年珍妃入宮到1900年慈禧攜光緒逃離紫禁城的這段歷史,而《刺馬》和《投名狀》講述的都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發生于1870年的“刺馬案”。在這個時期,中國還被稱為清朝,此時社會動蕩已經慢慢涌現出來,而各自家庭也隨著太平天國起義、八國聯軍進京等一系列政治事件而跌宕起伏。在《刺馬》中,米蘭雖已嫁與老二黃縱,但奈何黃縱生性好色又有強烈的大男子主義,跟隨老大馬新貽后官運亨通,有錢有勢,變得更加為所欲為,加上馬新貽形象偉岸,使得米蘭對大哥日漸傾心。任兩江總督后,馬新貽設法殺死二弟黃縱,并將弟妹米蘭占為己有。在這段時間內,太平天國運動風起云涌,朝廷內斗激烈,清朝皇室也處于兩宮太后垂簾聽政的局面。在《刺馬》中,上述時代背景成為國家的時代符號,對家庭構成以及內部成員的關系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影片中也呈現出了類似“家庭亂倫”的非常規家族關系。張徹借助這一故事表現了中國傳統社會中家庭關系的忠貞與狡詐、正直與罪惡的矛盾關系。《投名狀》中老大龐青云的出場就與《刺馬》中的不盡相同:龐青云原本就是為清朝賣命的軍官,可惜在一次戰役中其視如兄弟的戰友們因為友軍的見死不救完全戰死沙場,只剩下龐青云一個人茍延殘喘。社會騷動變亂,時代中的小家庭也隨之起起伏伏。《清宮秘史》里珍妃被迫投井,慈禧和光緒帶著其他妃子逃離北京。《明月幾時有》中母親帶著方蘭離開原生家庭,母女二人相依為命。在歷史題材作品中,幾位導演不約而同地將歷史背景作為影像符號,規避了宏大的敘事場面,將時代變遷縮小到家庭的細微生活之中,展現了導演個人的歷史觀,把簡單的家庭生活注入社會動亂的豐富內涵,用小家庭內部的倫理道德來重現歷史發展進程。
朱石麟、張徹、許鞍華以及陳可辛都偏愛使用家國同構的敘事方法,將家庭的倫理失衡與國家政治有機融合,把中國儒家文化中家國同構的觀念在家庭權力爭斗中呈現出來,表現出導演對于中國政治的獨立思考。
影片《清宮秘史》里,朱石麟把整個國家的興衰濃縮在一個家庭之中,光緒稱呼珍妃為“二妞”,慈禧喊妃子為“孩子”,唯有光緒稱慈禧為“皇阿瑪”,構成了三組矛盾關系。《清宮秘史》的故事雖集中描述了皇宮的小家庭生活,但慈禧和光緒的一舉一動卻關乎全天下百姓的生活,將家庭倫理與國家、民族結合在一起。這是一種專屬“文人電影”的情懷,從家庭生活入手,把倫理化的故事打上朱石麟的標簽,借助“家國”的文化內涵,有效地把大中華的歷史作為主體框架,完成了其對“家國”想象的敘事。在陳可辛版的“刺馬案”中,同樣是老大龐青云派人暗殺老二趙二虎,老三姜午陽刺死龐青云的故事構成,區別于張徹的家庭傳統倫理的描述,陳可辛把趙二虎之死歸結到了國家生死存亡的大義之上,而三人之死的驚奇故事更像是對當時社會亂象的再現。三人作為立下生死狀的結拜兄弟,本身就構成了儒學思想中家庭的概念。而在三人組建其小家庭的過程中,陳可辛更注重刻畫“人性黑白之間的灰”。三人難辨善惡的性格特征恰好與當時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性質相類似,家庭的崩塌與社會的動亂成為同一過程的兩個視角,構成了陳可辛式的家國同構的敘事模式。許鞍華導演的新片《明月幾時有》中也有濃濃的家國情懷。方母從最初自私自利的包租婆到成為舍生取義、寧死不屈的一代英雄,方蘭為了整個游擊隊的生命安全和對地下工作的保護意識放棄解救方母,都是一種舍棄小家救大家的精神。方母的逝去和李錦榮被槍殺,東江游擊隊失去重要力量,與日本在香港越演越烈的瘋狂掠奪交叉進行,將家庭生活與國家戰爭協調統一,形成了家國同構的敘事模式。許鞍華導演“以女性獨特的細膩敘事,將藝術光影融入整個戰爭主題的敘事之中,展現了一幅幅紅色革命歷史的生動畫卷”。
縱觀兩撥影人在內地與香港的南下與北上的遷徙,我們可以看到在他們的作品中一致呈現的家國情懷與風格變遷,始終與時代的氛圍伴生,與家國命運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