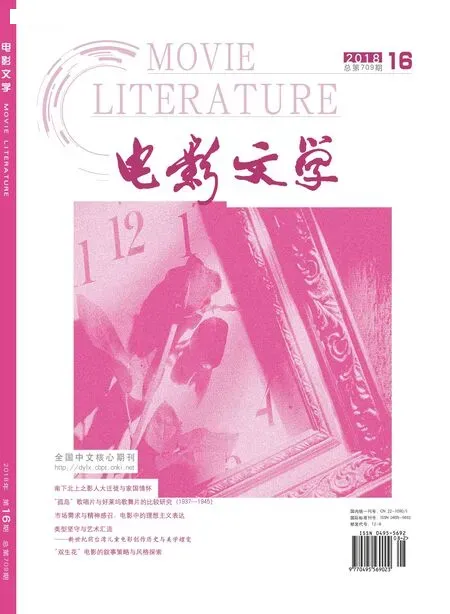電影嵌套式結(jié)構(gòu)敘事功能研究
賈 兵
(沈陽音樂學(xué)院 戲劇影視學(xué)院,遼寧 沈陽 110000)
嵌套式結(jié)構(gòu)屬于分形學(xué)的概念,指“結(jié)構(gòu)與結(jié)構(gòu)的互相嵌套,不同尺度、層級上的相似性對稱”。電影的嵌套式結(jié)構(gòu)則指影片各段落之間在主題、劇情、時空環(huán)境、敘述方式等內(nèi)容或形式上具有相似之處,且在結(jié)構(gòu)上具有包含與被包含的關(guān)系。按照這些段落間相互嵌套的層數(shù)可以分為雙層嵌套和多層嵌套兩類;按照被嵌套內(nèi)容的完整程度又可以分為插曲式嵌套和交錯式嵌套兩類。按照具有嵌套關(guān)系部分的相似點又可以分為情節(jié)與主題、時空環(huán)境、敘述層級等類型。
在電影嵌套式結(jié)構(gòu)的上述幾種分類中,以第三種分類方式最能突出各類型的嵌套在敘事功能上的區(qū)別,故此本文將以這種分類方式劃分出的情節(jié)與主題嵌套、時空嵌套和敘述層級嵌套幾種類型為主,兼顧電影嵌套式結(jié)構(gòu)的其他分類方式,全面分析嵌套式結(jié)構(gòu)在電影中的敘事功能。
一、情節(jié)與主題嵌套
結(jié)構(gòu)作為“情節(jié)的組織方式”實際上是一種由主題決定的如何把各故事段落組合成電影情節(jié)的理念或方法,主要涉及時間上對每段情節(jié)的先后安排,以及空間上對每段情節(jié)的明暗場取舍。因此電影的情節(jié)實際上就是依照某種或某幾種結(jié)構(gòu)方式對故事內(nèi)容的分段、取舍和重新組合,而被分成段落的情節(jié)又可以進一步被拆分成更小的段落直至事件、人物行動等最基本的情節(jié)單位。所以如果影片的某一小段情節(jié)和包含其在內(nèi)的大段情節(jié)具有某種相似性,最容易體現(xiàn)二者的嵌套式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
小段情節(jié)與大段情節(jié)的相似性可以體現(xiàn)在情節(jié)內(nèi)容本身的淺層相似和情節(jié)背后隱含主題的深層相似兩個方面。情節(jié)嵌套的敘事功能也分別體現(xiàn)在表現(xiàn)主題和反轉(zhuǎn)情節(jié)兩個方面。
(一)表現(xiàn)故事主題
通過與主線情節(jié)主題一致的故事來突出影片的主題是嵌套式結(jié)構(gòu)最常見的敘事功能之一。
對電影來說,大多數(shù)的商業(yè)影片都會把故事的主題通過比較直觀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但這種呈現(xiàn)方式又受到電影藝術(shù)形式上的制約:電影同戲劇一樣都具有內(nèi)外兩層交際系統(tǒng),前者是故事中人物的交流,后者是故事中人物和觀眾的交流。而絕大多數(shù)影片都遵守現(xiàn)實主義戲劇的要求,通過假想出的“第四堵墻”來阻斷故事中人物和觀眾的直接交流,因此處于內(nèi)層交際系統(tǒng)中的電影角色們只能通過合理的情節(jié)向觀眾們間接地傳遞有效信息。因此,影片的主題不能由人物直接傳達給觀眾,必須要通過人物之間的對話間接地告訴觀眾。
所以如何讓影片中的人物符合情境地闡釋影片的主題變成了一個艱巨的任務(wù)。而安排這些人物經(jīng)歷一小段和影片主要情節(jié)緊密相關(guān)的同主題事件,進而讓人物通過對這一事件的討論向觀眾闡釋故事的主題不失為一種巧妙的敘事方式。甚至在很多商業(yè)電影中都會在影片的第一幕也就是開端部分刻意地安排這樣一個“主題呈現(xiàn)”的環(huán)節(jié),讓人物通過一小段與整部影片主題相關(guān)的情節(jié)、事件或一個行動(對話)來表達整部電影的主題。
這種用來突出主題的被嵌套情節(jié)一般情況下是完整的“插曲式嵌套”。如果將其打碎,與主線情境的敘事構(gòu)成一種“交錯式嵌套”的形式會讓主題不夠明顯,但也會留給觀眾更多思考、總結(jié)的余地。比如我國電影《路邊野餐》就通過安排了與主人公陳升主線情節(jié)交錯并行的花和尚和老大夫的兩段支線情節(jié)來表現(xiàn)共同的主題:時間的流逝是不可逆的,對過去錯誤的彌補、挽救的行為是無力的。這一主題并非由影片中的某個人物直接說出,而要觀眾在看完了一主兩輔三段情節(jié)后自行總結(jié)出。
上述主題嵌套的“插曲式嵌套”和“交錯式嵌套”都屬于“雙層嵌套”——雖然《路邊野餐》具有主線情節(jié)下的兩段同主題支線,但二者處在同一層次上——如果將同主題的多個故事以“多層嵌套”的形式展現(xiàn)出來,該主題將會“具有普遍意義,是對人類社會的一種概括”,進而被凸顯成一種近乎世界觀的,對世界本質(zhì)的描述。比如我國電影《師傅》就以多達五重嵌套的“計中計中計中計中計”的結(jié)構(gòu)形式為我們描繪出了津門武林爾虞我詐,相互利用的殘酷世界。
(二)形成反轉(zhuǎn)
同主題情節(jié)的嵌套可以說是嵌套式結(jié)構(gòu)中敘事功能最為直接、簡單的一種類型。除去主題的相似,相似情節(jié)的嵌套所承擔(dān)的敘事功能更多地表現(xiàn)為造成影片情節(jié)的反轉(zhuǎn),其常見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反轉(zhuǎn)的方式是依靠人物出場時的能力展現(xiàn)事件為影片主線故事高潮部分的反轉(zhuǎn)提供鋪墊或提示。情節(jié)的反轉(zhuǎn)來自亞里士多德的“發(fā)現(xiàn)”和“突轉(zhuǎn)”理論。一般來說,情節(jié)在符合因果關(guān)系的前提下,變化得越突然,幅度越大,戲劇性就越強。因此“反轉(zhuǎn)”是現(xiàn)代影視劇情節(jié)最有吸引力的敘事技巧之一。對大部分敘事電影來說,至少要在影片的高潮部分安排一次情節(jié)的反轉(zhuǎn),讓主人公由逆境進入順境。為了避免主人公在高潮部分突然反轉(zhuǎn)的突兀感,影片通常要在開端部分的情節(jié)里對此進行鋪墊。這是因為影片的開端部分主要承擔(dān)交代故事情境、完成人物出場等功能,因此大量的用于交代人物成長經(jīng)歷、塑造人物性格、展現(xiàn)人物能力的狀態(tài)性事件會集中出現(xiàn)在這一部分。而在之后的情節(jié)中,主人公因為要進入主線情節(jié)當(dāng)中,幾乎所有的事件都是行動性的,不適合隱藏對人物反轉(zhuǎn)劇情手段起到鋪墊作用的內(nèi)容。
在上述敘事模式中,如果影片在人物出場時為人物安排了一個插入性的事件來展現(xiàn)人物的能力,并使這一能力成為主人公在影片高潮時完成反轉(zhuǎn),那么這一事件就往往和整部影片構(gòu)成了情節(jié)上的相似性,形成了一種嵌套關(guān)系。
比如美國電影《間諜大橋》的開端部分,主人公出場時作為一名保險公司的律師就摩托車連撞五人的理賠事件和對手展開爭論。主人公把摩托車連撞五人說成一起交通事故而非連續(xù)的五起,為公司減少了損失。而在本片的主線情節(jié)中,主人公面臨要換回兩名美國人質(zhì),手里卻只有一名蘇聯(lián)間諜的艱難情況。他最后巧妙地將兩次換人解釋成一次一對二的交換過程,圓滿地完成了任務(wù)。影片開端部分主人公出場時的理賠事件是一段單獨的,和影片之后情節(jié)并無因果聯(lián)系的“插曲式嵌套”事件,是作為展示人物能力的出場事件而安排的,但其同時為影片高潮部分的反轉(zhuǎn)提供了鋪墊和提示,并且和整部影片一換多的人質(zhì)交換主線情節(jié)具有內(nèi)容上的相似性,形成了嵌套結(jié)構(gòu)。
第二種反轉(zhuǎn)的方式是通過在影片的高潮部分解開人物出場時自帶的“心結(jié)”來反轉(zhuǎn)情節(jié)。影視劇往往會在主線故事中設(shè)計一段人物的“前事”讓人物出場時帶有某種“心結(jié)”,而當(dāng)情節(jié)發(fā)展到高潮時,人物將面對和形成“心結(jié)”時類似的情況,最后由于人物采取了和前事中不同的行動而逆轉(zhuǎn)了形勢,也解開并戰(zhàn)勝了自己的“心結(jié)”。影片中的短暫“前事”由于和影片的主線故事不處于同一時空——通過人物的回憶或夢境來表現(xiàn),又和之后的情節(ji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這段“前事”可以和整部影片構(gòu)成嵌套結(jié)構(gòu)。
在電影《機械公敵》中,主人公因疲勞駕駛導(dǎo)致自己和一名女孩同時落水,而趕來營救的機器人只會進行純理性的判斷,搶救了生存概率較大的主人公而小女孩被淹死。事后,從傷痛中恢復(fù)過來的主人公無法戰(zhàn)勝對自己疲勞駕駛的怨恨,尤其難以接受讓一個無辜的女孩因自己而死的事實,因此把對自己的怨恨轉(zhuǎn)嫁到了救人的機器人身上,認為是機器人的錯誤選擇讓本該接受懲罰的自己活了下來,而無辜的女孩被“害死”。主人公進而懷疑、痛恨一切機器人。但在影片的高潮部分當(dāng)男女主人公同時掉落深淵時,作為隊友的機器人只來得及拯救一個人,主人公要求它放棄關(guān)于生存概率的理性判斷,去救女主人公。最終機器人救下了女主人公,男主人公也憑借機械手臂安全著陸。同時,該片關(guān)于主人公對“前事”的回憶是穿插在現(xiàn)實世界的故事推進中不斷揭示的,屬于“交錯式嵌套”,這種類型的嵌套方式能不斷增加觀眾對這段“前事”具體內(nèi)容的期待,具有增強懸念的敘事效果。
第三種反轉(zhuǎn)的手段同樣來自主人公的“前事”,但主人公并不需要從中吸取教訓(xùn),而是將其作為例證(或反例)來勸服其他人物,反轉(zhuǎn)劇情,因為“只有劇中人物在對話中互相較量、互相影響,而導(dǎo)致各自的心情和相互關(guān)系的變化,才是有‘戲劇性’的”。所以,依靠自己的相似經(jīng)歷來改變其他人物往往成為電影編劇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戲劇性技巧。而人物與當(dāng)前情境類似的“前事”也是作為“插入式”的內(nèi)容(甚至僅僅由人物敘述而不通過畫面表現(xiàn),這種情況實際也構(gòu)成了敘述層級上的嵌套關(guān)系)嵌套在當(dāng)前的情節(jié)中的。
二、多重時空嵌套
現(xiàn)代電影中往往存在多個人物活動的“時空”,但并非所有的時空之間都是嵌套關(guān)系。如前文所說我們對嵌套式結(jié)構(gòu)的認定,時空嵌套的前提是某一時空必須從屬于另一個時空,并且二者具有相似性。比如《盜夢空間》的夢境是從屬于影片的時空的,而且二者都具有人物身份上的虛擬性:電影世界中的角色由演員扮演,夢境世界中的人物由電影中的角色扮演,其他像《法國中尉的女人》《勇敢者的游戲:決戰(zhàn)叢林》《頭號玩家》等影片都屬于這一類型。
從這一點上看,絕大部分存在時空嵌套關(guān)系的電影都同時存在敘述層級的嵌套關(guān)系,但也有例外的情況,那就是單一敘述層級下同時間維度中地域環(huán)境的嵌套。這種嵌套類型往往存在于災(zāi)難電影的結(jié)尾:許多災(zāi)難電影為了增加恐怖效果,都會把時空限定在一個封閉的地域環(huán)境中,而主人公的自覺意志就是逃離這一環(huán)境,但往往在電影的結(jié)尾,主人公逃離這一環(huán)境后卻發(fā)現(xiàn)外面的世界也處于同樣的災(zāi)難當(dāng)中,進而產(chǎn)生一種具有悲劇效果的無力感,并且使影片完結(jié)于一個情節(jié)點上,為連續(xù)敘事提供可能性。比如《生化危機》系列電影的第一部是女主人公逃離保護傘——地下實驗基地,而在影片的結(jié)尾她發(fā)現(xiàn)整個城市都陷入了同實驗基地一樣的生化危機當(dāng)中。在后續(xù)的第二部情節(jié)中,女主人公試圖逃離整個城市,但在影片的第三部整個地球都遭遇了同樣的危機。
可以說,正是這種地域從屬關(guān)系從小到大的變化讓故事持續(xù)發(fā)展,而同樣的充滿生化危機的環(huán)境則構(gòu)成了三者的相似性,進而形成了嵌套式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如果單純從第一部影片來看,該系列電影屬于雙層嵌套結(jié)構(gòu),如果把三部影片都納入研究范圍則構(gòu)成多層嵌套。
三、敘述層級嵌套
敘事中因存在不同的敘述層級而造成的“戲中戲”結(jié)構(gòu)是最傳統(tǒng)的嵌套式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從電影和戲劇藝術(shù)的本質(zhì)來說,如前文所述二者均存在內(nèi)外兩層交際系統(tǒng):角色之間、角色與觀眾之間。所以電影和戲劇這兩門藝術(shù)的存在形式本身就體現(xiàn)著嵌套結(jié)構(gòu):嵌套在現(xiàn)實世界中以及與現(xiàn)實世界相似的虛擬世界。而以“戲中戲”為代表的帶有多敘述層級的嵌套式結(jié)構(gòu)電影正是對這門藝術(shù)存在形式的一種深化和模仿,因此比起之前論述的幾種嵌套類型更值得研究。
含有多個敘述層級電影的嵌套式結(jié)構(gòu)可以按照敘述層級之間的跳躍方式進一步分為由內(nèi)到外和由外到內(nèi)。
由內(nèi)到外的嵌套結(jié)構(gòu)最常見的形式是放在影片的開場或開端部分,用來交代故事的情境。如《瘋狂動物城》的開場部分就是通過由小動物們扮演的戲劇來交代整部影片的故事背景。嵌套式結(jié)構(gòu)的這種用法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電影在開端部分的結(jié)構(gòu)功能就在于對情境的交代;而另一方面這種由內(nèi)到外的敘述層級跳躍必須放在電影的最開始,因為只有這樣才會在敘述層級由內(nèi)到外的跳躍時形成情節(jié)的反轉(zhuǎn),讓觀眾意識到這段情節(jié)只是戲中之戲。而一旦觀眾先接觸到外一層次的交際系統(tǒng),就等于暴露了這種“戲中戲”的嵌套關(guān)系,隨著敘述層級的跳躍而產(chǎn)生的反轉(zhuǎn)效果也就不復(fù)存在了。
這種嵌套結(jié)構(gòu)類型除了交代影片情境、形成反轉(zhuǎn)外,還有形成不可靠敘述的敘事作用。在常規(guī)的電影結(jié)構(gòu)中,開端部分交代的情境往往含有不可靠敘述的內(nèi)容,這些內(nèi)容會隨著情節(jié)的發(fā)展在影片的高潮部分被推翻。而使用了由內(nèi)而外進行敘述層級跳躍的“嵌套式結(jié)構(gòu)”電影,會因為被嵌套部分的預(yù)序在敘述層級上低于整部影片而讓預(yù)序更容易被推翻。比如泰國電影《天才槍手》就把幾位主人公預(yù)演考試作弊被抓的辯解場景放到了影片的開場,與影片形成了“戲中戲”的嵌套式結(jié)構(gòu),形成了幾位主人公因作弊被捕的不可靠敘述,這一懸念直到人物進行考試前的預(yù)演時才被揭開,形成了敘事上的反轉(zhuǎn)。值得一提的是,這段預(yù)演的情節(jié)針對幾位主人公被剪成了幾段,并伴隨他們的出場依次呈現(xiàn),使影片同時具有“時空交錯結(jié)構(gòu)”和“嵌套式”結(jié)構(gòu),形成了“交錯式嵌套”的特殊敘事效果。
這種由內(nèi)向外跳躍敘述層級的嵌套式結(jié)構(gòu)一般限于雙層嵌套,否則過多的敘述層級的跳躍會不斷否定之前的敘事,給觀眾帶來被愚弄的感覺。
另一種敘述層級的跳躍形式是由外而內(nèi)的,這也是最常見的一種嵌套式結(jié)構(gòu)。這種結(jié)構(gòu)的影片會先在開端部分展示電影世界的情境,然后隨著主人公進入更內(nèi)層的敘事層級而再次交代新世界的情境。故事的主要內(nèi)容就發(fā)生在這一時空中,直到這段故事結(jié)束后主人公回到現(xiàn)實世界,并通過在內(nèi)層時空的經(jīng)歷解決了現(xiàn)實世界的問題。典型的例子如《勇敢者的游戲:決戰(zhàn)叢林》。
這種結(jié)構(gòu)之所以盛行是因為電影藝術(shù)本身就是一個嵌套在現(xiàn)實世界中的虛擬世界,電影中的人物如果進入更低一層次的時空當(dāng)中會為電影觀眾帶來類似“移情”的共同感受和體現(xiàn),為觀眾帶來更大的吸引力。
同時,隨著電子游戲尤其是網(wǎng)絡(luò)游戲的發(fā)展,從《羅拉快跑》開始,游戲的時空模式也在不斷影響著電影觀眾的思維方式,因此其必然會對電影的時空模式造成影響。在這一類型的電影中,除了常規(guī)的“插曲式嵌套結(jié)構(gòu)”和“雙層嵌套”結(jié)構(gòu)外,也有像《頭號玩家》一樣,故事不斷穿梭于現(xiàn)實與虛擬時空同之間的“交錯式嵌套”的類型,以及和《盜夢空間》一樣具有多個敘述層級的多層嵌套類型。
電影結(jié)構(gòu)的變化是一個動態(tài)發(fā)展的過程,本文僅就當(dāng)下和經(jīng)典電影中具有嵌套式結(jié)構(gòu)的影片在敘事功能上進行了分類和研究。可以想象,隨著電影藝術(shù)的發(fā)展,嵌套式結(jié)構(gòu)的影片會呈現(xiàn)出更多的類型,也會承擔(dān)更為復(fù)雜的敘事功能。
注釋:
① 詳見賈兵:《論電影嵌套式結(jié)構(gòu)的內(nèi)涵與類型》,《電影文學(xué)》,2017年第24期,第53-54頁。
② 詳見賈兵:《從戲中戲、夢中夢到計中計——論嵌套式結(jié)構(gòu)在影視劇中的應(yīng)用》,《湖南大眾傳媒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2016年第六期。
③ 除去這兩種類型之外,許多嵌套式結(jié)構(gòu)的電影都存在不斷在內(nèi)外兩個敘述層級跳躍的情況,由于這類影片均屬于“交錯式嵌套”類型,所以本文并未將其單獨進行研究,而是針對第一次敘述層級的跳躍方式將其歸入前兩類影片當(dāng)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