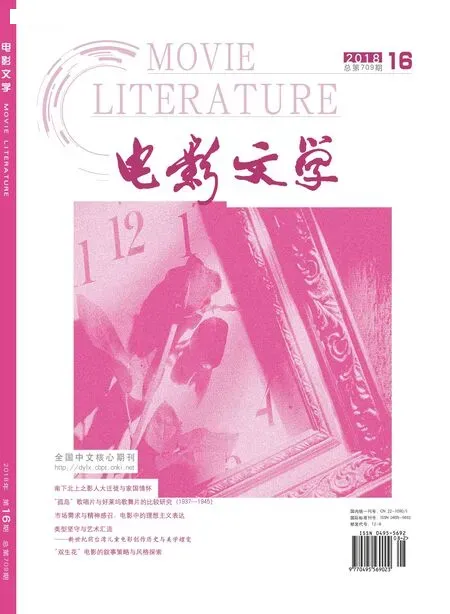《1980年代的愛情》:從文學到電影
楊涵鈞
(韓國清州大學,韓國 清州 360-764)
從處女作《贏家》(1995)開始,霍建起就不斷憑借著自己獨特的導演風格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在霍建起的電影中,人們幾乎總能尋覓一個烏托邦式的,迥異于令人焦慮和不安的現實社會的生存凈土,精神家園,或是一段純真的,人們在社會發展中遺失了的情感。其新作《1980年代的愛情》(2015)也不例外。電影改編自野夫帶有半自傳色彩的同名原著,電影在對原著的價值取向、情節梗概進行了忠實還原之外,也根據當代觀眾的審美傾向,以及電影藝術自身的特色對原著進行了改動。
一、原著審美理想的保留
在整個故事的主要情節、人物形象等方面,《1980年代的愛情》都做到了忠于原著,更重要的是,保留了原著的審美理想。野夫對于他心目中“1980年代的愛情”寄予了最為深切的懷念,認為那是其他任何時代的愛情都取代不了的,極為純真的一段情感。也正是在野夫的這種心理濾鏡下,“我”原本條件艱苦,內外交困的這一段小鎮生活被視為人生中最寶貴的經歷,閉塞的公母寨也顯得山清水秀,當地的土家族人也讓“我”感到淳樸善良,“我”甚至不愿意再離開小鎮,而只希望能夠留在這里與心愛的麗雯長相廝守。整部小說充斥著大量作者的內心獨白,而情節則極為簡單。而霍建起正好是當代影壇的一位“電影詩人”,小說重情感而輕情節的特點是與霍建起電影的風格不謀而合的,在其如《那山,那人,那狗》(1999)等電影中,情節都并不復雜,最令觀眾難忘的是人和人之間暗流涌動的情感,以及電影中情景交融、唯美詩意的畫面。美術出身的霍建起極擅長用美好的物象來表達情感,生活中普通的、無生命的事物都能在其鏡頭之下被賦予情懷。
首先,在《1980年代的愛情》中,人物理想主義的一面得到渲染。霍建起延續了原著對“人”的關注,對美好情感和品行的贊美。關雨波在內心中一直保留了給麗雯的位置,愿意為麗雯付出一切,而麗雯則更為無私地希望關雨波離開自己,因為了解關雨波是一個屬于遠方的人,是一個應該在路上的“天下客”,麗雯在深愛關雨波的情況下推開了關雨波,讓他去闖蕩四方。當關雨波借贊美麗雯的父母側面表達出對麗雯的愛:“患難相依一輩子,留下來也沒什么不好的。”麗雯直接回復道:“你懂我爸的陪伴,可你理解我媽的歉疚嗎?”甚至在兩人90年代重逢之后,發生了肉體關系,寡居的麗雯因為自己上有癱瘓的婆婆,下有小女兒,沒有與關雨波進一步建立關系,并把自己生活困難,身患癌癥的情況對關雨波守口如瓶,不讓情感成為對方的牽累。
其次,為了能突出這種“水過三秋,有些話就像夢一樣,說破了,就剩一地碎片”含蓄唯美的感情,電影設置了諸多猶如靜美清新的小品的橋段,帶觀眾進入到主人公的情感世界中。如在蔥翠的清江邊,麗雯坐在河岸晃蕩著雙腳,聽著小雅送給她的隨身聽,音樂響起,是悠揚的俄羅斯族民歌《永隔一江水》:“波浪追逐著波浪,寒鴉一對對。姑娘人人有伙伴,誰和我相偎。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兒已等碎,我和你是河兩岸,永隔一江水。”而關雨波則走到河邊,一邊洗臉,隨后與麗雯在說笑中打起了水仗。這一段的色調、畫面與意境實現了完美的結合。類似這樣的畫面在《那山,那人,那狗》、《藍色愛情》(2000)中也多有出現,觀眾在看到男女主人公以及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時,也感受到了霍建起一直用心建構的溫柔敦厚的鄉土意識。霍建起擅長將有別于都市文化的鄉土環境打造為一個主人公心靈棲居的“家園”,讓主人公和觀眾陷入在無限的追緬之中。
正是這種對于主觀情愫和物象營造的重視,原著中平緩、溫和的敘事節奏也得到了保留。在原著中,野夫采取一種主觀介入的視角,不厭其煩地敘說著自己對麗雯的情感,兩人一直若即若離,而生活則似乎沒有任何波折。電影中也如此,包括關雨波在工作中誤將詩歌當成給領導的演講稿的失誤,都因為工作調動的到來而輕輕揭過。隨后關雨波在進入90年代后的坎坷經歷也被一筆帶過,麗雯再次出現,在驚鴻一瞥的見面后,關雨波再一次得到麗雯的消息就是她的死訊。在關雨波順利地收養了和麗雯長相酷似的麗雯的女兒后,電影也就落下了帷幕。一切都平淡得酷似生活的原貌,但又在一幀幀畫面中具有感人至深、催人淚下的力量。
二、戲劇沖突的加入
電影的創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這也就使得《1980年代的愛情》與原著在有著大體上的“同”的同時,又有著“異”。考慮到過審以及讓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更為單純的需要,原著中“我”入獄的原因被改為替他人擔保受騙,麗雯父親落魄的原因也由“第三種人”改為了在“文革”中因為麗雯大舅的海外關系遭受牽連,至今沒有被恢復身份。因此,麗雯父親對“我”說的大段與政治有關的,引發“我”深思的內容也全部被刪除。原著中“我”和麗雯的父輩曾經是宿命式的“斗”與“被斗”的關系不復存在。原著呈現給讀者一個復雜的外部世界,而電影則全力提供給觀眾一個溫情脈脈的土家族山鄉,盡管減損了原著的豐富性,但也避免了觀眾對人物形象有可能產生的混亂認識以及電影上映的其他阻礙。
電影最明顯的改編就是,在《1980年代的愛情》中,霍建起加入了小雅這一人物,即關雨波在大學時候的女朋友。在原著中,“我”的女朋友始終沒有正面登場,她在畢業后留在了省城,與“我”只保持著極容易受到天氣干擾的書信聯系。女朋友希望“我”能考研去省城與她團聚,而“我”卻在見到了麗雯之后產生了留下的念頭,并開始質疑自己與女朋友這種沒有“痛感”的感情是否是自己需要的愛情。而在電影中,女朋友借著出差的機會來到小鎮看望關雨波,并在小鎮留宿了兩晚,也有了一個小雅的名字。由于考慮到男女同居一室的不便,關雨波將小雅安置在了麗雯在供銷社的小屋,盡管關雨波介紹麗雯為自己的“女同學”,小雅還是敏銳地感到了對方在感情上對自己的威脅。在原著中,女朋友游離于小鎮敘事之外,只在“我”的回憶中出現,兩位女性的對立也只在“我”的意識中展開,這無疑是較符合現實情況的。而電影則為了戲劇沖突的需要,通過制造小雅出差的巧合讓這一人物登場,并讓小雅結識麗雯,對麗雯產生敵視,也將關雨波不得不在兩位女性之中做出抉擇的心態明面化。這是一種典型的化生活矛盾為戲劇沖突的改編方式。
“生活矛盾是生活中的原始狀態,一般是散漫的,進展緩慢的,錯綜復雜的,有的矛盾沒有激化成沖突就轉化了,各種矛盾交錯影響,情況比較繁雜。而戲劇沖突是由作者經過長期深入生活,掌握住生活矛盾發展的必然規律,加以概括集中,典型化,根據主題思想的要求,突出一種矛盾沖突,加強它的戲劇性。”在原著中,屬于生活矛盾的這場“三角戀”最終由于“我”的心志不堅,與女朋友并非情投意合而無疾而終,并沒有激化成沖突。而在電影中,小雅則在幽暗溫暖的供銷社小屋質問麗雯:“你也喜歡他對不對?”而麗雯的回答則是:“山里人的喜歡和你們的喜歡是不一樣的。”隨后,小雅逐漸感受到麗雯的善良和無私,包括了解到麗雯也不愿意關雨波留在小鎮上耽誤前程,態度馬上發生了改變,甚至將自己貴重的隨身聽送給了麗雯。小雅盡管出場時間不多,但是自作主張幫關雨波報名考研,又將隨身聽送給麗雯,抱著麗雯的肩膀直白地對麗雯表示“我喜歡你”,一個強勢、開朗的城里姑娘的形象被塑造起來。相對于原著中只是一個符號式人物的女朋友而言,小雅給觀眾留下了較深的印象,觀眾也在小雅對麗雯的肯定中,進一步感受到了麗雯的美好和可貴。
三、民俗奇觀的營造
而必須注意到的是,霍建起一直保持著自己在兩代導演群體之間的特殊性,保持著自己并不迎合市場的詩意電影風格,并不意味著霍建起電影的創作思路是純粹個性化,無視受眾的。相反,從《那山,那人,那狗》贏得的世界性贊譽,在《暖》(2003)中邀請香川照之出演以打開日本市場,在《情人結》(2005)中選擇趙薇與陸毅出演并針對情人節檔期做了一定宣傳就不難看出,霍建起并非是一名無意于彌合藝術與商業,自我與市場,乃至民族與世界鴻溝的導演,甚至在其作品從文學變為電影的過程中,不乏與同時期導演趨同的一面。
在《1980年代的愛情》的改編中,這種趨同就體現在民俗奇觀的渲染上。在原著中,野夫對“哭嫁”和“跳喪”兩個儀式只是約略提及,更多的筆墨被用于表現“我”內心的主觀情感流動。然而對于電影藝術來說,相對于以旁白來表露主人公的思維和情感,觀眾更愿意接受多彩的畫面造型和新奇的民俗意象。另外,賦予民俗意象以指代意義,將一個對觀眾而言陌生的封閉空間與質樸的生活氣息,人們或壓抑扭曲,或熱烈奔放的生命情態并置,在某種程度上也能提升電影的深度。因此,在電影《1980年代的愛情》中,“哭嫁”和“跳喪”兩個儀式被以視聽語言綜合性地渲染和夸大。在“哭嫁”中,新娘身穿紅裝,頭披紅蓋頭,房屋里掛著一排紅燈籠,少女們則在新娘兩邊坐著,唱著悲哀的歌,被觸動心事的麗雯也借此機會流下了眼淚。原本應該是“嘴哭心里甜”的“哭嫁”儀式在這里被悲哀化了,而大片的紅色則給予了關雨波一種震撼,他本人的欲望萌動也在這一片紅色中被外化了。而“跳喪”則相反,黑白兩色成為主色調,作法之人在麗雯的棺木之前身穿黑衣,頭戴白布,載歌載舞,用一種狂歡的方式讓死者實現飛升,這在關雨波看來是美的,但他依然難以承受,備感壓抑。因為死去的不僅是麗雯,也是關雨波心中永遠回不去的木樓老屋,裊裊炊煙。
用一系列帶有神秘色彩的民俗奇觀來增加電影的辨識度,給予觀眾一種在視聽上的來自異域情調的享受,并非霍建起的原創。無論是第五代抑或第六代導演,都不乏為了構建一個能夠安置民俗奇觀的時空,而改變原著背景者。例如張藝謀改編自劉恒《伏羲伏羲》的,加入了“攔棺”等民俗的《菊豆》(1990)就模糊了原著的時代背景,也對原著的故事進行了截取而非全盤復制。又如《大紅燈籠高高掛》(1991)將蘇童原著《妻妾成群》中的江南背景置換為了山西干燥、封閉的四合院,規整的院落更使得電影新加的“點燈”習俗顯得觸目驚心。這些民俗奇觀的出現,在吸引觀眾目光,增強電影的東方色彩的同時,也使得敘事具有某種隱喻或象征修辭,可以說并非導演的嘩眾取寵。
同一個故事從文學到電影的過程,實質上正是觀眾對文學作品以影像為媒介進行選擇和接受的過程。霍建起的《1980年代的愛情》正是對野夫原著的一種“重讀”,霍建起在題材內容、藝術結構、人物形象等方面讓文本的故事鮮活起來,又根據電影的需要對原著進行了新的闡釋。另外,《1980年代的愛情》的改編也再一次證明了,電影對文學的改編引導著觀眾的品位和傾向時,也受著觀眾審美趣味、時代審美風尚的規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