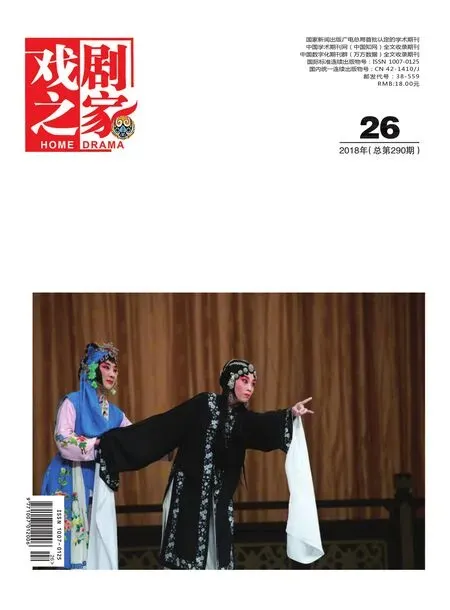《自私的基因》讀書札記
蔣雅君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29)
《自私的基因》是英國行為生態學家里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寫的,首次出版于1976年,動物行為是一書的主題。筆者看的是由盧允中、張岱云、陳復加、羅小舟翻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于2012年9月。筆者主要是想針對第十一章的重要觀點進行分析,道金斯在這一章一開始就說到,我們這個生物是獨特的。我們人類的獨特之處,主要歸結為我們擁有文化。
盡管這本書是生態學領域的書籍,但是文化的傳播有一點和遺傳相類似,即它能導致某種形式的進化。因而這本書也被文化人類學家奉為經典,當然,音樂學家也能從這本書中得到許多啟發。
一切生命都通過復制實體的差別性生存而進化,新的復制基因—Meme—能表達作為一種文化傳播單位或模仿單位的概念。覓母,是模仿的過程從一個大腦轉移到另一大腦,從而在覓母庫中進行繁殖。覓母具有高的生存價值,在文化環境中的穩定性和滲透性。覓母庫里有些覓母能夠取得較大的成功,這種過程和自然選擇相似。
有助于提高覓母生存價值的特性有三個(一般地說與復制基因的特性一樣):長壽、生殖力、精確的復制能力。生殖力比長壽重要,但覓母的傳播收到連續性發生的突變以及相互混合的影響。不能夠進行精確的復制,是通過非遺傳途徑“進化”的,而且其速率比遺傳進化快幾個量級。而通常見諸于文字記載的東西擁有巨大的潛在永久性。
基因不是是自覺的、有目的的行為者。凡是由于基因本身的行為而使自己在未來的基因庫中數量增加的,往往就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所看到的那些有效基因。覓母之間可能進行著某種類型的競爭。時間是一個比存儲空間更為重要的限制因素,是覓母激烈競爭的對象。如果一個覓母想要控制人腦的注意力,它必須為此排除其他“對手”覓母的影響。在肉食動物的基因庫里,相互配合的牙齒、腳爪、腸胃和感覺器官得以形成,而在草食動物的基因庫里,出現了另一組不同的穩定特性。
覓母庫逐漸取得一組進化上穩定的屬性,這使得新的覓母難以入侵。我們與生俱來的任務就是把我們的基因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每過一代,你傳給后代的基因都要減少一半,這樣下去,它們所占的比例會越來越小,直至達到無足輕重的地步。我們的基因可能是不朽的,但體現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基因集體遲早要消亡。
基因一旦為其生存機器提供了能夠進行快速活動的頭腦,覓母就會自動接管過來。大腦能夠進行模仿活動,那時就會形成充分利用這種能力的覓母。人類一個非凡的特征——自覺的預見能力,可能歸因于覓母的進化也可能與覓母無關。自私的基因沒有預見能力,它們都是無意識的、盲目的復制基因,但都將趨向于某些特性的進化過程,這種特性可以成為是自私的,而只有我們人類,能夠反抗自私的復制基因。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預見能力改變
這一章提出的“覓母”這一個概念,十分精妙。曲調、概念、妙句、時裝、制鍋或建造拱廊的方式都是覓母,我們還可以把一個有組織的教堂,連同它的建筑、儀式、法律、音樂、藝術以及成文的傳統等視為一組相互適應的、穩定的、相輔相成的覓母。
文化傳播并非人類所獨有。Jenkins提供新西蘭島上黑背歐鳥的例子。小鳥“發明”的新歌是由于他們模仿老歌時的差錯而形成的。Jenkins把這種新歌的起源稱作“文化突變”。但人類的文化傳播并不是遺傳的結果。
我們自己的物種才能真正表明文化進化的實質,語言僅僅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罷了,時裝、飲食習慣、風俗等實際上與遺傳進化無關。我們的文化發展是我們有意識地、自覺地。例如當下非遺活動的進行,為許多快要消失的文化“保駕護航”,通過國家干預的力量去遇見快要消失的將來,在當下可以保存下來。此外,我們人類發明了文字,可以將信息記錄下來,不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改變成為不朽的流傳。
覓母應該被看成是一種有生命力的結構,這不僅僅是比喻的說法,而是有其學術含義的。一種文化特性是按有利自己的方式形成的。借用覓母這個概念,能夠幫助我們在面對文化事項時,能夠有更寬闊的視野,能夠更加有力地透視文化底層的“覓母”。
在人類文化傳播中,有一類極有意思的現象,就是文化母體,例如同宗民歌,一個音樂曲調在不同地區傳唱開來,在不同的時代里流傳,這個母體會發生變化,但是其基本內核不會發生改變,即使相隔幾萬里,仍然能看到其本質不會改變。例如我國多地流行的《茉莉花》,不同的流傳地會將《茉莉花》曲調外形改變,甚至有的聽起來面目全非,但是細細分析其結構,會發現《茉莉花》最后一句過板淘的結構都保存下來了。這樣一個結構就可以看作是一個極具生命力的“覓母”。文化的傳播和遺傳有些相似,它能導致某種形式的進化。這樣一個覓母之所以能在文化長河中完整留存下來,代代相傳,歸因于我們是有自覺意識的人,跟基因相比,我們有超越時空的能力,將自己的文化記錄保存下來。這是我們不同于基因地地方,我們能將自己的優秀文化代代相傳,甚至不朽地保存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