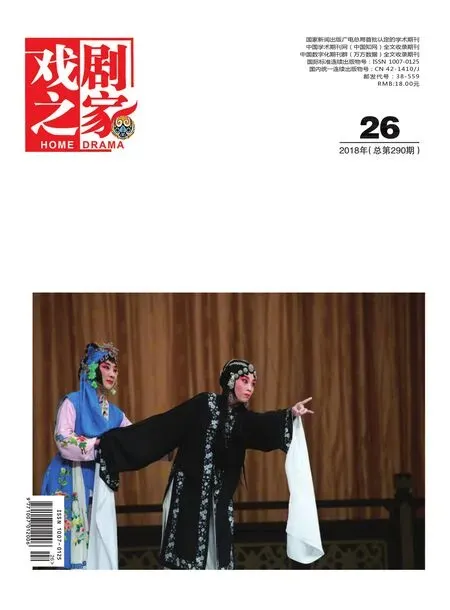《聊齋志異》中的報恩情懷
張兆菲
(江蘇師范大學 江蘇 徐州 221116)
一、報恩故事的類型
《聊齋志異》中的神鬼狐妖摘去法術外衣后,他們的精神內核與普通人非常相似,因此,它們的報恩方式也與普通人相差無幾,只是在報恩行為上略顯神通。本文以報恩帶來的結果將《聊齋志異》里的報恩故事分成五大類,以便清晰探尋作者的報恩情懷。(一)解決困難。《聊齋志異》中的受恩者在報恩時,基本都以恩主的需求為主。蒲松齡對那些不顧恩義的堂堂為人者,常發出這樣的感慨:“人有慚于禽獸者矣。”[1](二)贈物送金。在報恩故事中,恩主大都是普通百姓,而受恩者多為狐鬼精怪,這些狐鬼精怪常贈具體的金物來回報恩主。(三)結姻牽緣。書中報恩類的婚姻故事大致有一定的模式:受恩者為報答恩主,常以身相許結為婚姻;或者化為人形,結百年之好。當受恩者是年邁的長輩時,便將家中的侄女或女兒許給恩主為妻。更甚者,為了報恩化作月下老人,使有情人終成眷屬。(四)延命成仙。當恩主性命堪憂時,受恩者往往舍身相救,也有受恩者將法術傳授給恩主,或使恩主成仙的,這些都是常見的模式。(五)功成名就。在《聊齋志異》中,助人成就功名也是一種報恩方式。蒲松齡雖在科舉上蹉跎大半生,但他筆下人物依然為功名努力。可以說,許多作品中的主角都是作者某種理想的外化。
二、報恩故事流露的情懷
經過以上對《聊齋志異》報恩故事類型的梳理,我們可以試著挖掘蒲松齡在“報恩”這一主題中所反映的報恩情懷,分析作者的創作心理,透視狐鬼精怪報恩行為所反映的現實生活。
(一)示孤憤之情。《聊齋志異》承襲了我國發憤著書的寫作傳統。腐朽的官僚、橫行的地痞等,都使蒲松齡深惡痛絕。書中的孤憤還包含對現世不公、道德失衡的無奈,才華橫溢的蒲松齡無法在科舉考試上功成名就。在《葉生》一文中,蒲松齡借葉生這一人物形象表達他的痛苦。此外,蒲松齡的孤憤之情還表現在很多方面,有對愛情的崇仰卻無法實現的痛苦,有渴求知音而苦苦尋覓的孤獨等。故而,蒲松齡把心中的“理想社會”寄托在了《聊齋志異》之中,這部小說成為作者抒發悲憤情懷的物質寄托。
(二)勸善諷世之情。《聊齋志異》敘述了較多因果報應故事,蒲松齡之所以這樣描寫,其目的在于勸善懲惡。明清之際,社會風氣日益不堪,很多出身儒家的文人,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時體現出勸善懲惡的思想內容。蒲松齡就是典型的文人之一,他在《聊齋志異》中懷著勸善懲惡的救世婆心,鼓勵人們多行善事。
蒲松齡曾以“二十年來,習俗披靡”[2]來表達他對世風日下的社會現實的痛心,他有意借《聊齋志異》來勸世醒世,欲圖復歸淳厚古風,故而書中多借鬼怪寫人,并常發出人不如鬼怪的感嘆。在《二刻拍案驚奇》中凌檬初也有類似的感慨:“其間說鬼說夢,亦真亦誕。然意存勸戒,不為風雅罪人,后先一指也。”[3]蒲松齡巧妙地把花妖狐魅世界與現實世界融合到一起,以飽含深情的筆墨書寫知恩圖報的故事,廣泛運用因果報應觀和中國傳統的善惡報應觀念,以此對抗現實世界的昏暗與污濁。
(三)承知恩圖報之情。在蒲松齡眾多作品中,或多或少都體現了對報恩美德的繼承。在《聊齋志異》一書中,更是對“仁者愛人”的思想有所傳承,“對于遵從儒家道德規范、有大愛的人,都得到厚報,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為報恩的終極目標。”[4]數千年來,知恩圖報思想所宣揚的道德準則和高尚品質,被蒲松齡所珍視,無論是父母養育之恩,還是夫妻扶持之恩抑或兄弟救命之恩,“恩”被認為是所有情義之根源。蒲松齡在作品中表達出的那些重情重義、知恩必報的道德風尚,也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寶貴的精神財富。羅敬之先生曾贊嘆道:“志異之所以能傳誦古今,流播中外,即是其深具雄厚的道德力量。”[5]
三、結語
《聊齋志異》的“報恩”故事中,傳達了一些值得被人們永遠珍視的道德規范。蒲松齡通過報恩作品,集中表現出他的儒家道德理想,借作品中知恩圖報的故事,抨擊頹敗的世風,力圖救世。雖說這包含一定的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消極意味,但我們也不能否認蒲松齡對“報恩”的大力提倡,具有提高民眾的道德素質,挽救社會風氣的積極作用。《聊齋志異》中的報恩作品雖大多帶有一種理想化的色彩,但這是作者對現實生活中美好品質的集中和概括,同時也是他在落敗的現實中對美好人性的憧憬與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