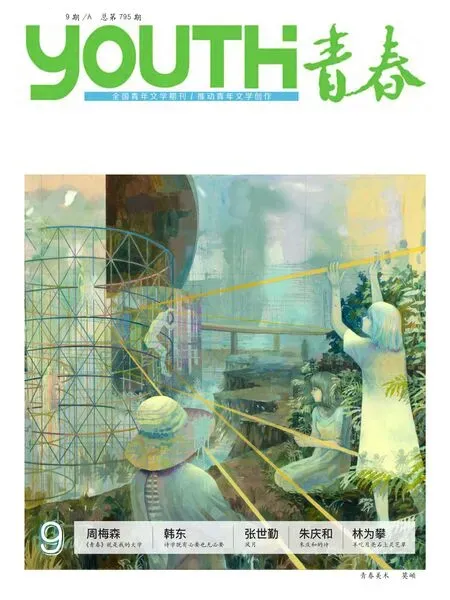門 神
一
我對薛有福最初的印象,是他們家大門上貼的那兩個門神——深紅色的正丹紙上畫著兩個穿著花里胡哨的大胡子。那時我上小學三年級,已經搬去城里住,只有在大年三十那天,會跟隨我爸回老家薛鎮貼春聯。那天我們搬了梯子,把最后的一張出門見喜貼在門口的電線桿上后,就準備返程回家了。農村里年味很重,站在大街上,不時能聽見二踢腳的聲音,聲音過來沒多久,便能聞見刺鼻的火藥味,有時還會混合著油煙味,吸進鼻子里,我爸告訴我,那是油炸酥菜的氣味。以前出了正月十五,才算把年過完,在此期間,為了囤一些食物過年,老人會用面糊裹上土豆條、蘿卜餡、豬肉、豆腐、魚,然后下到油鍋里炸,炸好之后放在干燥陰涼處,能保存很久,直到出正月。
我就是聞到了油煙味才找到薛有福家門口的。他媳婦正在家門口炸酥菜,灶臺是用磚頭堆起來的,上面架著油鍋,下面燒著柴火,油煙呼嚕呼嚕地往外面飄。他一邊被油煙嗆得咳嗽,一邊把兩張門神貼在雙開的木門上,貼好后,他退后幾步,站在門前觀摩了幾秒鐘,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門口的另一邊,鄰近大街上,停著一輛他新買的摩托車,整個車身是藍色,只有后座的皮墊子是黑色,車身油桶的側面印著一行字母:SUZUKI,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時我在班里干語文課代表,認識的生字和成語比其他同學加起來還要多。但面對這行字母,我按照拼音的發音,拼了好久都沒有拼出來。
薛有福看到我,便朝我招手,叫我的小名。當時我還不認識他,但他認識我。當我朝他走過去的時候,他從他媳婦油鍋旁邊的竹筐子里,捏起了兩個炸酥菜遞給了我。他說,你得叫我三叔。于是我叫,三叔。他把酥菜給我,我接過來咬了一口,外面一層面糊是脆的,咬下去咯吱一聲,里面的土豆已經熟透了,軟乎乎的,嚼起來很香。薛有福的媳婦是我們那兒典型的農村婦女,沒有什么特點,但薛有福和村里的其他男人很不一樣,他的頭發梳得锃亮,皮帶扎在外面,穿著發亮的咖啡色皮衣,靠在摩托車旁邊跟我說話。那時候,農村里有摩托車的都是少數,就連城里也不多見。
我吃完手里的酥土豆,他又給我拿了幾個炸的蘿卜丸子,但他媳婦好像不太樂意,他沒有管他媳婦的臉色,而是塞到我手里,說,拿著吃。說完,他轉過身去,擦著一根火柴,把腳底下的一堆廢紙點著,那一團廢紙在火里燃燒的時候,來回擺動,好像身體在顫抖。我看見燒著的紙上畫著的人像,和他門上貼的門神一模一樣。我走過去,指著火堆問他,為什么燒這些。薛有福說,這是揭的去年的,得燒了。我又問為什么,他說,是對門神的尊重,一年到頭,都得靠門神保佑。我指著門上新貼的那張,問薛有福,那是誰。薛有福說,那叫神荼,你知道不。我搖搖頭。薛有福從地上撿起一小塊褐紅色的磚頭子,在家門口的水泥地上寫下兩個字:神荼。于是我念,神茶。薛有福糾正我說,神,tu。之后他又問我,你上學考了多少分。我說,語文九十九,數學九十六。薛有福說,那考得不孬,可得保持住,考上了大學,以后好坐辦公室。他說完,我突然想起教室后墻的黑板報上寫的幾個大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但薛有福卻告訴我了另外一個道理:為坐辦公室而讀書。
沒過多久,我爸就找過來了。他看到我在薛有福家門口吃酥菜,便上來客套了兩句。看見印著拼音的摩托車,我爸笑著問,新買的啊。薛有福笑嘻嘻地回應,年前買的,然后又補了一句,不值錢。后來,回去的路上,我爸告訴我,在農村,種一年的地都買不起一臺摩托車。于是我就問,那薛有福為什么說不值錢。我爸想了一會兒,也沒有回答我。他可能不知道該怎么回答,便跟我說,薛有福不在農村種地,他在城里開了個玻璃店,給別人劃玻璃、裝鏡子,掙了不少錢。
二
我剛上初中那年,進入了新世紀,我們那個小縣城里的網吧像春筍一樣拔地而起。在每一個背誦完化學元素周期表的午后,我都會偷偷地鉆進黑網吧里,打開紅警,操縱世界大戰。結果是我的學習成績直線下滑,從班里的前幾名掉到中游。我爸因為這件事情,被老師叫去學校開了好幾次會。我爺爺知道我成績下滑,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農民熱愛土地,工人熱愛機器,你要熱愛學習。
初三那年寒假,我爸把我鎖在家里,監督我備戰中考。即使我面對著中考模擬試卷,心里還在盤算,對付蘇聯和伊拉克這種國家,是應該用德國的坦克殺手還是韓國的黑鷹戰機。于是我每天趴在燈下,看似在學習,其實心不在焉。終于在大年三十這天,我爸才同意給我放一天假。但我并沒有時間溜去網吧,因為他要帶我回薛鎮貼對子。
那時候過年,很多人家已經不再貼門神,而是改貼“福”字和對子了。但薛有福家,每到大年三十,總還是會換上新的門神,從神荼郁壘,到關羽張飛,再到秦瓊尉遲恭,他們家的大門上,換了一批又一批的門神。
三十那天一大早,我和我爸來到薛鎮,路過薛有福家門口的時候,看見他家大門緊閉,但門上已經貼好了新的門神。秦瓊和尉遲恭雙手各執兵器,莊嚴威武,眉毛呈倒八字,目視斜前方。我們從秦瓊和尉遲恭身邊走過,他們兩個一動也不動。我對我爸說,薛有福他們家貼得還挺早的。我爸說,薛有福在城里忙著賣火鞭,擎等著掙錢。
貼好薛鎮老家的春聯后,我們便返回城里。回去路上,我爸騎著摩托車載著我,繞過北街的友誼廣場,一路往南去。我問我爸去哪兒,他說去找薛有福買火鞭。
那已經是大年三十的下午,街上的門市部都關了門,只有幾家小賣部門口還擺放著酒箱、牛奶箱和糕點盒子,兩列箱子和盒子擺放在門口,店里卻黑燈瞎火,屋里的盡頭處擺著老式電視機,小孩坐在一旁,收看往年春晚小品的集錦。這種人家,大概就是在小賣部里過大年三十了。
薛有福的火鞭鋪子就離一家小賣部不遠。說是火鞭鋪子,其實是用軍綠色厚帆布和鋼管搭起來的棚子,五面圍得嚴嚴實實,座落在一片空地上。這種棚子平常日子里沒有,只是到了臨近過年的時候才會出現,都是用來賣火鞭、禮花和炮仗的。薛有福已經是第二年搭這種棚子了,去年過年時候,他在城邊上搭了個小的,掙了不少錢。今年剛入臘月,薛有福就去托關系,陪人喝了好幾頓大酒,終于把城里搭棚子的準可證給拿下來了。拿到準可證的那天,薛有福又擺了一場,專門致謝,當晚喝了二斤白酒,騎著摩托車回家的路上,沒看清道路,栽到路邊的下水溝里去了。不過幸好人沒大事,只是胳膊上打了個石膏。這場意外并沒有耽擱薛有福辦事,他還是雇人搭起了棚子,而且比之前的大一倍,又囤了很多貨物,不僅有火鞭,還有禮花。
那天,我和我爸一起走進薛有福的火鞭鋪子里,他就坐在門口,抱著富光牌水杯,里面放的茶葉能占到杯子一半的容量。我們走進去時,他正滿臉呆滯,看到是我們,勉強擠出了一點笑容。我爸上去便問,生意挺好的吧,薛有福沒說話,吧唧著嘴,喝了一大口茶,嘴里吃進幾片茶葉,他噗噗噗吐了三下,把茶葉吐回到杯子里,說道,沒法兒干。他說話時眉頭緊皺,倒八字的眉毛像是門神上的秦瓊。我爸問他,怎么回事。他說,小年前下了一場大雪,棚子沒蓋嚴實,火鞭都受潮了。薛有福面前的玻璃柜上擺放著禮花和各種炮仗,那大概是大雪過后僅有的幸存品。聽他這么說,我爸嘆了一口氣。薛有福又說,也就這些禮花還能賣。他大概也猜出來我爸來的意圖,于是從身后大紅色的火鞭堆里取出一掛,放在玻璃柜上說,你看看能用就用,拿走就是。他說這句話,是不用給錢的意思。我爸伸手去摸,明顯能感覺到受了潮。我爸說,你擱著,看看年后能干了點不。我爸沒要那掛火鞭。
臨走前,薛有福又叫住我,從柜子上拿了兩盒小蜜蜂,想要送給我。我作為一個已經開始打電腦游戲的中學生,理所當然地認為這種東西是小孩子才玩的。我忙對薛有福說,不要了,我早就不玩這個了。薛有福看了看我,才注意到,我已經不再是個小孩了。時間在大人面前過得不快,只有在小孩面前才蹭蹭地往前跑,因為小孩要長個子。薛有福打量完我,把小蜜蜂放下,又拿了兩盒黑蜘蛛,遞給我,說,小男孩都喜歡玩這個。薛有福堅持要給我。我看了我爸一眼,我爸點頭給我示意,說,拿著吧。于是我就接了下來。
回到家后,我爸順嘴和我爺爺聊起了薛有福開火鞭鋪子的事情。我爺爺說,那怪不得呢。我爸問,什么事。爺爺說,今天去東市場上,聽老劉講,薛有福從東市場進貨,賒著錢,找他要錢,就一直拖著,今天年三十,一大早去他家,看見大門上貼著兩塊嶄新的門神,他這是成心不想給。
我當時沒有聽懂,后來才知道,老輩有個說法,叫年三十貼完門神,家里的錢財就不能再進進出出了。有欠債的人,故意在三十那天一大早就貼上門神,是躲債用的。債主要是追上門去,便能用老輩的風俗回應。即便是這樣,有的債主也不吃這一套,畢竟門神是紙上的,人才是活的,誰家都得過年,該要債的照樣要。那天東市場的老劉找上門去,只有薛有福的媳婦和兒子在家里,問薛有福的火鞭鋪子在哪,他媳婦死活不說。
爺爺說,那看這個樣子,薛有福年三十晚上都不敢回家了。
那天趁我奶奶和我媽包餃子的時候,我拿著薛有福給的黑蜘蛛,對我爸說,我去外面放擦炮。出門之后,我就奔到網吧里,開了一局紅警。我擔心自己在外面逗留時間太長,被家里發現,也沒有戀戰,一局之后就離開了。那時候天快黑了,網吧里只有兩三個人,彼此坐得很遠。網管孤獨地坐在前臺,電腦里不時傳來QQ來消息的聲音,他面無表情地敲打鍵盤,讓我想起同樣孤獨的薛有福。
回到家后,桌子上已經擺好了八個菜,有涼有熱,有素有肉。電視機調到了中央一臺,在播放廣告,我奶奶和我媽討論,她們說今年是倪萍主持的最后一屆春晚了,剛說完,畫面就切換到了倪萍。倪萍開口說話時,外面突然響起了一陣鞭炮聲,噼里啪啦的,持續了將近半分鐘。那半分鐘里,只能看見電視機上倪萍的嘴巴在動彈,根本聽不清她說什么,我們一家人坐在堂屋,對著電視機看,像一群聾啞人在看電影。
此刻如此喧囂而又安靜。我又想起了薛有福,他應該還在火鞭鋪子里。這個時候,街上已經沒有人了。他坐在軍綠色的帆布篷里,被一堆受了潮的火鞭包圍,聽著外面傳來噼里啪啦的鞭炮聲,倒數著舊年的最后幾個小時。也或許,他會拿上幾盒小蜜蜂和黑蜘蛛,走去附近的小賣部里,送給別人家的小孩,然后坐下來,和他們一起觀看聯歡晚會。
他是怎么度過那個除夕夜的,我不知道。只是春晚播出的過程中,外面時不時地會響起禮花爆破的聲音。跑到院子里,抬頭望上去,能看見一支火光沖上天,各種顏色先后綻放。也不知道薛有福有沒有看到這些煙花。
三
我二十歲時,還沒有讀大學。和我同齡的人,讀技校的,都快要畢業了。當時我堅持要考電影學院,甚至立誓,考不上就不剪頭發。留了將近一年的頭發,拖到脖子邊上,覺得自己像個搞藝術的。學校門口的理發店里,剪頭的大哥勸我說,你這個頭發,我給你燙一下,你就是貝多芬。我當時有過心動,因為我最喜歡的一個南斯拉夫導演就披著一頭長卷發。在我還沒決定要燙頭的時候,我們班主任把我扯到了辦公室。他是個謝頂,頭頂上都禿光了,只剩下耳邊一圈茍延殘喘,仿若盤山公路。我們同學給他起外號,叫他謝頂,或謝老師。當時謝頂惡狠狠地盯著我的頭發說,你給我把這個二鬼子頭給剪了,我說我不剪,頭發是我身體的一部分,你憑什么干涉我的身體生長。謝頂說,就憑我是你老師。我依舊說,不剪。他講道理講不過我,就打電話把我爸叫來了。謝頂當著整個辦公室所有老師的面,把我罵了一頓。我爸當時站在一旁,一句話都不說,我不知道他是在生氣,還是在羞恥,又或者是在思考。我正準備再次跟謝頂辯駁時,我爸突然從辦公桌上抄起一把剪刀,兩步朝我走過來,一手揪住我的頭發,另外一手揮舞剪刀,咔嚓一聲,一把頭發從他手心滑落。與此同時,他咬牙切齒地喊道,你再給我犟!我反應過來時,想要躲開,于是在辦公室里四處亂竄。我爸依舊緊握剪刀,隨時朝我刺來,辦公室的老師忙著拉架。最終,我屈服了,跟著我爸去理發店,花了八塊錢,剪掉了頭發。
那年過年期間,我感覺很壓抑,經常白天跑出去,到半夜才回家,沒地方去的時候,我就跑去老家薛鎮。薛鎮還有我們家的宅子,只是沒有住人,那兩年也沒有租出去,就閑在那里。離我們家沒多遠,就是薛有福家。那是個大年初五,我走在薛鎮的路上,聽見兩個農村婦女在聊天。其中一個說,薛有福在礦上偷金子,讓人給逮住了。她又說,薛有福跑去云南跟人挖礦,在施工隊里開升降機,用刀子劃破大腿,把小金塊塞肉里。我躲在一旁,裝作在玩擦炮,以便聽她們講故事,結果越說越驚心動魄,但也越離譜,我一想,她這講的不是闖關東嘛。我從她們身邊離開,直奔薛有福家。
到他家門口時,門上的門神赫然站立。仔細去看,會發現兩邊不太對稱,一高一低,有一邊還滿是褶皺,估計是貼得不用心。我推開門,朝里面走去。薛有福的媳婦正在屋里生爐子,她蓬頭垢面的,穿著臟兮兮的花棉襖,聽到我的腳步聲,轉過頭來。我說,嬸子,我找三叔。她看著我,愣了一下,好像沒認出來我是誰,但還是給我指了指,說,他在東屋。我轉而走去東屋,東屋的屋門是雙開的,門上有玻璃,左右兩邊各貼著明星海報,一個是唱歌的周杰倫,另一個是打球的科比,左右對稱,和大門上的門神如出一轍。我不禁覺得有些好笑,這兩個人像是專門守護東屋的門神。
我走進去,看見薛有福半靠在床上看電視,電視機里在播《西游記后傳》。我進門便叫三叔。薛有福當然認得我,他看見是我,忙說,呦,你怎么來了。他想站起來迎接我,但只是做了個起身的動作,然后指著大腿說,年前干活給碰傷了,不好站起來。我說,不用,三叔你坐著就是。我朝他大腿上看過去,黑色棉褲的一條褲腿是經過改造的,空出來的腿上纏了一圈又一圈的繃帶。一看到這,我便想到剛剛聽到的談話,說薛有福偷金子的事情,不知是真是假。我還在想著這事時,薛有福開口問我,下學了嗎。
這是我們那兒的說法,下學了嗎,意思是問從學校里出來了嗎,也就是說,還有沒有在上學。我回答說,還沒。薛有福又問,在哪上大學呢。他以為我在讀大學。我說,還沒考上,在復讀。薛有福一算,覺得也不對勁。于是我先說,第三年了,高六。薛有福有些驚訝地看著我。我說,我想考電影學院,考不上,我就不上大學去。薛有福流露出不能理解的表情,但還是繼續問,你考電影學院,得考多少分。因為他兒子也在讀大學,前兩年剛剛經歷過高考,他大概知道考試分數。我說,考電影學院,得先考專業課。薛有福又問,那專業課怎么考。我說,就是考你看的電影,還有寫的文章。薛有福噢了一聲,然后說,你都看什么電影。我想了想回答說,都是藝術電影。薛有福便沒再說話了。
電視機里還在播放《西游記后傳》,正演到白蓮花被押在刑場上,千鈞一發,孫悟空從天上扔下來一塊黃布,上面寫著:神靈不樂,速放白蓮。刑場上的官員被嚇傻了,趕緊宣布釋放白蓮花。于是,喬靈兒和白蓮花重新抱在了一起。這一段很精彩,我和薛有福都盯著電視機看。屋里很安靜,我倆誰也沒說話。過了好一會兒,薛有福才對我說,這個電視拍的不孬。然后問我,你以后也能拍這個不。我說,不比這個差。
我又想起來他屋門口的周杰倫和科比,便問他,門口上的畫是你貼的不。薛有福以為我問的是大門上的門神,于是說,我腿沒好利索,讓小新(他兒子)貼的,他干活不行,貼得邋邋遢遢,不板正。然后又補了一句說,這一年到頭,都還得靠門神保佑,門神可別生氣。我才意識到,他說的是門口的門神。于是我重新問,東屋門上的畫是你讓貼的不。薛有福這次聽明白了,說,那是小新的畫,他娘貼的。我又問,你知道那是誰不。薛有福說,管他是誰,我不認的。我笑著說,也是門神。薛有福跟著也笑了,補了一句,外國門神。
然后,薛有福又跟我聊了一會兒考試的事情,他鼓勵我說,有理想很好,爭取今年一定考上。我說,我也是這么想的。薛有福又說,等以后我看你拍的電影。我看他笑得很燦爛,于是說,好。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次約定,總之很草率,也很荒唐。
那天晚上回家后,我收拾行李,準備第二天去北京考試。我爺爺給我拿了五百塊錢,讓我考試留著用。我跟爺爺說,我今天去薛有福家了。爺爺問,給他拜年了嗎。我說,沒磕頭。我爺爺說,大過年的去,你不磕個頭不像話。我發現我把這事給忘了。
我爺爺又說,薛有福是個講究人,也是個場面人。前幾年有錢的時候,要場面,我回薛鎮,他都給我玉溪的煙吸。這兩年沒掙著錢,但也要場面,你過年去他家,不給他磕頭,他得生氣。我想了想,應該不會,因為我們聊的很歡樂。最后告別的時候,他還想出門送我,但站不起身來,就坐在屋里面,看著我走出東屋,離開他家。
大年初七的早上,我去北京參加考試。一周后,我進了復試,又一周后,公布三試名單,我落榜了。
四
大概有三年多,我都沒有再見過薛有福。再次聽到關于他的消息,是在正月十五,我爸和我爺爺聊天,說薛有福的媳婦讓大車撞死了。具體怎么回事,誰也沒見到,都是口口相傳。據說,薛有福的媳婦大晚上騎著電動車,從村子口往大馬路上去,半夜里,大貨車司機沒看清路,連人帶車一起撞了。
那時候我正面臨大學畢業,上半學期已經在一家廣告公司實習過了,所以也不著急返回學校。我本來在想,要不要回趟薛鎮,去看看薛有福。我突然想起來了那個荒唐而草率的約定。薛有福曾經說,他以后要看我拍的電影。當然,我猜測,他自己都把這句話給忘了,但我還記得。事實上,我沒有考上電影學院,而是去了一個三本院校,讀的專業叫廣播電視編導。我們整個班里,只有兩個人看過庫斯圖里卡的電影,這讓我覺得很傷感。大三大四這兩年,我跟著學校里的老師,拍了很多次婚慶和宣傳片,唯獨沒有做跟電影相關的事情。
當然,這些都和薛有福無關,他此時正沉浸在喪親的痛苦中。我不是不忍心去打擾他,而是我不知道該怎么去打擾他。
后來聽我爺爺說,薛鎮的人都傳言,說薛有福的媳婦,是他們家門神克死的。
他媳婦出車禍是在年后。年前,薛有福和他媳婦整天打架,好像是因為薛有福在外面胡搞,被他媳婦抓到了。他媳婦天天罵他,他也理虧,就不還嘴。有一回,約著村里的伙計在家里喝酒,喝多了,說起了關于女人的事情。他媳婦聽見了,又破口大罵,伙計們都在場,薛有福覺得臉上難堪,又趁著酒勁,打了他媳婦一巴掌。他媳婦這下不愿意了。等薛有福酒醒過來,才發現媳婦回了娘家。等了一個星期,都沒回來,薛有福買了煙酒糖茶,去娘家邀她回來,媳婦死咬著嘴,說不回。又過了一個月,快到年關了,媳婦還沒回家。薛有福去給媳婦娘家送節禮,順帶著認錯,再請她回家,但媳婦依然沒松嘴。
大年三十那天,媳婦還是沒有回來。那年兒子也在深圳定居了,第一年不回家過年。到了三十下午,天都快黑了,薛有福站在家門口望出去,大街上一個人都沒有,只有鞭炮聲。薛有福便拿出新的門神和熬制好的漿糊,把門神貼在門上,一個人回家里去了。
他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舊時貼門神有個講究,說是家里人都回家了,才能把門神貼上,要是貼完之后,再有人回家,門神不認這個人,不僅不會保佑,還會有災禍。當然,這些沒有科學依據,但村里人信這個,尤其是老一輩的。
三十那天晚上,薛有福貼完門神后,天就黑了,回屋下餃子的時候,他媳婦突然拎著包裹回來了。薛有福自己都沒想到。媳婦說,自己是被娘家人勸回來的。三十當天一大早,娘家人來來回回地勸她說,無論多大的事,都得回家過年,年后再說。于是中午之前,她就從娘家出來了。但她覺得不能回來,因為咽不下這口氣。從娘家出來后,就在路上走,走了好久,都沒有回薛有福家,最后走在路上,實在是太餓了,路上也沒人賣吃的,她知道娘家不讓回了,于是只能回到薛有福家。媳婦說完,鍋里的餃子正好開了,飄浮上來,在水里搖搖晃晃。薛有福給媳婦盛了一碗,媳婦沒再吵架,兩個人一起過了除夕。
至于年后的幾天,薛有福和媳婦也沒再起爭端。據說,薛有福給媳婦徹底認了錯,并立了保證。這件事情好像就翻篇過去了。正月十三那天,媳婦晚上騎電動車回家,讓大貨車給撞了。
整件事情就是這樣。于是村里有老人說,是門神克死了他媳婦。
那時候整個薛鎮,過年貼門神的不過三五戶。大多數人家,都是門心上兩個“福”字,門垛子兩邊一副對子,類似“新春新歲新氣象,迎財迎福迎吉祥”,然后門檐上一則橫批:歡度春節。這是新時代的祈福。大家似乎覺得,有沒有門神,也無所謂。而且,路邊上賣門神像的也越來越少了,很多地攤上只有春聯。要是問他,為什么不賣門神,他說往年進的,不好賣,今年干脆連進都不進了。
薛有福媳婦的喪事辦的很簡單,正月十五之前就完事了。
那幾天里,我實習的廣告公司給我打電話,問我要不要繼續回去工作,我沒有給他答復。因為我并不喜歡那些工作,每天要面對各種PPT,無聊透頂。以前薛有福告訴我,考上大學后就能坐辦公室,可是現在滿世界都是大學生,畢了業都能坐辦公室,圍著一塊辦公桌,像農民圍著一塊土地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不過城市的人管這叫朝九晚五。這種生活不僅讓我覺得無聊,甚至有些絕望。可是更讓我絕望的是,除此之外,我好像沒有別的出路。之前聽一個導演說,想搞電影,必須要去北京。可是北京那個地方,我只在小時候去看過一次天安門升旗,那里和我一點兒關系都沒有。說到底,我心里全是害怕。
在我決定返校的前幾天,我爸讓我開車載他回薛鎮辦點事。那是一個晚上,大街上燈火通明,小路上還是一片漆黑。停好車后,我爸去辦事,我呆在車里等他。
當時已經立春過后很久了,天氣漸漸轉暖。即使是晚上,也不會覺得太冷。我從車上下來,在薛鎮的大街上瞎逛,走著走著,沒幾步路,就走到我家宅子附近。我意識到薛有福家就在前面,于是我又朝前走了幾步。快走到的時候,我心里竟然生起一份期盼,好像是去見一位老朋友,我們好久沒見面了,需要坐下來好好聊聊,我甚至想要把自己內心的焦慮講給他聽,即使他未必能給我指點。走到他家大門口時,看見大門上兩個門神還在那兒,他們面目凝重,一日長于百年。看到他們那一刻,我心里的期盼好像落下來了。我不知道這是為什么,但我停在了門口。我知道,我不會走進薛有福的家里去了。我告訴自己,也許他不在家。突然,我又覺得,如果這時候,薛有福從家里走出來,看見了我,該怎么辦,我是不是要上前跟他打招呼,我需要解釋什么嗎,只是碰巧路過,還是故意造訪?如果他問我近況如何,我該如何作答?復雜的思緒讓我有些不知所措。我決定從他家門前離開,或者說是逃走。
于是,我轉過身去,拐進了一條漆黑的小路,朝停車的地方返回。
五
畢業之后,我去了北京,做過很多份工作,在劇組干過制片助理,在電視臺干過攝像助理,去后期公司,專門給視頻素材合板,又在編劇工作室替小有名氣的編劇搜集資料,總的來說,我沒有離開電影的行當,但一直都是個助理。混了四年,總算穩定下來,在一個影視公司里做策劃。部門的總監給我允諾,說不出兩年,我就能做上策劃經理。因為多次復讀的緣故,現在我已經二十八歲,兩年后就三十了。我想起看電影史的書上講,戈達爾三十歲已經拍出《精疲力盡》,特呂弗三十歲之前就把《四百擊》拍出來了。而我三十歲,就快要當上策劃經理了。我并沒有為此而難過,因為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樣。于是,我抱著辛酸的僥幸度過了在北京的一個又一個夜晚。
有時候我會想起薛有福,即使是在北京的時候。他篤信門神能保佑他,于是一年又一年地在門上貼門神,從未間斷。我不知道門神是不是暗中給了他保佑,但從他的生活條件來看,好像并沒有。最早我認識薛有福的時候,他是薛鎮的有錢人。后來慢慢就不行了。這兩年,聽說混得更差勁。還去深圳待過一年,因為他兒子在那里定居,他把這些年攢下來的錢都給他兒子買房用了。當然,也沒有攢多少。在深圳那一年,他什么事也沒干,呆在家里,身上起滿了濕疹。北方人到了南方,都會有不適應。薛有福更為嚴重,又疼又癢,反復發作。最后,薛有福從深圳回來了。
他一個人住在薛鎮,也不知道在做什么。我聽我爺爺講,整個薛鎮上,只有他一家過年還貼門神。他是如此的虔誠,還是說,他只是懶得改變。我有時候在想,我如果是薛有福,也相信門神的話,是不是要把盧米埃爾兄弟的畫像貼在門上,兄弟兩個,左右各一幅。想到這兒,我就想笑,別人肯定會覺得我有病。但如果真能保佑的話,我也愿意這么干。
我突然覺的,薛有福是真的相信門神會保佑他。我決定過年回家,去找薛有福好好聊聊,說一說自己這幾年的經歷,也問問他怎么樣了。
今年過年回家,遇見了不少老熟人,有同學也有鄰居,都是好久沒見了。甚至年二十七的下午,我去小區門口的超市買蒜瓣兒,碰見了高中的班主任。自從畢業后就沒再見過。我倆迎面撞上時,他一眼就認出我來了,上來就叫我的名字,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是謝頂,我差點脫口而出,叫他謝老師。我努力去回想,實在不記得他姓什么了,只記得謝頂這個外號太響亮。我沒有加上姓氏,直接叫了一聲,老師,我倆寒暄了好幾句,甚至臨走的時候,他對我說,要不要去他家坐坐,就住附近。我忙說,不了不了,還有事。分別之后,我才想起來他打電話叫我爸去學校給我剪頭發的事情,當初我恨他恨得咬牙切齒,他整我整得心力交瘁。大家再見面時,卻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年三十那天中午,我主動請求回薛鎮貼春聯。到那兒后,我先把家里的春聯貼好,然后走去薛有福家,快走到時,我看見他家門口周圍長滿了雜草,好像很久沒人來清理了。再走近時,門口是干凈的,只是雜草長在兩旁。但讓我覺得驚訝的是,薛有福家的大門上貼著兩個大大的“福”字,兩邊門垛子上空著,上面是一副橫批。我看到時,甚至覺得走錯了地方,左右再去看,發現沒錯,這正是薛有福的家。我走上前去,仔細地看,門上還有長方形的印記,已經很淺了,那是以前貼門神留下來的。我沒有想到,他們家的門上竟換成了“福”字。
于是,我敲了敲門。過了很久,都沒有人回應。大街上有兩個小青年路過,他們和我年齡差不多,只是留在了農村。他們看見我在敲門,其中一個對著我說,薛有福一大早就把對子貼好,回城里上班去了。說完,他們繼續走。我叫住了他們問,薛有福去哪里上班了,剛才那個人便說,在小區給人當保安,看大門。我又問哪個小區,那人說不知道。我繼續問,他家怎么不貼門神了。那人說,去年就沒貼了。另外一個人說,前年也沒貼,沒貼門神都好幾年了。幾年了,我追問。至少得三四年了,那人回答。我算了算日期,好像就是薛有福媳婦去世那年。我又回想起我爺爺說過,整個薛鎮就只剩下薛有福一家在貼門神了。
我越想越覺得混亂,實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難道說,因為薛鎮上有人傳言,門神克死了薛有福的媳婦,他就不貼門神了,這會不會是真相。我不知道。
回城里的路上,街邊有商店都還開著門,遠處有鞭炮聲不時傳來。最近幾年,路上的那種火鞭鋪子已經沒有了,因為影響市容,不允許搭。我路過友誼廣場的時候,想起薛有福以前的火鞭鋪子就在離這兒不遠的地方,那里現在新建起了一棟大樓,還是個高檔小區。
到家后,我奶奶和我媽正在包水餃,她們面前是一臺液晶電視,掛在墻上,看的還是中央一臺。餐桌上已經擺好了準備的飯菜,有涼有熱,有素有肉,一切好像都沒變。窗外時不時傳來鞭炮聲,讓人聽不清電視機里在說什么。
等鞭炮聲過去,我爸從屋里拿出一瓶白酒,吩咐我起開,分別倒上。我跟我爸說,今天回薛鎮,看見薛有福家的大門上貼了福字。我爸沒接話。我意識到,他沒聽懂我在說什么。我又說,薛有福他們家以前都貼門神。我爸說,現在哪還有人貼門神。我一邊倒酒,一邊聽我爸嘮叨。他說,現在用不著門神了,你看咱小區,都有保安,保安就是門神。我一想,突然覺得,我爸說的很對。我又想起白天的遭遇,那個薛鎮的小青年說,薛有福在干保安。這么看來,薛有福就是門神。
他這么相信門神,最后成為了門神。也許這就是真相。我倒酒時走了神,白酒從酒杯里溢出來了,灑在桌上。我這才回過神來,趕緊用抹布擦干。
我又想問我爸,薛有福到底是什么時候開始不貼門神的。話剛說出口,外面又響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聲,持續了很長時間。北京已經禁燃了,我們家鄉還沒有,不過應該也快了,這算是禁燃之前最后的狂歡。鞭炮聲響完過后,外面又傳來了禮花爆破的聲音,我朝窗戶外望,有好幾束火光沖上天空,然后炸裂開。我走到窗邊去看,那些火花四散開來,和以前過年時一模一樣,比如,薛有福躲債的那個除夕夜晚。今年的此時此刻,薛有福應該坐在某個門衛處過除夕吧。往年和今年,這里和那里,又有什么區別呢。如果薛有福也在看的話,我想,我們看到的煙花,應該是同一片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