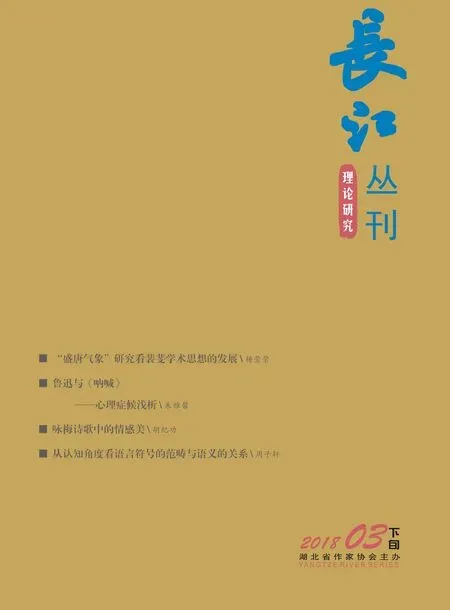萬歷朝鮮戰爭和薩爾滸戰役中明軍的比較研究
■李博宇/西北大學附屬中學
一、萬歷朝鮮戰爭經過簡述
日本安土桃山時代,是日本史上戰火紛亂之時。一代梟雄豐臣秀吉在織田信長死后,接過了統一日本的大旗。成功統一日本本土后,豐臣不滿足于日本既有領土,開始覬覦明朝。而要對明有所企圖,就須先征服朝鮮。于是,豐臣向朝鮮國王致國書,直言“明年將大舉假途,直犯上國”①。1592年4月,豐臣秀吉派遣以小西行長為首的十余萬日軍侵略朝鮮,浹旬之內,朝鮮“三都淪陷,十八道瓦解”。應朝鮮李朝所請,宗主國明朝派遣以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為經略、李如松為提督的4萬多明軍渡過鴨綠江援朝。明軍于1593年正月初八收復平壤,初十夜收復開城,基本匡復朝鮮絕大多數領土,救回被俘王子。于是中日議和,明軍于1594年正月班師,第一次入朝作戰結束。
1595年,和議失敗,明朝派遣以兵部尚書邢玠為總督軍門、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鎬為經略朝鮮軍務,率領3萬多明軍入朝作戰。在經過稷山之戰獲勝、蔚山戰役先勝后輸、鳴梁海戰與露梁海戰等多次戰役之后,戰局陷入膠著狀態,加上豐臣秀吉于1598年病逝,軍后勤不穩,無心戀戰,只得退。中朝聯軍取得最終勝利。
二、薩爾滸戰役經過簡述
明朝末年,努爾哈赤在東北崛起,逐漸統一女真各部。1618年,他在盛京發布“七大恨”告天,正式向明廷宣戰。明廷派遣楊鎬為遼東經略,李如柏為總兵官,率領包括朝鮮、葉赫一并12萬大軍于1619年三月初一兵分四路進攻后金都城赫圖阿拉。努爾哈赤率軍將四路大軍逐一擊破,五天之內明軍三路覆沒,一路敗退,后金軍完勝明軍。
三、兩次戰爭中明軍的不同表現淺析
從萬歷朝鮮戰爭到薩爾滸之戰,其間相隔不過二十年。從兩次戰爭的結果看,明軍和朝軍聯手,擊退日軍,使得日本吞并朝鮮,進而覬覦中國的企圖破滅,可謂不世之功。但二十年后,明軍在與后金軍的較量中,卻幾無還手之力,十幾萬大軍頃刻覆沒。這樣的結果反差,令人吃驚,值得后人深思。
從今天的立場看,兩場戰爭對明朝而言都是生死攸關的。援朝抗日,不但是維系宗主國的地位,也是自保。如果一旦失去朝鮮的屏障,明廷將直接面對日本的挑戰,再無寧日。而薩爾滸之戰則是明、金雙方在關外爭奪戰略主動權的一戰,幾乎傾盡關外精銳的明軍如果失敗,其結局是不言而喻的。今人評價戰事,往往以所謂正義戰爭、非正義戰爭而論。其實戰爭本身固然有道義,但是結果是不可回避的。再正義的戰爭,如果沒有實力為后盾,也是打不贏的。因此,有必要從戰略態勢、軍隊素養、后勤補給、臨陣指揮等多角度,全面回顧總結明軍在這兩次戰爭中的表現,才能對兩次戰爭不同的結果做出合理的解釋。
萬歷朝鮮戰爭前,明神宗已經親政十年,也就是說,距張居正去世已有十年。不算張居正當朝,那么這十年是萬歷主政早期,政治還不似其晚期那般松懈。但是對于日本的情況,明廷缺乏了解。以至于全國上下都一時找不到精通日語且忠誠于明廷的可用之才,這為其后沈惟敬的得勢及垮臺埋下了伏筆②。當然,日方對明廷也缺乏了解。因為長期內戰,日本早已不似隋唐年間那樣頻繁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對中國頗為生疏,狂妄地貿然發動侵朝戰爭本身就是例證。
薩爾滸之戰前,明廷對努爾哈赤建州女真相對倒反而更加熟悉一點。努爾哈赤祖上即和明朝往來密切,雙方可謂知根知底。但是在薩爾滸之戰前,努爾哈赤主要精力在統一女真各部,和明軍尚無大規模摩擦沖突,這是明軍戰略上最大的盲點。而努爾哈赤因為始終以明軍為假想敵,因此準備充分。
在萬歷朝鮮戰爭中,明軍初期處于極其不利的局面。因為朝鮮淪陷太快,明軍沒有立足之地和足夠的補給,加之最初入朝作戰的史儒、祖承訓兩部輕敵,都全軍覆沒。痛失兩軍,促使明廷以宋應昌為經略,派出李如松等干將入朝。明軍從遼東、宣府、大同、江浙、四川各地抽調精銳部隊,并配有火銃和火炮,這些精銳部隊長期都在一線作戰,經驗豐富。雖然日軍多是經歷戰國時代洗禮的老兵,但是平壤戰役,明軍成功破城,大敗日軍先鋒小西行長部,一舉扭轉局勢。由此可見,從軍隊素養,到武器裝備,明軍中的精銳部隊,都不遜于日軍。日軍大多數都是在戰國時代錘煉出來的武士,并且也配有當時全世界領先的火繩槍,但是這些優勢對于在成建制的明軍面前不復存在。
明朝的火器,如佛郎機炮,多由西方傳入。佛郎機,本是明代對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統稱。正德末年,白沙巡檢何儒在來華的西班牙船上看到了西洋火炮,其性能優于當時中國的火炮,于是便動員船上中國籍的槍炮匠上岸,仿造了第一批西洋火飽。此后明軍的大將軍炮等其他炮型也多由此演變而來。明軍火炮因此有所提升,但是也存在不少問題,火器質量參差不齊。有的銃管有炸裂的危險,致使士兵提心吊膽,甚至不敢雙手握銃以作精確瞄準,有的炮彈與炮口尺寸不合,有的則是導火線無法點燃③。日軍火器也源自西方,時間也和明朝相當,大約都是在十六世紀中葉傳入。種子島第十四代當主種子島時堯在偶然中巨款購得了西方鐵炮后,命令八板清定等人潛心研究,幾經周折,終于學會了鐵炮的制造工藝和技術。和明軍一樣,日軍火炮性能也不穩定④,雙方可謂八斤八兩。此后的戰局發展也印證了這點。
日軍武士經過戰國時代錘煉,戰術素養頗佳。因為火繩槍在日軍中得到廣泛配置,因此一些新的戰術打法也在日軍中出現。例如織田信長的“三段射擊法”,鈴木重秀的“鐵炮狙擊法”,另外還有伊達政宗的“騎鐵”戰術,都是圍繞火槍的特點來設計的。因此,在壬辰戰爭中,雙方都注重火器的使用,且以輕小型火器為主,大型火器較少,在武器裝備上可以說是差距不大。相比之下,明軍騎兵比例更高,輕型火器略少。在正月下旬的碧蹄館之戰中,雙方基本上平分秋色。這也比較真實地反映出兩軍陸戰實力。只是因為朝鮮水軍大敗日軍水軍,對日軍補給線造成極大破壞,因此戰局逐漸向有利于聯軍的方向發展。
明軍的這套班底和戰術打法,此后也基本上沿用至薩爾滸之戰。在薩爾滸之戰中,明軍和后金軍實力對比并不大。后金軍在統一女真各部的戰爭中,兵源素質良好。更重要的是,努爾哈赤在和明朝貿易的過程中,非常注重火器的采購,以東北盛產的貂皮等特產和明朝邊界商人交換硝石、硫磺,以制造火器之用。女真人原本就擅長游牧,騎兵作戰能力很強,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之后,對兵源進行優化,裁汰冗員,騎兵機動能力更強。再加上配以火器,戰斗力就頗為可觀。雖然和此后袁崇煥的紅衣大炮相比,后金軍的重型武力裝備還顯不足,但是在輕小型火器上,則不讓明軍。因此,后金軍騎兵、火器均較之明軍不落下風,為薩爾滸戰役的結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結語
嚴格來說,萬歷朝鮮戰爭是一次戰爭,前后時間跨度長達六年,有多次重大戰役。而薩爾滸之戰是一次戰役,時間不過五日。因此,將兩者相提并論,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兩者都對明朝的歷史走向,產生重大影響,而且都發生在萬歷朝末年,其結局卻天差地別。二十年中,雖然諸多變遷,很多士兵早已更替,但是二十年中究竟發生了什么,使得一支當年的勁旅,從勝利走向失敗,其中的過程,值得玩味、深思。
首先,最容易讓人想到的,就是軍隊的戰術素養。在萬歷朝鮮戰爭中,明軍先后兩次入朝作戰,都是從全國各地抽調參加過對蒙古、云南等地的戰斗的精銳,戰術素養比較高。同時,如前文所述,明軍的火器裝備也較成熟,初步建立了大型火炮和輕小型火器相配合的戰術體系。從軍隊素養和武器裝備看,明軍和日軍、后金軍沒有明顯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明軍和日軍的組成都比較復雜。明軍由宣大、寧夏、四川、江浙等地不同的部隊構成,而日軍則來自不同地方藩國,分別由家督或大名率領。兩軍在協同配合上都存在一些問題。因為明軍和日軍不同,沒有相應的家臣效忠體系,因此出現軍餉不濟的情況,極易發生兵變。相比之下,日軍由各家家督、大名統帥,將帥和士兵之間相安無虞。到了薩爾滸之戰時,明軍的戰術素養并沒有明顯的下降,但是各軍協調問題依舊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將帥與軍隊脫節、將帥親疏有別,對最終戰局產生重大影響。而八旗制度體系下的女真部隊,和日軍頗為類似,士兵對領袖效忠程度較高。
在兩次入朝作戰中,明軍都曾經取得過大捷,也都曾經錯失良機。朝鮮友軍的表現,對整個戰局具有深刻影響。尤其是李舜臣率領的水軍,對日軍打擊尤甚。日軍戰略補給全部仰賴海路,因此水軍的失敗對于日軍士氣打擊很大,并且造成日軍后勤不穩。雖然有學者認為,不應把李舜臣的作用夸大,例如鳴梁海戰中李舜臣之所以沒有全殲日軍,就是因為李舜臣已經力竭,如果繼續戀戰恐怕他原本就不厚實的那點家底都要打光。而且直到日軍最終從朝鮮撤退,都沒有完全喪失制海權,沒有一名陸軍的主要將領陣亡,成建制順利退回本土。但是朝鮮水軍的優異表現無疑對戰局走勢有重大作用。如果沒有水師的佳績,戰爭陷入曠日持久的拉鋸戰,那么對于戰線過長的明軍來說是不利的⑤。薩爾滸之戰,明軍的補給線不僅更長,而且暴露在后金軍攻擊范圍內,葉赫部和朝鮮的友軍都未及趕到戰場,戰役就已經結束了。
萬歷朝鮮戰爭和薩爾滸之戰另外一個顯著的差異,在于兩次戰爭的戰略目標并不相同。在萬歷朝鮮戰爭中,明軍沒有以殲滅日軍為戰略方針。這一是取決于雙方實力對比,兩次入朝作戰,中朝聯軍都沒有對日軍形成絕對優勢,包括被后世夸張渲染的海戰中,李舜臣也沒有對日水師形成絕對優勢,圍殲日軍就是一個神話。另一個因素就是明軍在和日軍接觸過后,充分認識到日軍戰斗力,故沒有制定不切實際的戰略目標,只是以趕走日軍為訴求。而在薩爾滸之戰中,明軍在對敵情況不了解的情況下,僅僅依據所謂數量優勢——事實上連數量優勢都不具備,明軍號稱47萬,其實不過10萬——就妄圖一口把努爾哈赤吃掉,嚴重脫離實際。
反觀對手。日軍在平壤之戰后失去了戰略主動權,此后雙方互有勝負,但是日軍都難以再爭得先手。日軍始終沒有拿出一套針對明軍的有效方案,陷入一種無戰略怪圈。每打一仗,勝負都在天數。例如蔚山之戰,明軍兩次攻擊后,日軍眼看就要崩潰,明軍主動停止攻擊,隨后日軍援軍趕到,戰局逆轉。但是日軍即便戰勝,也無力扭轉整個戰局,歸根結底,在于既沒有長期戰略部署。前方吃緊,則臨時征調補充。這種景象,到二十世紀淞滬戰役后再次重演。日軍戰略之迷茫,可見一斑。薩爾滸之戰中,努爾哈赤很快找到明軍命門,針對明軍的分兵而進,制定出“憑你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方針,戰略部署極為明晰。從統帥到士兵,都打明白仗。與其說明軍二十年后大失水準,不如說對手更加精明、更加有章法。
因此,在評價兩次戰爭時,不能輕易認為,明軍在兩次戰爭中表現天差地別。如果不是豐臣“及時”去世⑥,而是換做日后的德川幕府,則日軍的資源調動能力或更強大,那么戰爭究竟會如何發展,將會是一個未知數⑦。誠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中朝聯軍的勝利,確實并非完勝,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薩爾滸之戰,明軍四路大軍,三路被奸,也是不爭的事實。過高評價萬歷朝鮮戰爭的勝利,過低評價薩爾滸之戰中明軍的戰術素養,都不能完全揭橥歷史的真相。
注釋:
①朝鮮宣祖修正實錄 卷24年3月。
②陳尚勝.壬辰戰爭之際明朝與朝鮮對日外交的比較[J].韓國研究論叢,2008(1).
③朱子彥.明朝火器的發展、運用與軍事領域的變革[J].學術月刊,1995(5).
④陳波.日本火器發展過程中的文化視角[J].遼寧工業大學學報,2011(1).⑤陳尚勝.壬辰御倭戰爭初期糧草問題初探[J].社會科學輯刊,2012(4).
⑥明史卷322·日本傳。
⑦陸成侯.豐臣秀吉之死與壬辰倭亂的結局[J].新史學通訊,1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