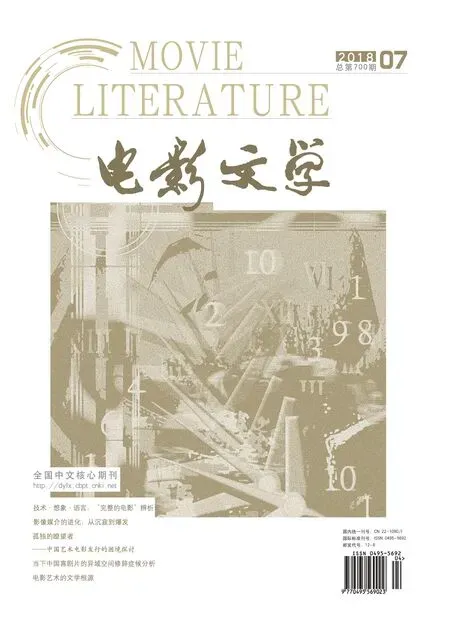視覺文化時代中美魔幻電影比較
謝 楠
(衡水學院,河北 衡水 053000)
魔幻電影是視覺文化時代最能體現時代文化風向以及大眾審美趣味的藝術形式之一。而從電影產業本身的發展來說,魔幻電影也同樣是當下最能征服全球觀眾的商業片類型之一。在視覺文化時代決定了魔幻電影的廣闊市場的同時,魔幻電影又豐富了視覺文化時代的文化特征。無論是中國抑或美國電影人都想方設法地在魔幻這一領域內開掘出新的題材,創作出新的作品。從整體上來說,中國魔幻電影距離美國同類作品還有一定的差距,這是毋庸置疑的,而要奮起直追,在這個圖像不斷征服受眾的時代分得市場的一杯羹,就有必要對中美魔幻電影的異同進行總結,從而對中國魔幻電影的大致特色與發展階段有一定的了解。
一、視覺文化時代的魔幻電影
毫無疑問,當前人類已經進入了視覺文化時代,該時期又被戲稱為“讀圖時代”,其原因就是在圖像面對文字時,其駕馭、凌越的姿態已經越來越明顯。在20世紀30年代,海德格爾提出了“世界圖像時代”的說法,在海德格爾的理論中,人類不僅要進入圖像時代,且勢必是全體性、概莫能外地進入這一時代,應該說,海德格爾對于視覺文化時代的影響力的把握是準確的;相對于前人主要著眼于“時代”的論述,到了60年代,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則對整個人類社會提出了“景觀社會”的總結,其《景觀社會》一書更是被譽為“當代《資本論》”;而從70年代至今,先賢的說法更是不斷在銀幕以及其他地方被驗證。
我們不難發現,促使人們意識到視覺文化的強悍力量的正是電影,而電影藝術在過去一個世紀也不斷地進行自我完善,擴展著自己的影響力,展示著自己在文字面前的權威。可以說,作為視覺藝術之一的電影已經憑借其在創造圖像上無可替代的優勢滲透進了當代人的日常生活,改變了人類接受信息的方式,如本雅明所言,人類已經更傾向于被電影的“子彈”擊中,而不是以“靜觀”的方式玩味富有“韻味”的文字,甚至對電影的欣賞成為人類的某種文化儀式。
魔幻電影興起于這樣的背景中。20世紀70年代為觀眾提供視覺文化盛宴的電影類型主要為科幻電影,一方面,從電影的內部來看,科幻電影盡管方興未艾,但是其本身在軟硬科幻兩方面的擴展已經逐漸放緩甚至停滯,尤其是在“冷戰”帶來的科技熱潮冷卻之后;而另一方面,就電影外部的原因來看,“冷戰”結束后人們尚未從現實世界的痛楚中恢復,“9·11”等恐怖襲擊,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現象,包括環境的污染、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巨大破壞力等都大大降低了人們對于科幻電影的追慕熱情。這種時刻,有著復古、復魅意味的魔幻電影則橫空出世,給觀眾提供了一個充滿假想的、令人陶醉的美好空間。
生逢其時的魔幻電影很快表現出了和視覺文化千絲萬縷的關系。例如,《獵神:冬日之戰》(The
Huntsman
:Winter
's
War
,2016)的劇情與迪士尼熱門動畫電影《冰雪奇緣》(Frozen
,2016)頗具雷同之處,電影追求的是以“暗黑童話+真人電影”的方式制造震撼觀眾的視覺效果,如頗具帝王氣勢的、氣勢磅礴的弗雷亞的冰雪王國,形式美超越了真實性本身。又如中國魔幻電影中的《鐘馗伏魔:雪妖魔靈》(2015)、《封神傳奇》(2016)所追求的藝術魅力顯然就已經從本雅明描述的韻味型走向了震驚型,電影中的人物關系較為簡單,而人物的造型則力求每一個都給予觀眾視覺沖擊力,甚至不惜通過夸張的手法讓其與人們刻板印象中的傳說人物形象,如雷震子、妲己等,產生距離。而這類魔幻電影盡管口碑參差不齊,但就票房吸引力來看卻是具有一定競爭力的。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能夠不斷給予觀眾視覺快感的魔幻電影正是當前消費社會以及視覺文化時代下的產物。
二、奇觀化的深刻轉向——中美魔幻電影之同
中美兩國的魔幻電影都有著明確的從敘事向奇觀的轉向,電影原來的話語中心逐漸讓位于圖像中心。讓影像給觀眾制造快感這一點在創作中具有主導和統治地位,甚至在極端的狀況下,敘事有可能成為奇觀的附庸。
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霍比特人》(The
Hobbits
)三部曲。從故事本身來說,《霍比特人》原著是較為單薄的,作者托爾金所創作的僅僅是一部情節簡單、基調歡快的兒童故事,相比起同樣是由托爾金創作的,具有史詩意義的《指環王》(The
Lord
of
the
Rings
)來說,《霍比特人》的情節建構完全稱不上曲折離奇,其體量是撐不起和后者一樣的三部曲的。然而在市場的誘惑下,電影將其擴展為三部曲,在這擴展的過程中,強大飽滿的視覺刺激就發揮了重要作用。電影圍繞著小說中并未出現的人物,精靈王子萊戈拉斯至少加了四場打戲:精靈王子帶領部下與蜘蛛的對抗,精靈王子追殺索林·橡木盾等矮人,精靈王子和女精靈陶瑞爾對敵方老巢的偵察,以及精靈王子最終和獸人的決戰。如此一來,不僅電影的體量大大增加,且視覺的霸權和誘惑通過繁復炫目的打斗無處不在:俊美而勇武的精靈王子身輕如燕地穿越于叢林溪流,在崩塌的斷橋上腳踏碎石飛身而起等場景都既逼真,又是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的,在殺戮讓觀眾興奮時,精靈王子的身體本身也對觀眾直接造成快感。正如桑塔耶納所指出的:“我們審美敏感的全部感情方面——沒有這方面便是知覺的和數理的敏感而不是審美的敏感了——就是來源于我們的性機能的輕度興奮。”而中國魔幻電影也不例外,在《畫皮1》(2008)中,電影中以極美和極丑兩個方面來塑造九霄美狐小唯的形象,她擁有畫皮掩蓋出來的美麗肉身,畫皮之下則是令人驚恐的黑色妖身。電影中小唯拽下畫皮露出真面目的一幕令人極為難忘。《畫皮2》(2012)中,靖公主和小唯的水中換心等場景也不例外。如果說《畫皮1》就已經是用視覺來擴展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故事,那么《畫皮2》則更是奇觀壓倒敘事的新創之作,電影中的歷史背景更加虛無縹緲,話語性因素的重要性也更低,天狼國、寒冰地獄等的出現更主要是為了使電影能更好地創造視覺奇觀。這一類奇觀的共同之處都在于,首先,它們不需要,或沒有來自現實生活的,可以與之比較的原型,這也給予了主創們肆意發揮的余地;其次,主創以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創造出來的奇觀,是指向觀眾的心理真實的。如觀眾本身對于一個靠吃人心生存的妖是什么樣的并沒有概念,但電影便以令人作嘔的圖像表現了出來,這能激起觀眾實實在在的生理反應,以及與之相關的人道情感,如觀眾在看到佩蓉被施法誣陷是妖之后兩眼流血的害怕、同情之情;最后,奇觀中暴力和性往往是并存的。恢宏、激烈的打斗場景是電影奇觀的一部分,而對身體的欣賞則是奇觀的另一重要內容(這種對身體慷慨展現以制造視覺沖擊的方式在當代的廣告中也屢見不鮮)。盡管身體本身并不被膚淺地作為賣點,但是也絕不是導演回避的對象。與之類似的還有如《畫壁》(2011)、《倩女幽魂》(2011)等魔幻電影。
由此可見,以巴赫金的理論來觀照魔幻電影,我們可以認為,中美兩國都力圖讓電影回歸到視覺藝術本體論的位置中去,讓電影為觀眾制造一場又一場的“狂歡”。
三、快感文化與理性文化的兼顧——中美魔幻電影之異
在肯定了中美魔幻電影擁有共同點后,有必要對二者的區別,主要是中國魔幻電影相對于美國同類作品的不足之處進行總結。從直觀上來說,限于投資以及經驗等原因,國產魔幻電影往往在技術上無法與美國魔幻電影相媲美。我們需要明確的一點是,盡管魔幻電影的興起是近年出現的現象,但是美國在這類電影上的嘗試要遠比中國早得多。早在1939年,美國就拍出了彩色故事片《綠野仙蹤》(The
Wizard
of
Oz
),這部電影也被視作不朽的經典。在21世紀,電影藝術無論是前期抑或后期制作,都離不開數字技術對電影在鏡頭、光影以及色彩等方面的全面介入,包括中國導演都無法拒絕數字技術的巨大力量。如一貫對電影有強烈掌控欲的張藝謀就曾表示,很多時候自己是被電腦導演支配。此時的美國魔幻電影更是在數字技術的幫助下不斷創造視覺奇跡,在產業的資金良性循環方面也已經形成了成熟的鏈條,如《指環王》和《霍比特人》系列讓新西蘭的維塔工作室名聲大噪,并且在電影上映后,電影還可以依靠遺留下的影視城、周邊產品等繼續盈利,而中國電影在數字技術的研發上則較為滯后。因此,單純就技術而言,起步較晚,并且資金往往受限的國產魔幻電影不及美國魔幻電影是不難理解的。這里要重點強調的是二者在文化內涵上的差異。從文化源頭的角度來說,美國魔幻電影大多取材于歐洲神話傳說,或在此基礎上創作的現當代魔幻作品,如根據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以及索福克勒斯、歐里庇得斯等人的作品改編而成的《特洛伊》(Troy
,2004)等。而中國魔幻電影同樣有源遠流長的文化滋養,如來自《白蛇傳》的《白蛇傳說》(2011),來自《西游記》的《西游·降魔篇》(2013)等,二者可說是沒有高下之分的。但是中國魔幻電影的癥結在于,要么是在對一個舊故事進行重新闡釋時,無法在視覺快感之外給予觀眾更多的理性文化思考,如當觀眾可以見仁見智地從《指環王》和《納尼亞傳奇》(2005)中分析故事的反戰、環保宗旨時,《白蛇傳說》和《西游·降魔篇》對于故事的演繹依然沒有超越愛情和降妖除魔、求取真經這一本意。要么是脫離民族傳統文化進行一個全新的世界觀制造時,敘事的合理性或流暢性被破壞,讓觀眾難以接受。如《無極》(2005)、《爵跡》(2016)等電影,這一類電影的視覺效果幾乎是無可挑剔的,但是從對世界觀的理解上來說,電影需要觀眾的高度參與,而華麗的視覺效果又極有可能分散觀眾的注意力,或是在敘事上的瑕疵,都有可能影響觀眾對故事內涵的思索。但是,中國電影人試圖擺脫機械地復制文化母題,以創新精神打造新的魔幻世界譜系,這是難能可貴的。并且可以肯定的是,隨著在不同IP上的嘗試,中國魔幻電影也必將尋找到能實現感官娛樂和文化內涵兼顧的表現之路,實現電影和觀眾(包括外國觀眾)之間更好的互動。電影提供了一種能夠幫助觀眾脫離現實煩擾紛爭的娛樂方式。在人類全面進入視覺文化時代的今天,魔幻電影則迎合了人類無意識的呼喚,即在科學和理性之外,提供給人類另一種唯美的,重新認識世界的途徑。這也是中美兩國都在大量創作魔幻電影的原因。就追求視覺的奇觀化這一角度來說,中美魔幻電影,乃至其他文化背景下的魔幻電影是趨同的,因為市場對于“眼球元素”的渴望是趨同的;但是,在具體的數字技術的運用以及文化內涵上,中國魔幻電影與美國魔幻電影差距又是較為明顯的。在一個全新的、和視覺文化時代互相成就的影像時代到來的今天,中國魔幻電影要想趕超美國魔幻電影,其任務依然是艱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