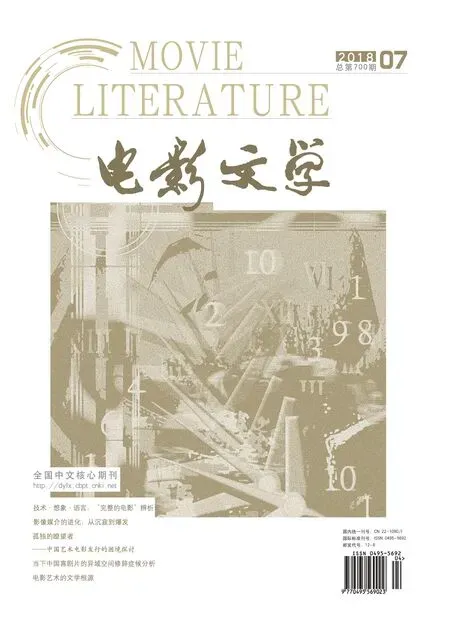“嚴肅”與“通俗”之間的《無聲言證》
張國俠
(綏化學院 外國語學院,黑龍江 綏化 152061)
安東尼·威勒自編自導的電影《無聲言證》被認為是俄羅斯驚悚電影中的上乘佳作。從亞類型片的角度來看,驚悚電影與恐怖電影存在一定的區別,相對于恐怖電影中能夠出現妖魔鬼怪等超乎現實的異域生物,以及斷肢血漿等直觀上刺激觀眾感官的元素而言,驚悚電影更強調在極具現實意味的敘事中,通過懸念和氛圍給觀眾制造恐慌、緊張感。而《無聲言證》則在角色的設定、情節的編排乃至氣氛的營造等方面,既具備驚悚電影應有的娛樂效果,又隱含了較為嚴肅的社會批判意識。
一、《無聲言證》與驚悚電影
《無聲言證》的情節設置可以說是驚悚片的范例。影片中,一個美國劇組在俄羅斯拍攝小成本驚悚片,女主人公比莉便是這個劇組的道具師,比莉天生無法說話。由于無意中將東西遺忘在了片場,比莉返回片場取東西,不料管理員卻鎖上了大門。被迫留在片場過夜的比莉在晚上無意中看到了一個色情恐怖片的拍攝現場,在激情鏡頭之后,女演員被殘忍地殺害了,一切都被拍攝了下來,而死者便是自己這部電影的女演員。目睹了一切的比莉被拍攝者看見,加上拍攝者無意中遺失了一張有罪證的磁盤,于是拍攝者對比莉展開了追殺。電影無意將“兇手是誰”作為吸引觀眾的懸念,而是讓觀眾站在比莉的視角疲于奔命,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既要躲避對方孔武有力的殺手的追殺,還要在自己是唯一目擊者,且不能說話的情況下說服執法者,揭穿兇手的謊言。可以說,電影劇情極為緊湊,在短短的90分鐘內,每一分鐘都令觀眾緊張無比。
值得一提的是,《無聲言證》本身是有著對于部分低俗驚悚、恐怖片的主觀超越追求的。電影以一段“戲中戲”開始,這是一段類似于《猛鬼街》系列的情節:在一個裝潢精美的房間中,一位美貌的年輕女性遭遇了持刀歹徒的襲擊,場面極其兇殘可怕。觀眾被直接帶入到了一種恐怖而又令人迷茫、疑惑的緊張氣氛之中,形成了一種心理期待,即整部電影將是關于警方與這個兇手之間斗智斗勇,并且繼續上演血腥場面的故事。然而與《驚魂記》(1960)等電影,兇殺情節干脆利落地結束不同,被“殺”的年輕女子并沒有倒地不起,而是在身中數刀的情況下痛苦地掙扎、翻滾,撲倒了堆滿東西的桌面,又起來抓倒了窗簾等,她不斷地倒地又起身,似乎不像是符合常理的垂死掙扎,讓觀眾摸不著頭腦。隨后鏡頭移開,才揭露了真相,原來這只是一個由倉庫改裝而成的電影片場,導演和其他工作人員,包括扮演蒙面歹徒的演員等,都在一臉戲謔地看著“死者”的表演,直到導演無奈地喊停。原來女主人公是一名名不見經傳的小演員,她為了盡可能地給自己爭取多一點露臉的機會而進行了這種“死也死不掉”的表演。首先,這一段不乏幽默感的敘事結束以后,觀眾的情緒完成了一個由張到馳的周期,同時還能夠收獲會心一笑。其次,從情節安排的角度來說,這一段其實并非單純搞笑的閑筆。正是因為女演員這種不敬業的表演,整個劇組才會被耽誤了時間,到了晚飯時間導演決定收工,第二天再來補拍鏡頭,以至于相關的大量道具等都遺留在了這個大倉庫中。這為后來比莉進入猶如迷宮的倉庫,利用里面的各種陳設逃避追殺埋下了伏筆。第三,女演員的拙劣表演代表了一種低俗驚悚電影層出不窮的套路:兇手的殘忍殺戮被無限制地放大,而女性作為被害者只能尖叫和跌倒,不斷暴露自己的弱點,或是與男一號產生情愫,而除此之外女性對于劇情的推動幾乎毫無意義,在用弗洛伊德的“死本能”吸引觀眾之外,這類電影基本上不能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這正是《無聲言證》所規避的。
二、“通俗”效果
正如尼采所說的,生活的單調導致人們需要戲劇。驚悚電影首先便是要給予觀眾現實生活中難以具備的,能夠帶來恐懼心理的經歷和體驗,因此電影必須給觀眾制造大量人類作為有機體不得不逃避、擺脫的對象,才能達到通俗的、能獲取大多數觀眾歡迎的效果。
《無聲言證》的通俗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分別是具有跌宕性的敘事以及在畫面上給觀眾造成的官能刺激。
(一)跌宕性敘事
如前所述,觀眾在電影中早已獲知了兇手和死者是誰(劇組的工作人員),因此電影的懸念主要在于比莉是否會為他們所害。女演員的被殺景象是先聲奪人的。隨后兇手和比莉都因為大門被鎖而困在倉庫之中,比莉的處境是極為不妙的,倉庫里的各個房間、道具,乃至垃圾通道、電梯等,都成為比莉求生的依靠。比莉也在其中表現出了冷靜和智慧,如即使在逃命時也注意扶住跌倒的東西避免發出聲音,打破墻上放置備用鑰匙處的玻璃拿到備用鑰匙等。而在比莉離開倉庫回到家以后,觀眾仍然可以看到危險在向她步步逼近。在家遇到兇手鉆門進來的比莉此時處于更加弱勢的境地中,她周旋的空間更加狹小,但是比莉此時還是想盡辦法用身邊的一切來解困,如在兇手全力撞門時猛然開門,又如當兇手落入裝滿水的浴缸里時往浴缸里放入插著電的電吹風,直接電死對方等。這些以弱勝強的橋段都給予了觀眾極大的生動性與趣味性。
(二)官能刺激
在視覺上,電影也注重給予觀眾刺激。如運動鏡頭與動作場面,電影中既有人和人在狹小、封閉空間內的肉搏,又有大街上汽車的圍追堵截,這些畫面都極具藝術感染力,讓觀眾始終提心吊膽。又如恰到好處的情色和暴力畫面。死亡是驚悚電影幾乎都不可回避的內容,電影中要表現女演員的被殺,但是并沒有直接呈現給觀眾血淋淋的場景(與之前“假死”時出現比莉負責的一箱帶甜味的假血形成對比,此時再出現所謂的“真血”,觀眾也有可能無法獲得驚嚇感),而是表現了在一個垃圾通道下面,堆著幾個黑色的垃圾袋,躲在這里的比莉依稀看到了女演員的手,而這很有可能便是自己的下場。電影用這樣的方式提醒觀眾女演員不僅已經被殺,而且已經被粗暴地分尸了。電影對兇殺的表現點到即止,而觀眾可以用自己的經驗對此進行補充,從而神經緊繃。
除此之外,威勒還有意識地在電影中加入了具有幽默感的內容,如上述的拍電影情節,又如姐夫安迪在家里做晚飯時跟胡椒粉和鍋手忙腳亂地“搏斗”,當樓上比莉的家里在發生致命打斗時,電影偏有閑筆去表現一下樓下的鄰居因為嘈雜而睡不著,于是拿著馬桶的皮搋子想捅一下天花板以示警告,最后忍不住登門提醒,大受驚嚇以后穿了超人的衣服逃之夭夭等,這種情節的加入緩解了電影暴力、兇殺內容的沉重感,讓觀眾獲得了更充分、更豐富的娛樂享受。
三、“嚴肅”指向
在滿足了驚悚片應有的藝術形式要求后,《無聲言證》還具有嚴肅的批判指向。觀眾可以感覺到,恐怖是必要的,但并不是目的本身,或并不是唯一的目的,電影還試圖通過恐怖的故事、令人毛骨悚然的情節,敦促人們對一些問題進行理性思考。
首先,電影從性變態這個角度,揭示了俄羅斯社會的黑暗一角。電影中的兇手在攝像頭前剝奪女性的生命,并錄影制成光碟給他人反復播放觀看,以此牟利,可見社會中確實有這樣的性變態需求者。但是性變態本身并不是電影批判的對象,電影針對的是盤根錯節、無惡不作的俄羅斯黑幫。出現在觀眾眼前的兩名惡人只是活躍在前臺的人,而他們的保護傘,不斷推動犯罪發生的人其實是俄羅斯黑幫。而誘騙女性拍攝殺人電影,顯然僅僅是黑幫營利的手段之一。自1991年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各犯罪集團,如“塔里耶爾·奧尼亞尼幫派”等就不斷擴張勢力,成為當地社會動蕩因素之一。如阿里克塞·巴拉巴諾夫的《兄弟》(1997)等俄羅斯電影都反映了類似問題。
其次,無能的、不盡忠職守的俄羅斯警方同樣是電影批判的對象。警方理應是本地公民和外國合法入境者的保護者,然而在電影中,警方卻是失職的。在原本傳喚死者就可以查清真相的情況下,警方卻毫無行動,聽信兇手,放虎歸山,顯然是與黑幫有所勾結,無怪乎整個社會治安極差,兇手當夜就跟蹤女性,公然破門殺人。也正因如此,比莉才會對俄羅斯的公職人員都失去了信心,一度和真心想要幫助她的拉森先生進行搏斗。
最后,電影批評了人們對待暴行時主動的、幫兇式的沉默。電影的“無聲言證”中的“無聲”其實總共包含了三層意思。第一層是比莉本人無法用嘴巴和別人進行交流,包括求救、解釋等。雖然她已經用種種方式克服自己的殘障,但是在危機時刻這一生理上的缺陷還是極為致命的;第二層則是比莉身在異國他鄉,語言不通,這一點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普通人即使沒有身障,但也同樣有可能因為主客觀因素的限制而與他人缺乏正確有效的溝通,然后導致各種誤會的產生,最終無法順利地解決事件,甚至引來危險;第三層則是最為可怕的,即人們并不是口不能言,也不是語言不通,而是由于恐懼、僥幸或包庇等心理,面對清楚的犯罪事實而緘口不語,讓真兇逃脫法律的制裁。這便是涉及每一個人的社會法制建設問題,也是電影大力批判的。如果我們回溯電影開始時那段戲中戲就不難發現,電影特意用移鏡頭表現了劇組人員對于“掙扎”景象的無聲圍觀,這其實就代表了人們面對暴行無動于衷的態度。而《無聲言證》則給予了觀眾一個積極的結局,面臨著三重無聲困境的比莉終于以自己的方式發出了聲音,伸張了正義,維護了法律的尊嚴,這是值得觀眾為之慶幸和效仿的。一言以蔽之,在讓人喘不過氣來的追殺敘事表象下,《無聲言證》隱藏著對社會問題頗為尖銳、冷峻的思索,這提高了電影的格調。
可以說,就驚悚片這一類型片而言,電影人們到目前為止已經進入了一個創新的瓶頸期。觀眾越來越不容易被激發出恐懼與緊張感。就藝術技巧,如劇情、畫面、布景、音樂等之間的配合而言,《無聲言證》可以說取得了較為客觀的成就,讓觀眾為之眼前一亮,但這也是不易模仿的。如《八面埋伏》(2004)中同樣設計了身體不便的殘疾者是受害者,但是他無法成為唯一的受害者來引領劇情。而電影在思想性上蘊含了嚴肅態度卻是完全可以,也應該被后來者繼承的。這方面較為典型的便是《伊甸湖》(2008),電影之所以能作為一部驚悚片而屢獲大獎,很大程度上就在于電影揭露了現實生活中英國社會里嚴峻的青少年教育問題,包括酗酒、犯罪,以及英國的地域歧視問題、城市貧民窟問題等,都能讓人感覺恐懼離自己并不遙遠。如果說《無聲言證》給予了觀眾一個樂觀的結局,那么《伊甸湖》則因上述問題依然觸目驚心地存在而以悲劇告終。
盡管就當下的電影市場來看,驚悚片的市場份額不斷被科幻、奇幻等具有“狂歡化”影像的視覺大片擠壓。但由于恐懼是人類永恒的、普遍的心理,加上“人們集體害怕自毀于厭倦和麻木,于是喚出一切惡魔,讓他們像獵人驅趕野獸一樣來驅趕自己,人們渴望痛苦憤怒、仇恨、激昂、出其不意的驚嚇和令人窒息的緊張,把藝術家當作這場精神狩獵的巫師召喚到自己面前”為自己制造恐懼,驚悚片依然會繼續存在著,而成功游走于“嚴肅”和“通俗”之間的《無聲言證》便是人們在進行創作時的一個極好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