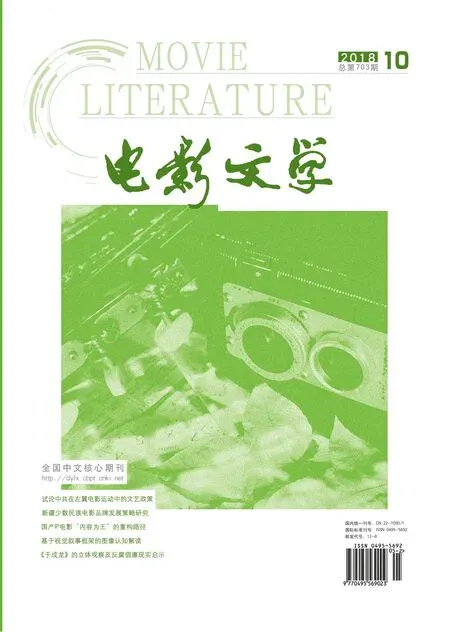《穿條紋睡衣的男孩》對人性的審視
劉 麗
(重慶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通識教育學院,重慶 401120)
馬克·赫爾曼的電影《穿條紋睡衣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
,2008)改編自愛爾蘭作家約翰·伯恩的同名小說。電影從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布魯諾的視角,為觀眾展現了戰爭的殘酷與荒謬。但戰爭本身并不是電影表現的對象,電影繼承了小說中悲天憫人的情懷,以布魯諾的遭遇,對納粹乃至人性進行了審視與批判。一、反戰立場與人文情懷
第二次世界大戰帶給人類以刻骨銘心的傷痛記憶,盡管親歷者逐漸凋零,戰爭所帶來的巨大傷害依然是活著的人們不能釋懷的。尤其是在二戰中,納粹何以會出現在以理性著稱的德國,并做出種族滅絕這一行徑,這是讓人不得不追根問底的。這一話題吸引著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對歷史進行解讀,如斯皮爾伯格的,小姑娘嘴里大喊“再見,猶太佬”的《辛德勒的名單》(1993),貝尼尼的《美麗人生》(1997),羅曼·波蘭斯基表現猶太人無處可逃的《鋼琴師》(2002)等電影,都充斥著對這段滄桑悲苦歷史的反思情懷。
約翰·伯恩和馬克·赫爾曼都在小說和電影中表露了鮮明的反戰立場與人文情懷。由于納粹軍官父親的升職外調,布魯諾一家搬離柏林,住到了沒有玩伴的陌生農村。而新家附近則有一個奇怪的農場,里面有許多穿著條紋睡衣的人在勞作。熱衷于探險的布魯諾不顧父母的警告多次走近農場邊的鐵絲網,并與里面的小男孩希姆爾結下了友誼。在父母發生爭吵,布魯諾即將和家人一起搬到海德堡之前,他挖開鐵絲網下面的土,鉆進農場中想在走之前幫助好朋友希姆爾尋找父親,不料卻和希姆爾以及其他大批猶太人一起被送進了毒氣室。
掌管這個農場(集中營)的軍官父親無疑是作惡者,他所代表的是執行滅猶政策的納粹,他不斷用“軍人的責任”“國家的復興”來為自己的惡行辯護,最后痛失愛子,他的惡行直接報應在了他自己的身上。8歲的布魯諾代表了德國的未來,他的死意味著德國為這場戰爭必然付出的代價,他換上“條紋睡衣”(囚服)鉆進集中營的出發點是善良的,但是他卻不得不成為成人作惡的犧牲品。盡管無論是父親抑或是布魯諾、希姆爾,在整個歷史進程中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他們全部承受了二戰的戕害,他們的命運是值得人們痛思和反省的。
布魯諾的悲劇并不僅僅在于最后的身亡,電影用多個細節表現了戰爭對于人性,尤其是原本純真善良的兒童的人性的傷害。如12歲的姐姐格蕾特爾原本喜愛洋娃娃,即使在搬家時也不忘懷抱洋娃娃。她的屋子原本堆滿了各式各樣的娃娃,但是有一天這些娃娃卻全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格蕾特爾在墻壁上貼滿了納粹的海報。而當布魯諾去地下室找自己的足球時,才發現姐姐已經把那些娃娃都收了起來。對此,格蕾特爾的解釋是,只有不成熟的人才愛玩娃娃,現在是國家要復興的關鍵時刻,她應該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國家大事”上。在家教老師的課上,格蕾特爾也比布魯諾更認同老師對猶太人的仇恨言論。她用這樣的方式來證明自己接近、靠攏著成人世界,并急于和并不仇恨猶太人的、幼稚的弟弟區分開來。而布魯諾因為年幼而對于猶太人是否邪惡沒有概念,家教老師盡管強迫布魯諾讀希特勒的書和所謂的德國歷史,告訴布魯諾“猶太之流詬吾族,誘吾族之敵”“凡其所到之處,災害不斷”“吾國必因其而亡,不遠矣”。但是布魯諾是不接受的。他之所以沒有像姐姐一樣篤信老師的話并不是因為他已經學會了獨立思考,而更主要的在于對老師不讓他再看探險小說的不滿。
對于父親的軍人身份,布魯諾充滿了自豪,他也堅信父親是一個“好戰士”,每天為了國家的富強而工作。在電影的一開始,布魯諾就和自己的好朋友卡爾、萊昂等人一起在街上奔跑玩耍,而就在他們跑過的街道上,就有著被驅趕上卡車的猶太人。對于年幼的布魯諾而言,他還無從分辨戰爭的正義與否,只是懵懂地認為成為軍人,進行戰斗是光榮而偉大的。“很多影評都提到,這一歡樂的場面與隨之而來的小伙伴間的離別構成了反差,卻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孩子們的奔跑本身也極具象征意義:他們玩的是張開雙臂模仿戰斗機俯沖穿行的游戲,嘴里同時在模擬戰斗機發出的轟鳴聲——導演馬克·赫曼正是用這一帶有隱喻性的橋段和幾面巨大的納粹旗幟點出了故事發生在‘二戰’期間,并不露痕跡地控訴了戰爭所施加給兒童的無形的戕害。”
二、人性的美丑善惡
在《穿條紋睡衣的男孩》中,電影的大部分篇幅都集中在日常敘事中,出場的人物也并不被直白地表現出畸變、陰狠的一面,而前線的戰況更只是寥寥幾句成人之間的對話便加以概括,如住在柏林的奶奶在空襲中被炸死等,但這并不意味著電影對于人性的沉痛解剖是不深刻的。
電影中,人性的美丑善惡被以一種對比鮮明的方式呈現出來。首先是場景的對比,猶太人在集中營中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宿舍里人擠人,平時的勞作極為辛苦,并且除了希姆爾之外,幾乎每個人都生活在隨時有可能喪命的絕望中。而與之形成對比的則有兩個場景:一是布魯諾生活的舒適豪華的別墅,二是父親在電影中搭建的虛假的,充滿了歡聲笑語的場景,后者充分反映了納粹的虛偽。其次則是人物的對比,展現了最激烈的惡的便是科特勒中尉。他的父親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叛逃去了瑞士,為了表示自己與父親劃清界限,科特勒平時就表現得對猶太人格外兇狠苛刻,在布魯諾父親的譏諷之下,他更是對在布魯諾家里幫傭的帕維爾拳腳相加,將對方活活打死。而布魯諾父親則默許了這一切,隨后還是以沒有向上級匯報家庭狀況為借口將科特勒中尉送上戰場赴死(真實原因是中尉無意對布魯諾母親泄露了黑煙的秘密,導致布魯諾母親崩潰)。可以說對“嚴格來說,其實不算是人”的猶太人的蹂躪和殺害在他們看來已經是正義正常的事。
在電影中,嘲笑父親一身制服的奶奶和因為得知那些黑煙來源于猶太人被焚燒的尸體而痛哭失聲,想從奶奶的棺材上拿走希特勒語錄的母親是持反戰態度的,盡管由于父親的存在,她們無法更加真切地表白自己的立場。電影對人性美與善的展現,更多的是集中在布魯諾身上的。布魯諾渴望友情,一次次地去找希姆爾,給他帶吃的,還想扔籃球給對方玩,一心邀請對方到自己柏林的家來玩。當希姆爾說自己之所以穿著“條紋睡衣”是因為那些軍人把大家的衣服都收走了時,布魯諾馬上說自己的父親是那種“不會拿人家衣服”的軍人,在以為父親給予了猶太人很好的生活后,布魯諾馬上沖去緊緊地擁抱父親,可見布魯諾有著基本的是非觀。當希姆爾來布魯諾家擦杯子時,布魯諾怕小伙伴肚子餓就給了他點心,而當希姆爾被科特勒中尉責問時,布魯諾因為害怕而不承認自己給過希姆爾點心,導致希姆爾被毆打,對此布魯諾感到無比愧疚,決定要為對方找到爸爸以彌補自己的過失。最后在進入集中營發現電影中一切都是假的時,布魯諾產生了回家的念頭,但是當希姆爾說“那我爸爸怎么辦”的時候,布魯諾還是鼓起勇氣繼續陪伴著希姆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可以說,主創們在抨擊納粹之惡時,又在布魯諾這個角色的身上,寄托著一種令人向往的精神境界,只有布魯諾的善得到放大和發揚,人才能抵抗人性惡的侵蝕。
不得不提到的是,在《穿條紋睡衣的男孩》中,出場不多的猶太人形象同樣是復雜的。赫爾曼并不僅僅將猶太人作為一個單純的、沉默的受害者平面形象來呈現。在猶太人被驅趕著走向死亡時,手持木棒維持隊伍秩序,催促人們不斷向前走去,并說“那只是洗澡”的,也同樣是猶太人,只不過因為種種原因,他們被納粹賦予了協助管理的權力,于是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同胞被害的幫兇。又如在毒氣室之外,猶太人被命令脫下衣服時,一位瘦骨嶙峋的老者從布魯諾的一頭黑發中認出了他,這名老者正是在帕維爾死后,取代帕維爾到布魯諾家削土豆皮的人,但是有可能是出于復仇的心態,他選擇了沉默,而與仇人之子共赴死地。電影中的人并非僅被分為應該被崇奉,或應該被唾棄兩種,揭露人性的復雜正是《穿條紋睡衣的男孩》的高明之處。
三、人性弱點與悲憫意識
如前所述,《穿條紋睡衣的男孩》敘事的切入點是日常瑣事,主人公布魯諾在搬到新家后的活動范圍以及能接觸到的人都是極為有限的。電影在各種小事和細節上進行了擴展(如布魯諾在念書時念錯“命運”一詞被家教老師糾正,而在生活中,他也確實沒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最終營造出一個具有一定容量的、整體性的,能以小見大的情景結構,并在這些小事與細節上注入了主創的悲憫意識。如父母在一開始勸說布魯諾搬家時,用的理由就是把這次搬家當成一次探險,因為他們知道布魯諾喜歡探險,而最后布魯諾敢混進集中營,有一部分原因也正是因為他同樣將這個行為視為一次探險。而另一方面,這也與電影專門加入的一段情節有關,父親拍攝了一段粉飾集中營猶太人生活狀況的影片,在放映給其他納粹軍官時,布魯諾也偷看了,這使得布魯諾在心里為自己的父親是個好人而舒了一口氣,也使得布魯諾天真地相信“農場”里面的生活是安全平靜的,每個猶太人都是自足快樂的。可以說,在兒子的悲劇上,父親有著不可推卸,但是又幾乎無法避免的責任。又如布魯諾為希姆爾帶了超大三明治,結果三明治卻在爬窗時掉在了地上,對此希姆爾并不計較。而如果布魯諾帶來了三明治,并等待希姆爾吃完,那么他還是有可能躲過這次毒氣屠殺的。觀眾能感受到布魯諾之死的偶然性,以及偶然背后的必然性。
值得一提的是,電影并沒有僅僅將角色視為善惡品性的容器,電影在審視著人性善惡的同時,也以一種悲憫之心洞察著人性的弱點。在電影中,成年人由于道德感或對國家機器的畏懼而都對集中營的真相采取了隱瞞態度,尤其是母親對布魯諾的隱瞞,包括背著孩子和丈夫爭吵等,正是出于保護、關愛兒子的立場,不料這卻使得兒子邁向危險。而在未成年人中,姐姐一方面對于戰爭只有一些空洞的如“猶太人是害我們輸了戰爭的敵人”的觀念;另一方面正為自己對中尉的初戀情懷苦惱。希姆爾出于善意或自尊的顧慮也沒有跟布魯諾說更多集中營中的生活細節,加上目睹了布魯諾偷拿食物的女仆瑪利亞等人自作聰明地給布魯諾一次又一次的包庇,這也就使得布魯諾越來越接近死亡。而布魯諾本人在天真無知之外,好奇心、魯莽和對家長的叛逆心理也同樣是他的弱點。當其他人只是因為隔閡或恐懼而選擇沉默和隱瞞時,布魯諾卻是一次又一次地撒謊。所有人為了安穩無事而進行的努力最終卻導致不可逆轉的悲劇。但與其說這是某個人的具體錯誤,不如說這是荒謬的戰爭和種族清洗這整個讓人性泯滅、讓社會失序的罪魁禍首造成的。
對人性進行審視,從而否定納粹,是《穿條紋睡衣的男孩》的最大價值所在。納粹軍官之子布魯諾在搬到集中營附近后與“穿條紋睡衣的男孩”開始交往,直到自己也成為“穿條紋睡衣的男孩”這一段經歷,成為電影巧妙的藝術時空,觀眾在布魯諾和猶太人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敘事中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盡管電影的兒童視角,使得人物形象和故事并不復雜,但電影依然通過各種細節深入到人性的隱秘層面,讓觀眾在電影平和而又富于張力的敘事中窺見了戰爭中人性的美丑善惡,完成了一次對人類精神價值的追尋與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