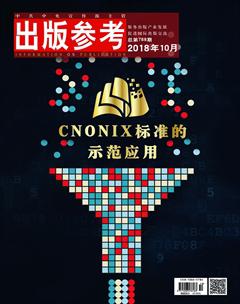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影像闡釋的集體記憶
韓岳
近年來,隨著作為紀實影像的紀錄片進入公眾時代,紀錄片研究也儼然成為了一門顯學。學者們在不斷完善紀錄片本體研究的同時,更多地開始采用跨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不斷拓展紀錄片研究的理論視野和研究版圖。其中有兩個領域收獲頗豐,一是與經濟學、管理學相結合,通過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探索紀錄片產業化的發展路徑。二是與文化學相結合,通過田野調查、深度訪談、文本細讀等方法,對紀錄片的文化記錄功能、文化形象塑造、跨文化傳播等展開研究。與政府對傳統文化的重視相呼應,作為紀錄片重要分支的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創作與研究在中國迎來繁榮發展的機遇期,影視工作者、科研院所與民間力量都呈現出旺盛的參與熱情,為學界提供了豐富的研究樣本。“中國影視人類學學術年會”、“視覺人類學與當代中國文化”論壇、“中國節日影像志”、“中國史詩百部工程”等學術活動和課題項目,為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研究搭建了交流平臺。可以說,文化人類學紀錄片以文化人類學為經,以影視學作緯,正日益成為紀錄片研究的重要坐標。文化人類學紀錄片是用影像來記錄和深描文化的影視片種,而關于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研究則喚醒和構建起人們對祖先及自己所創造的文化的集體記憶。
一、關注文化熱點,瞄準紀錄片發展
在學界和業界的關注與重視下,國內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學理研究已經小有規模,但對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發展脈絡做出系統梳理的佳作并不多見。而對于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本體而言,只有總結歷史、立足當下,才能夠更好地面向未來。從這個角度講,由曲阜師范大學副教授趙鑫博士撰寫、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專著《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史論》,其面世恰逢其時。全書以不同時期在國內外獲獎并具有一定影響力的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為樣本,圍繞“紀錄理念”這一核心因素,結合政治環境、社會思潮、技術應用等層面展開分析,形成對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發展的一次歷時性掃描。
概括而言,《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史論》全書可以分為“概念界定”“發展圖譜”“問題與對策”三大部分。首先,對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概念、功能等基本問題進行分析,框定了研究對象的基本理論范疇;其次,梳理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在各個歷史階段的創作特征,形成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發展圖譜,并從中探析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創作規律;再次,以創作規律為依托,審視當下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創作的現存問題,并提出相應對策。三大部分層層推進,既有學理層面的深刻思索,也有實操層面的總結與反思,對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立足本體,為“文化人類學紀錄片”正名
文化人類學紀錄片是文化人類學與紀錄片相結合的產物,同時包含了影視人類學與影視藝術學的雙重范疇。其身份的混合性決定了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研究的復雜性。面對這一特殊的研究對象,其基本概念的界定是開辟研究道路的首要之務。概覽現有研究文獻,人類學紀錄片、民族志電影、人類學片、影視人類學片等術語被學術界同時使用,而其指涉的對象又基本相同。可見,研究術語的規范與統一也是當務之急。因此,《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史論》的第一部分正是從概念辨析與界定出發,為“文化人類學紀錄片”正名。作者借鑒吳秋林教授在《影視文化人類學》中提出的用“影視文化人類學”代替“影視人類學”這一翻譯的學術觀點,認為用“文化人類學紀錄片”代替學界常用的“人類學紀錄片”,能夠避免術語使用上的歧義,并且更加凸顯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內涵和本質。在此基礎上,作者將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定義為:創作者運用真實記錄的手段,對田野調查中的研究對象(文化持有者及其展演的文化事項)進行長期和盡可能全方位的記錄,對研究對象進行深度掃描并在文化人類學層面上給予文化闡釋的紀錄片。由此可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既是以動態影像形式存在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成果,同時也是經過拍攝、錄音、剪輯等影視手段,對現實進行了創造性處理的完整的紀錄片作品。這一概念的界定既確保了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在人類學領域的學術價值,也確保了其紀錄片本體的審美功能;既規避了那些反映民族題材卻文化信息不足的偽文化人類學紀錄片,也將那些僅由資料性素材簡單堆砌而成的粗糙的影像文本排除在外。
三、以“人”為切口,全景掃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影像闡釋的歷史
作為一部“史論”,對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發展歷程的評論與總結,是全書的主體部分。然而,面對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60多年積累下的上千部作品,如何避免掛一漏萬,并且找到一條貫穿的線索,將紛繁蕪雜的歷史事項梳理串聯,形成一條邏輯清晰的發展脈絡,這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一個關鍵問題。《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史論》以“人”破題,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以人為本”是文化人類學的要義所在,同樣,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創作與研究,也要牢牢抓住“人”這一核心要素。其中,創作主體是文化的感知者、觀察者,其觀念、視角、知識背景和創作理念對文化客體的意義賦予和文化現象的解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說,創作主體是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演進的發生動力。
《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史論》的第二部分,正是通過創作主體這一角度,把脈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發展歷程,創新性地將其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學者與電影工作者通力合作的起步期;科研院所推動的恢復期;影視工作者創作活躍的發展期以及影視工作者、科研院所、民間力量多元助推的繁榮期。從創作主體入手,既可以牢牢把握“紀錄理念”這一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創作的核心要素,并將各個時期的主要作品及其創作得失納入研究視野;也便于將社會、時代、政治、文化思潮、技術應用等因素做綜合考量,對某一時期創作風格樣態的形成肌理做深入分析。
四、帶有問題意識,直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影像闡釋的現存問題
以史為鑒是為了更好地前進。在對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進行理論審視的基礎上,作者結合近年來對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相關活動的實地調研,剖析了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創作的現存問題,指出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雖然在數量上快速增長,但是題材選擇有所偏廢且整體質量普遍不高。具體表現在,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題材扎堆,而對都市文化和漢族題材關注不足。文化人類學學者創作的作品在可視性上處于劣勢,而影視工作者的創作在文化人類學信息的完整性、文化人類學觀點的表達、文化人類學方法和視角的使用上均有欠缺。總體而言,科學研究的學術性與影視創作的藝術性之間存在割裂現象。針對這些問題,書中給出了相應的發展對策。創作中的問題歸根結底也是“人”的問題,雖然文化人類學學者與影視工作者的理念與訴求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學術研究與大眾傳播之間并不一定要相互對立,不可兼得。作者對某些學者僅將影視作為田野調查的手段和工具的觀點提出質疑,強調了規范且熟練使用視聽語言的必要性,并指出“文化人類學與紀錄片是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兩個本體,前者提供內容與方法,后者是手段和載體,二者缺一不可,彼此依賴,彼此融合”。
五、彌補創作者的聲音,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影像闡釋的集體無意識
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一路走來,離不開一代代文化人類學紀錄片人在創作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對文化、真實與理性的默默堅守。而他們的思想與聲音往往隱藏在作品背后,不易被大眾捕捉和關注。我們欣慰地看到,《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史論》在全書的最后,收錄了作者對楊光海、龐濤和王海兵等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創作者的訪談實錄,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個遺憾。楊光海是中國第一位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導演,同時也長期從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研究工作,是《影視人類學概論》的撰稿人之一。因此,對楊光海的采訪既從實踐的層面還原了中國早期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創作圖景,也從學理層面對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問題以及與國際上的差距做出理性的思考。龐濤也同時具有創作者與研究者的雙重身份,作為中國影視人類學學會的常務副會長,對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現狀較為熟悉,其采訪對把握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最新發展態勢具有重要的意義。王海兵是國內較早從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創作的導演之一,其作品在國內外屢獲大獎,其采訪在影視藝術范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通過幾位重量級的創作者對當時創作過程的回顧與思考,呈現出了文化人類學紀錄片作品形成背后的豐富信息,既為全書的論述提供了有力的佐證材料,同時也為建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影像闡釋的集體記憶提供了難得的一手資料。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健康發展需要文化人類學學者和影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長補短,也需要一線創作者與學術研究者們優勢互補,通力合作。希望有更多學術性和傳播力俱佳的文化人類學紀錄片面世,也期待文化人類學紀錄片的學術研究不斷結出累累碩果。
參考文獻:
1.趙鑫.中國文化人類學紀錄片史論[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
(作者單位系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