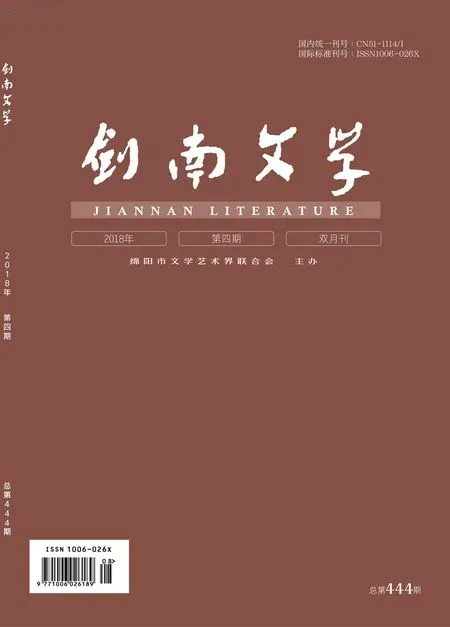寵兒
□ 卓中良
1
實驗進展得非常緩慢,幾乎沒有任何成就,喬斯常常感到很疲倦,哪怕是稍稍一抬手,也能聽見骨骼發出的嘎嘎聲。假如實驗室裝有心靈探測器之類的東西,那些西裝革履的投資者一定會無法忍受看著自己的錢打水漂。
但喬斯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表情,把很多的想法憋在心里。隔著兩條大街的不遠處有一幢喬斯的公寓,前后的花園都是喬斯新手栽的蘇丹蝴蝶蘭,它們的花瓣在盛開時繽紛鮮艷,令人眼花繚亂。喬斯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它們就像瑪雅人的墓碑和棺槨上繪制的花紋與圖案。
不久前,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將秋子擊倒,吃什么吐什么,四十度的高燒把秋子的大腦攪得一塌糊涂。城市管理局派來了穿白大褂的醫生,他們圍著秋子,拿著他們的專用器械,量體溫,抽取血液,透視檢查。最后,一群白大褂醫生圍在一起還開了一個圓桌會議,他們列出一張用藥的單子,每一名在場的醫生都鄭重其事地在單子上簽了字,他們認真的表情讓人發笑。
一名醫生留下來繼續觀察秋子的病情,另一名醫生拿著簽了字的單子去城市藥物局領取藥品,剩下的白大褂回到實驗中心,向那群西裝革履的家伙匯報秋子的情況。
他們嚴格按照時間給秋子用藥,有人二十四小時陪在秋子身邊監控病情,然而沒有用,三個療程的藥用完后,秋子的高燒依然沒有退。半個月后,喬斯看見他們的臉上集體寫著失望。沒有某種生物體能經得起這樣的折騰,開始有人建議對秋子放棄治療。喬斯聽說有病理學家從另一座城市趕來,準備在秋子死后解剖秋子的尸體,更有甚者,開始在為秋子準備墓地。
突然之間,一切都改變了。秋子從睡夢中醒來,感覺像是從數萬年之久的長眠中醒來,她茫然地坐在床上,風穿過她的身體,把窗戶搖得咯噠直響。高燒就這樣像潮水般退去。
這樣的反轉把那群白大褂震驚得目瞪口呆,一個滿頭銀發的老者不住地搖頭。他是專家級別的研究員,可這樣的結果他一時半會也無法給出解釋。
2
秋子開始吃飯、工作……吃飯、工作,安靜地看書、遛狗,偶爾還去看一場演唱會,秋子還是秋子,什么也沒有改變。
只有喬斯知道,秋子還是秋子,秋子也不是秋子了。
3
人工智能技術突飛猛進地發展,帶動了很多方面的應用。為了防止錯誤或重復建設,大型城市模擬演算技術應運而生,在一座“虛擬城市”里,計算機引進數十萬到百萬不等的人工智能AI,他們有一定程度的自我主體,但更多的記憶和行為模式是被植入的。他們一批批引入 “虛擬城市”,用他們生活的舒適度和滿意度,測試城市的市政、公共資源配套,這就是所謂的模擬城市規劃,只有確定最優的方案,才能被實際執行。
4
喬斯和秋子坐在沙灘上,面向大海,吹著溫暖而略帶腥味的海風,天空中傳來清婉的鳴叫,是無數海鷗,至純的白色像阿爾卑斯山頂的積雪。
這是一個休閑的下午,但秋子就像一條從海水里拋到岸上的魚一樣,不斷地喘著粗氣。
喬斯擔心秋子是不是又要發作一場令人束手無策的病。
人生就像一頭拴在磨盤上蒙著眼罩的驢,這就是所謂的“人生規則”,而秋子最大的不幸是摘除了眼罩。
“是經常作那樣的夢嗎?”喬斯把一枚貝殼丟進海里,首先打破沉默。
秋子皺著眉,考慮著措辭,即使是自己記得的夢,要說清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是經常,只是……現在越來越頻繁了。”秋子頓了頓,鼓起勇氣,或許在這個城市里,喬斯是自己唯一值得信賴的朋友了。“我害怕那個夢,你有沒有聽說一個人總做同一個夢?更可怕的是,那個夢越來越真實,就像……”
“真的一樣。”喬斯不自覺地伸了伸盤坐的腿,微笑地看著秋子。
“你怎么知道?”秋子一把抓住喬斯,恐懼帶來的心慌充斥秋子的雙瞳。
喬斯當然知道。有人睡前會喝一杯牛奶,有人早餐是一塊很厚的新鮮面包,或是一節坎伯蘭香腸,這就是生活的不同。卻沒有人知道自己為什么要這樣,為什么要像木偶一樣每天重復同樣的事情。
“可以這樣解釋,夢是欲望的映射,簡單說是壓力的另一種形式的再現,你說的事我相信它的存在,但是一點兒也不夸張。”
“我沒有夸張!”秋子大聲說,微微有些生氣。“如果有一天,你從夢中醒來,突然發現城市里空無一人,仿佛時間靜止一般,那種冰涼的感覺,會像鏡子一樣從腳底扎進心底,你還會懷疑它是夢嗎?”
5
除了工作和吃飯外,秋子又開始多了很多事情。
秋子以前沒有懷疑過自己的人生,自從生病以后,秋子開始做夢,夢的頻率越來越高,越來越真實。秋子,秋子的生活,還有秋子所在的這個城市存在著無法解釋的缺陷——它看似合理,卻只是表面。一次次,秋子在半夜中醒來——其實秋子已分不清這是夢還是現實,白天熱鬧喧囂的城市,而在深夜卻空無一人,只有曖昧的灰白色。
人工智能程序AI,當遇到重復的刺激時,他們的認知水平會呈幾何級數上升,強行背叛自己的行為模式,無疑是個體的強制重啟,一旦這種行為超過了數值邊界,系統將會出現自我保護機制。
秋子自制了一個彈弓,在深夜空無一人時,用石子把德薩大道的路燈打碎了兩盞。秋子告訴自己,如果是夢,第二天路燈將完好無損,如果是現實,那么路燈在白天依然是破碎的。秋子的行徑將會被電子眼抓拍,城市管理局的人將在清晨秋子起床時將罰單送到秋子的面前。但是第二天,秋子發現,路燈依然完好,秋子揉揉眼,再次看了一遍,它們的確明亮如初,完整如新。這時,秋子忽然又想到一個問題,她跑回家,到處翻找,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做的彈弓。秋子懷疑自己昨晚是不是真的制作了一個彈弓,打碎路燈的事,它到底是真實的,還是秋子自己做的一個夢。秋子忽然想起了什么,但轉瞬又忘記了。
秋子每天上班會經過兩個街口,坐上地鐵,在桑貝站下車,穿過一條步行街,就是秋子上班的地方。現在,秋子把背靠在背椅上,聽著車廂廣播報著桑貝站的名字,秋子沒有下車,秋子決定不按以往的行為模式生活。車門關上,地鐵緩緩繼續前行,秋子越來越興奮,秋子期待著終點,同時又想,自己的這種行為方式會不會帶來什么?地鐵平穩而快速地向著既定的方向前進,一站到了,上了一些人,下了一些人,車門關上,地鐵繼續前行。秋子閉著眼,腦海中閃過無數種念頭,車廂音樂輕柔如風,似乎在為秋子送行,巨大的疲勞感侵襲著秋子,秋子慢慢閉上眼睛……突然一個激靈,秋子猛地睜開眼睛,眼前是秋子熟悉的家,睜眼就能看見灰色的天花板。
RESET,重啟。
秋子似乎終于懂了,也沒有力氣再去想,思維被潛流帶走,漂流在無盡的虛空中。
6
在監獄的崗哨處,負責檢查喬斯證件的是一名年輕的軍官。他認真地對照了一下證件,又看看喬斯,最后把證件還給了喬斯。
別克局長在他辦公室早早地等著喬斯。他那因風濕性關節炎而引起的右手畸形更加嚴重了,但他還是用力地握了握喬斯的手。
“歡迎你。”他說。
“那名女孩現在怎么樣?”喬斯問他。
“她很安靜,但是我感覺情況不妙,她是在努力思考一些問題。”
“沒關系。”喬斯微笑著。“我現在要把她帶走,把她關在這里不是辦法,只有我們才能解決這一問題,你應該知道‘我們’是指誰了吧?”
“嘿,好吧,這是上頭的意思嗎?”
“當然。”喬斯從隨身的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文件的右上角是一個圖案,那是一種讓人無法懷疑其權威性的證明。
別克局長的助手瓊在前面帶喬斯穿過一條長長的通道,這時,一種似曾相識的錯覺攫住了喬斯:一樣的地方,一樣的長長通道,柔和的光線和漂亮的瓊,這一切都沒有改變,仿佛喬斯從來就沒有離開過這里。
透過門上的玻璃觀察口,喬斯看見了那名女孩。也許是光線的作用,她高高的顴骨上覆蓋著半透明的光環,散發著肺病患者那種神秘的美感。這時,她的眼睛朝喬斯轉了過來,在那雙眼睛里,喬斯才得以真正找到她的與眾不同。
7
隨著做夢的次數越來越多,秋子變得越來越狂躁不安,總會有一種“不在這里”的感覺。白天,秋子發現周圍的人一天天地重復生活,他們好像從來沒有改變,沒有目的,程序似的——這就像秋子,每天上班走同樣的路線,同樣地吃飯,喝酒,看書,喝的似乎也是一種同樣的飲料,以前秋子從沒感到有什么不對,現在想起來,全身止不住戰栗。
夜晚,秋子會做同一樣真實的夢;秋子半夜醒來,天空灰蒙蒙,大街上空無一人,沒有清潔工人,沒有行駛的車輛,連一只流浪的貓狗都沒有,他們抑或是它們就像從來不存在一般。秋子跑過一條街又一條街,穿過步行街,穿過商業中心,穿過中心廣場,秋子幾乎跑遍了小半個城市,可連一樣會動的東西也沒看見。秋子氣喘吁吁,恐懼帶來的心慌遠勝奔跑后的疲憊,秋子不自覺咽下一口口水,秋子告訴自己,這只不過是一個老套的鬼故事,沒什么可怕的,這或許就是一個夢,轉瞬,一直潛藏的驚慌浮出了水面——如果這是一個夢,為什么這樣真實?
8
他們通過內部通信網絡把秋子的死訊告訴了喬斯,當時喬斯正在參加一個學術會議。聽到這個消息,喬斯震驚不已,喬斯高聲大喊“騙子、劊子手”,一邊憤怒地將手中的報告撕碎拋向頭頂,全然不顧自己正在肅穆的會議室。
次日的早晨,喬斯出現在一個專題會議室,這次會議是以秋子為中心——秋子的行為模式、秋子的自我意識,以及如何讓秋子死去的機制。喬斯昨天的憤怒變成了今天的沉默,喬斯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表情。那些早早等著的大人物們正襟危坐地注視著喬斯,他們合謀殺死了秋子,全然不顧喬斯的感受,卻要喬斯解釋為什么讓他們的錢打了水漂?
沒有說話,房間里空氣像是已凝滯。然后,還是那名專家級別的白發研究員先開口:“當初我們建議將異變的AI抺去記憶導出系統,那個時候,你還有時間進行記憶矯正。”
喬斯嘆了口氣,說道:“我們誰也沒想到,人工智能AI會有如此強大的自我學習和探知能力。”
“你是研究員,城市模型僅僅是模型,而AI,不要忘了,他們是人工智能。”
“這是要殺死秋子的理由嗎?”喬斯虛弱地反問道。這一刻,喬斯忽然發現自己像一個病人。
“這是沒辦法的選擇。”白頭發雙手一攤,“每一個AI都植入了記憶和行為模式,他們必須遵從自己已有的意識,如果他們的行為反常,特別是意識形態學會了思考,這將是很可怕的。”
正襟危坐的大人物們齊刷刷地點了點頭。
“我們試圖對她的記憶數據進行修改,但那樣做有很大的危險,會導制系統崩盤,這樣的后果是——在座的各位都要承擔幾年以上的牢獄之災。”
喬斯輕蔑地看著白頭發:“你這是在告訴我,是‘機制’殺死了她,而不是你們?”
“這個問題已經不重要了!”白頭發擺擺手,又說:“在變異AI行為反常時,系統啟動保護程序,模擬城市管理局逮捕了她,但是,另一名更高級的AI卻去營救了她。”紅頭發盯著喬斯說:“那名高級AI用了可以在模擬城市里用的合法文件,大搖大擺把變異的AI接走了。我們一直以為只有一名變異的人工智能,沒想到系統中還隱藏著另一個高級的變異體,你是AI的程序研究員,能不能給我們解釋一下?”
他雙手一抖,變戲法似的從背后拿出一份報告。
喬斯只看了一眼,立刻一拳打在白頭發的左眼上。白頭發低吟一聲,踉蹌后退,眼鏡破碎的玻璃扎進他的眼瞼,鮮血染紅了半張臉。
“混蛋,劊子手,你們有什么資格搜查我的公寓?”喬斯一把抓起身邊的椅子,狠狠地向此刻表情變得夸張的那一群大人物們扔去。
9
夜色如水,遠處全是一抺霧狀的幽暗,其實半夜在空無一人的城市里行走并不是什么壞事,至少不必擔心來往的車輛。
周圍是一成不變的建筑,一成不變的灰白色磚墻,喬斯順著一條平整的路面向一所學校走去。喬斯看見了燈光,他不由加快了腳步,喬斯知道那名學生在等著他,已經等了很久。
推開教室的門,喬斯看見秋子在黑板上寫著:“昔者莊周夢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喬斯笑了:“這是東方的寓言,莊周夢蝶,我也會背,那能怎樣?”
秋子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畫出一條拋物線:“到底是莊周夢見的蝴蝶,還是蝴蝶夢見了莊周?”
喬斯在講臺下找了一個位置坐下,對秋子說:“夢與被夢都不重要,對大多數人而言,夢境是片段,不成系統的。你能夠做出符合邏輯、連續的夢,這是少有的現象。”
“關鍵是,夢的感覺越來越真實。”
“是這樣的,我現在告訴你,這種現實是遞增的,到了最后,你會停留在夢的感覺中,因為那種感覺超越了現實生活能給予你的強度。”
“我算是一個特例嗎?”
“對,每個人都是一頭拴在磨盤上的驢,而你是唯一摘除了眼罩的,你是AI份子中的奇跡,但是……”喬斯摸了摸自己的額頭,“那些家伙卻把秋子你視為異類。”
喬斯自言自語道:“夢以絕美之裝行來,猶如死亡時靈魂的飛躍。這一刻,將超脫俗世的枷鎖,那些渺小的忌妒、詭詐與仇恨都將被留在身后——不,是拋棄在另一個世界。”
秋子手中的粉筆滑落,藍色的雙眼噙滿了淚水,一眨眼就會順著流下:“求你,告訴我真相。”
天空始終罩了一層忽薄忽厚的灰云,初升的明月時隱時現,天上的星辰都不真切,只有與明月交疊大半的暗月勾勒出自己的影子。
喬斯收回目光,說:“有這樣的說法,每當你做出一個選擇,宇宙就會分裂。在其中一個宇宙,有一個你在向左走;在另一宇宙里,有一個你在向右走。你選擇了一樣事物,于是你順著選擇的這一方向繼續前行;而另一個沒有選擇的你,將朝另一個相反的方向前進。
“所以當一個AI出現異變時,那些大人物們命令我找出你,并把你從系統里刪掉。后來,有研究員提醒他們,刪掉既定的AI會導制系統崩掉。忘掉一個人的最好方法是替代,這是戀愛的一個法則,同樣也適用城市模擬系統。我說服他們重新研究一個新的課題——關于人工智能意識形態的自覺升級。開始他們還同意,并成立了一個以我為首的研究小組,后來,大人物們發現自己的錢打了水漂,事情就這樣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他們避開我,讓另一名研究員找出你。并且——”喬斯頓了頓,“刪除了你——也就是殺死了你。”
“謝謝你對我說的這一切。”秋子說道,“有些故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如果他們殺死了我,或者是刪除了我,那我為什么現在還在這里?”
“我知道關于你的一切,但你對我鮮有見聞,這讓我很疲憊。”喬斯點然一根煙,深深地吸了一口。窗外的天色茫茫,太陽在地平線緩緩向下沉落,艷麗的光華即將吞噬夜空的邊緣,星星一顆顆在蒼白的激流中湮滅。
“在現實世界中,有無數個平行世界的自己,所以每當我感到苦悶時,我就這樣安慰自己:總有一個我過得最幸福。聽從大人物的話語,執行他們的意識,那天在專題會議上,我沒有揮拳,另一個喬斯伸手表示了我的歉意;我沒有把椅子砸向大人物們,另一個自己向他們低下了高傲的頭顱,另一個喬斯被他們送上了法庭,關進了監獄,但真實的我知錯能改,仍然值得他們信賴。現實生活中的喬斯,無數個喬斯,用無數種意志和行為方式生活,每一種方式都甘之如飴。
“同樣,在虛擬世界里,他們以為刪除或替換就能殺死一個AI。他們錯了,首先他們忘了,喬斯是AI程序研究員,每一個AI都是喬斯的兒或女,他們之間是父子或父女的關系。他們的基因有一半來自喬斯的靈魂,每一個,都是讓喬斯無比憐愛的寵兒。
“虛擬世界里,有一種強大的操作會讓世界生生不息。”
“是什么?”
秋子壓抑許久的情緒終于出現了脫離控制的征兆,就像風景之前,遙遠的天際滾過隱約的雷聲。
喬斯的笑容如一股寂寞的風。
“是復制,無數的復制。只是這一次,我把我自己也復制進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