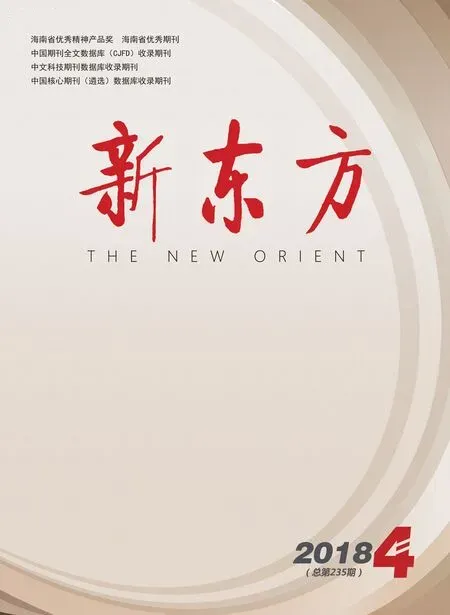鄉村振興中農村金融立法困境與路徑優化
丁 佳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①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17-10-28.這為我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健全農村金融立法提供了思想理論指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指出:“強化鄉村振興法治保障,把行之有效的鄉村振興政策法定化,充分發揮立法在鄉村振興中的保障和推動作用。”②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N].人民日報,2018-02-05.這為我們做好鄉村振興中的農村金融立法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明確要求。農村金融是促進農村市場發展的“助推劑”,應使其沿著民生金融、普惠金融的方向發展與開展,農村金融立法是農村金融規范化、科學化、法制化、專業化的“金鑰匙”,是鄉村振興的根本法治保障。為此,必須建構完善的農村金融法律規范體系和法律規范結構,促進“三農”事業健康發展。
一、文獻梳理及問題提出
國內學術界、政治界從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對“農村金融立法”這一問題進行相關研究,產生了一些具有原創性的理論成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農村金融立法制度改革。如周昌發認為可以通過變革農村金融立法、建立嚴格的農村金融監管法律制度、加強農村信用法制環境建設、加大農村金融司法保障制度這四個途徑來加強農村金融生態法制環境建設①周昌發.中國農村金融生態法制建設研究[J].云南社會科學,2013(2).。劉莉亞認為應著重從金融組織機構創新、金融服務創新、融資渠道創新、風險保障機制創新、金融立法創新來加強金融支持新農村建設②劉莉亞.關于金融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思考[J].經濟與管理,2009(3).。第二,農村金融立法具體實施。全國政協委員鄭鈜認為從加快農村金融立法進程、確定農村金融立法名稱、明確農村金融立法范圍、確定農村金融立法框架、明確農村金融立法內容、完善農村金融立法方式六個維度加強和推進農村金融立法③鄭鈜.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亟需加快農村金融立法[J].中國發展,2018(1).。劉莉亞認為需要從盡快啟動金融立法,將農村合作金融政策法制化和加快民間金融立法研究兩個方向下大力氣。第三,農村金融立法有力保障。學者黃瀟瀟、鄧冰聰從包容理念、可持續發展理念、保護農村弱勢者權利理念三個層面創新指導理念,從實現發展權入憲、制定農村普惠金融基本法兩個層面完善立法體系,從構建金融機構社會責任制度、構建農村弱勢者金融權利傾斜配置制度、農村弱勢者金融權利救濟制度三個層面構建促進普惠金融發展主要制度,以這三個維度內容來完善農村普惠金融立法保障機制④黃瀟瀟,鄧冰聰.論我國農村普惠金融立法保障機制的完善[J].科技經濟市場,2017(10).。當然,還有很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在這里不再一一贅述。顯然,這些成果為我國推進農村金融立法工作提供了借鑒、指導、參考的作用,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之處:第一,研究視角層面,已有的成果主要從宏觀層面進行研究,而中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的研究成果相對不足。第二,研究內容層面,已有的成果要么傾向于農村金融立法的問題及對策研究,要么傾向于框架結構和保障機制的研究,二者融合性研究成果相對不足。第三,研究主體層面,已有的成果主要傾向于服務新農村建設,而服務于鄉村振興的研究成果相對不足。這一方面是因為鄉村振興戰略是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并作為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頒發實施;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具有新環境、新矛盾、新目標,鄉村振興與新農村建設二者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基于此,本文以此為出發點,梳理鄉村振興中的農村金融立法現狀、揭示農村金融立法困境、提煉農村金融立法框架、建構農村金融立法路徑,一方面豐富鄉村振興金融立法問題理論成果,另一方面為實施鄉村振興、健全金融立法實踐提供指導。
二、鄉村振興中農村金融立法現狀
第一,法律完備狀況。在實踐中,我國農村金融工作主要由三家國家政策性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國家開發銀行)承擔金融信貸實施。1993年頒布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對加強支農、惠農政策性銀行法律監管提出了具體明確的規定,但之后的2003年《中國人民銀行法》修訂版又取消了這些具體規定,使政策性銀行和商業性銀行在法律監管方面趨同。隨后頒布的《銀行業監督管理法》附則中關于支農、惠農政策性銀行立法工作保留了一定的空間。目前,就已經出臺的法律法規而言,沒有一套系統明確的、專門的支農、惠農政策性銀行的法律法規。國務院所頒發的《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與下發的各類組建、管理、檢查等通知,皆是以文件的形式呈現,并非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呈現。這表明支農、惠農政策性金融法的缺失使其游離于行政法律法規之外,處于一種“無法可依”的游離狀態。
第二,法律約束力狀況。關于支持“三農”發展的專門法律與行政法規層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以下簡稱《農業法》)、2012版《農業保險條例》均對于金融支農、扶農、農業保險作出了概括性的相關規定,如《農業法》的第45條和第46條,這可以說是金融支農的基本框架,但非具體操作運行,而《農業保險條例》則充當了暫時性、應急性、規范性的金融支農文件。關于支持“三農”發展的農村金融消費權利維護層面,更是缺少系統性、成效性、針對性的法律文件,一般較多的表現為管理部門的一系列工作規定或者管理規定,普遍約束力并不強,自然而然成效就差。
第三,法律系統性狀況。《農業法》從法律層面劃定了金融支農的總體框架和頂層規劃,但未出臺具體的行政法律法規。同時,對于政策性金融機構、商業性金融機構和合作社性金融機構等不同支農主體,在職責、地位等未進行明確、合理的區別,使其法律界限模糊。與此同時,《關于改善農村地區支付服務環境的改善意見》《村鎮銀行管理規定》《財政縣域金融機構涉農信貸增量獎勵資金管理辦法》等分別是由人民銀行、銀監會、財政部所發布的部門規章或者規范性文件。這種條塊分散模式嚴重降低了法律的系統性,大大減弱了法律效果,也大大增加了法律沖突發生的可能性。
三、鄉村振興中農村金融立法困境
現狀是困境的前提,困境是現狀的提煉。通過對鄉村振興中農村金融立法現狀分析,筆者認為鄉村振興中農村金融立法存在立法層級過低、立法定位不清、立法內容錯位三大困境。
第一,立法層級過低。伴隨著鄉村振興作為國家級戰略實施,振興什么?如何振興?靠誰振興?這些都成為實施鄉村振興的時代之問。在實施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涉及到一個資源配置的問題,尤其是資金的配置問題,而金融業雖然具有高風險性,但對農業的促進、運用得當的話,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如何發揮金融助推鄉村振興?如何完善鄉村振興金融立法?學界、政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但就其共性來看,從國家層面研究制定專門的鄉村振興金融法律很有必要。但實際中,關于農村金融的一系列管理規定主要是由國務院所頒發的文件、通知等。從立法層級來看,文件通知并不能代替正式的行政法律法規,致使立法層級過低。這在某種程度上使農村金融實施工作法律缺失,同時對于農村金融監管工作缺少系統性、針對性和全面性。
第二,立法定位不清。立法究竟是為了什么?怎么樣立法?立什么法?這是關系到農村金融立法方向和原則的問題,也更涉及到農村金融立法的初衷和成效。在現實的農村金融立法層面,存在立法定位不清的困境。政策性銀行是執行支農、惠農政策的主體,一方面由于政策性銀行在實施助農活動的同時,又以金融市場主體和金融政策主體的身份參與市場活動,另一方面關于政策性銀行支農、助農、扶農的金融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容易致使政策性銀行如“脫韁的野馬”,這就很容易將政策性銀行與商業性銀行混為一談。尤其是對于政策性銀行具體的定位不強、定位不清,很容易導致不公平競爭現象發生,違背市場原則和市場機制。政策性金融機構立法定位模糊,不僅擾亂金融市場秩序,也不利于鄉村振興的實施。
第三,立法內容錯位。實施鄉村振興,完善農村金融立法,關鍵在于明確農村金融立法的具體內容。但是在現實中,就政策性金融機構而言,相關金融法律存在立法內容錯位,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層面:一是政策性金融機構部分內容存在一定的滯后,立法進度較慢。尤其是對其主業務的規定明顯趨于僵化,容易促使其出現定位不清的危害。二是內容執行性差。有關政策性金融銀行的規定,多是傾向于宏觀領域的法律監管,無法實現設置監管機構的初衷,自然使內容的執行效果大大降低。三是內容缺失。查詢目前政策性金融機構法律文件、規定等狀況,發現在風險防范、監管運行、處理機制等方面未明確規定,這就導致本應規定的內容缺失。
四、鄉村振興中的農村金融立法框架
第一,加強鄉村振興農村金融法治建設。《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積極推進農村金融立法”①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N].人民日報,2017-02-05.,要求加強涉農金融的法治建設,尤其是重點打擊農村存在的一系列非法集資現象,合理引導農村資金有序流動。《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提出:“強化鄉村振興法治保障,把行之有效的鄉村振興政策法定化,充分發揮立法在鄉村振興中的保障和推動作用。”②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N].人民日報,2018-02-05.全國上下掀起一場關于鄉村振興金融立法的大討論。事實上,有關農村金融立法工作早在2009年時就逐步開始。那時,由全國人大農委作為牽頭方,組織協同人民銀行、財政部、銀監會、稅務總局、保監會等等單位參與農村金融立法。規范支農惠農責任、完善支農惠農政策、差別支農惠農監管是當前建設農村金融法的基本框架。但制定一部金融法律,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現實農村出現的所謂金融詐騙亂想,亟需完善配套措施,依法有序深入開展綜合性農村金融治理。
第二,強化鄉村振興農村金融法治督查。一方面要強化農村金融機構的部門責任,尤其是要強化銀監會、保監會等監管部門職責,加強在貫徹國家支農惠農政策方面的作為,是否完全按照政策和要求執行,簽署責任狀。另一方面要明確支農惠農合作社、金融服務公司等的監管部門職責,上級部門要加強督查,嚴厲打擊利用政策的行為,那些既套取國家補貼,又非法集資,傷及百姓利益的行為。同時要警惕當前互聯網金融對農村的副作用,對農村互聯網金融信貸制定出更加科學、合理、有效的監管機制、監管制度和監管法律。
第三,強化鄉村振興農村金融法律責任。關于鄉村振興,樹立穩定壓倒一切、發展壓倒一切、責任壓倒一切的理念,及時依法處理涉農金融民事糾紛。尤其是現在社會高度關注的金融詐騙和非法集資現象,進一步在法律層面明確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二者之間的具體界限,嚴厲打擊以維穩名義損害人民群眾和涉農金融機構的合法權益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保護二者的合法權益就是最大的維穩。妥善處理動產、不動產抵押擔保等銀行金融機構、擔保公司的合法權益和應盡責任(包括業務責任和法律責任),嚴肅處理為非法集資、坑蒙拐騙、損害百姓利益的涉農金融公司站臺的領導干部,對于構成民事犯罪和刑事犯罪的,要依法移交司法機關嚴格處理,以此來強化鄉村振興農村金融的法律責任。
五、鄉村振興中農村金融立法路徑
第一,明確鄉村振興農村金融立法目的。農村金融立法的目的直接決定著資源的調配方式,直接決定著金融立法的實施成效。加強農村金融立法建設就是為實施鄉村振興提供法治保障,促進“三農”發展。為此必須要厘清四個界限:一是要厘清政策性銀行和非政策性銀行之間的界限。二是要厘清非法集資和民間正常借貸之間的界限。三是要厘清正規性金融業務和非正規性金融業務之間的界限。四是要厘清各類金融機構(諸如農村合作社、私募基金等)違法經營和合法經營之間的界限。
第二,明確鄉村振興農村金融立法邏輯。加強農村金融立法建設,必須實現問題導向與過程導向相統一、結果導向與源頭導向相統一。農村金融立法邏輯有兩個層面:一是農村金融立法為了什么;二是農村金融立法如何立。由于存在安全隱患,必須要加強農村金融立法。尤其是現在盛行的非法集資現象,公安機關進行處理時,除了宣傳引導民眾之外,要以非法集資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作為立案處理的參照。也就是說,以結果為導向,并非以源頭為導向——即為什么會產生非法集資現象,如何有效制止非法集資現象。由此所帶來的立法邏輯極易使農村金融立法進入一個誤區,只要資金鏈沒有斷裂,集資人、集資公司即是合法性經營者,反之則是違法性經營者,由這種立法邏輯所帶來的農村金融法律勢必會導致自身的漏洞。
第三,明確鄉村振興農村金融立法結構。鄉村振興是一個系統性工程,農村金融立法也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首先要明確立法的主體。關于農村金融立法建設,當由堅持黨的領導,全國人大農委作為主要牽頭人,財政部、人民銀行、保監會、銀監會等單位部門作為協同部門進行立法建設。關于農村金融立法框架,加強鄉村振興農村金融法治建設、強化鄉村振興農村金融法治督查、強化鄉村振興農村金融法律責任。關于農村立法內容,包括政策性銀行和非政策性銀行立法、產業補貼和金融信貸的立法等。關于農村立法原則,實現黨的領導、以人民為中心、農村金融穩定三者有機統一。關于農村立法目標,既要致力于促進鄉村振興,又要穩定農村金融市場,還要保障群眾和金融機構的合法性利益。
第四,明確鄉村振興農村金融立法界限。首先明確非法經營與合法經營、非法金融機構與合法金融機構、非法業務與合法業務之間的界限。一方面要加大對支農涉農金融機構(包括政策性金融機構與非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合法性檢查力度,包括經營檢查、業務檢查、依法守法狀況檢查等,以此作為判別合法與非法的一個依據。另一方面建議對現有的《合同法》不合時宜的地方進行修訂完善。尤其是涉及重大資金交易、發生行為的地方,進一步規范民間借貸行為,明確民間借貸的范圍、內容、原則、監管等,增強合約意識。其次明確非法金融主體。要依據《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指引》《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金融機構以此為遵照開展業務,避免淪為非法金融主體,監管部門要以此進行監管,防止非法金融主體進入農村金融市場。最后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個人破產制度為制度救濟陷入非法集資或者金融詐騙的百姓提供屏障,盡可能地將其損失降到最低,以此來強化農村地區民間信貸所存在的法律風險和信用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