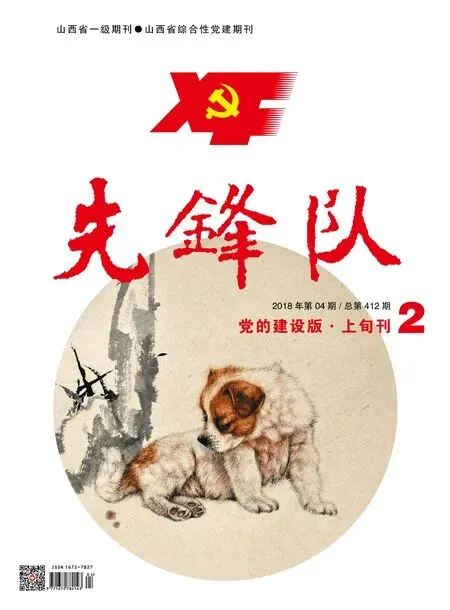走紹興
■ 王哲士
走紹興,第一站便落腳魯迅故里,這是大多數游人的選擇。這里最火爆,火爆的背后折射出一個時代背影,一個文化巨人的背影。在深宅大院的故居和百草園、三味書屋、咸亨酒店出出進進,走走停停,陳年的景象一如魯迅筆下的烏篷船從眼前輕輕劃過,隨著欸乃的櫓槳聲,我的思緒搖進記憶深處……
也是從上海動身,也是搭乘火車,那年那月我孤身一人來到水鄉紹興。
冬雨霏霏,冬水澹澹,冬菜青青……冬日的紹興依舊不乏生機,但在雨霧中猶抱琵琶半遮面,朦朧的可以。沒有雨具遮擋,不通吳儂軟語,幾番打問魯迅故居,聽起來明白,走起來糊涂,在曲曲折折的石板街亂撞了幾個來回,人已然被江南的冬雨愛撫了個夠總算找到地方。
近前一看,只見大門緊鎖,院墻用圍欄圍了,一張“內部整修,暫不接待”的告示,給遠道而來的拜謁者當頭一瓢冷水。這瓢冷水比淋濕了衣衫的天雨還涼,那是透心的涼,失望的涼,無助的涼。好在那時的紹興老街尚存,古風未去,我走過了咸亨酒店,走過了古軒亭口,走過了光滑的石板街,略略溫習了魯迅筆下的風物,沒來得及吃孔乙己的茴香豆,也沒來得及喝紹興黃酒,帶著欲知未知的空白悵惘離去。那時,貧乏的常識和雨霧的朦朧,遮蔽了心田和眼界。在我心中,紹興就是雨色連天中的一盤古鎮,而魯迅或者可以看作是古鎮的象征。除此,對紹興的前世今生,了無印痕。
北國的秋說來就來,江南的秋卻姍姍來遲:山依舊青,水依舊秀,花依舊紅,田依舊綠……二十五年后一個沒有煙雨霧靄的日子,再次走進魯迅筆下的紹興,下榻一處名叫魯鎮酒家的旅舍。在紹興選魯鎮,一者離魯迅故居較近,二者沾魯迅筆墨之光。果真,這次沒費多少腳力,一日光景遍游魯迅故居、祖居和紀念館,也光顧過先生筆下的咸亨酒店,油燭店、茶漆店、錢莊、當鋪……先生筆下的人物,如閏土、阿Q、孔乙己,祥林嫂、假洋鬼子、魯四老爺、阿長……仿佛一個個在古城的長街窄巷、深宅陋室中現身,音容笑貌仿佛又鮮活在你的面前。
魯迅因紹興而文思不竭,紹興因魯迅而名重一時。正是因為魯迅與紹興的不解情緣,寫出如此多的動人風物,感人形象,以及籠罩在那時那地的變幻的風云。他委婉的筆寫下深沉的愛,犀利的筆當作剖視靈魂的刀,同情的筆流露出平民意識,靈動的筆描繪出多姿多彩的風物,當然少不了用彷徨的筆,寫下對鄉土五味雜陳的感覺。鄉愁,始終是魯迅心中的不了情,始終是他人生世界的精神密碼——盡管魯迅對故鄉的情感比較復雜,憶舊與避諱兼而有之,盡管魯迅尋找的真正精神家園并非現實中的紹興。這些點滴感受是由讀魯迅的課文到讀魯迅的書然后觀紹興風物后的思考。
當然,此次紹興游,收獲還不僅僅在于上次遺憾的補嘗。收獲還在于一個游者的見多識廣。
比如,游了沈園,方知道陸游、唐婉的愛情悲劇在這里留下銘心刻骨的印記,何以為證?便是留在八百歲沈園中一唱一和的《釵頭鳳》。陸游“錯,錯,錯;莫,莫,莫”兩次長嘆;唐婉“難,難,難;瞞,瞞,瞞”反復悲鳴,道盡了多少思念、情怨、悲痛和無奈。世事詭譎,人生無常,一對麗影成雙、吟詩答對的夫妻,硬是被不能見容兒女情長的家母活活拆散。在沈園,在陸游和唐婉離異以后的偶遇地,面對《釵頭鳳》詩墻,那凄婉悲愴的文字,那字字血、聲聲淚的傾訴,即使鐵血男兒也不免黯然神傷。就在唐婉酬答陸游《釵頭鳳》詞不久,竟日思念,抑郁成疾,最終化作一片凋零的秋葉飄然而去。后陸游多次游沈園,每次都有詩記其事。其中一首這樣寫道:“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帳然”。八十多歲的老人,依然讓家人攙扶著游園,為的是憑吊香消玉殞的唐婉。沈園見證了陸唐二人的愛情悲劇,也留下幽怨千古的絕唱。沈園所以留存至今,應是《釵頭鳳》的福佑。斯人已去,傷心常駐沈園,結伴而來的情侶在悲其人時更多的是慶自身。
游了賀知章故居,你為與這位大唐詩人在這里隔著時空相逢而慶幸。賀知章的出名,并不在于他是進士出身,也不在于他是大唐五朝元老、長壽詩人,而在于他發現了李白,舉薦了李白,使李白得以脫穎而出,聞名于世。他的出名還在于他的那首被人稱為《唐詩三百首》七絕第一的“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回鄉偶書》應是在他告老還鄉時隨手所得。詩中山河依舊,人事不同的感覺最是滄桑之筆,最能打動人心。記得鄉愁、縈繞鄉情的人最能為人記得。賀知章就是這樣一個人。
游了秋瑾故居,為文脈涌動之地擊節嘆賞的心情還未平復,又為仗劍報國的俠客之鄉再掀波濤。秋瑾自幼習武射騎,目睹國勢危急,清廷腐敗,便立志反清革命獻身救國事業。作為兩個孩子媽媽的秋瑾,兩次東渡日本留學,辦刊物,結同志,寫詩作文,提倡女權,宣傳革命。回國后首次策劃起義未果。二次策劃起義,因事泄被捕,在紹興古軒亭口從容就義。臨刑時仰天悲嘆:“秋風秋雨愁煞人”,一腔豪氣從風輕水軟的吳越震驚神州大地。作為革命家的秋瑾以身許國不皺眉,作為詩人的秋瑾,生花妙筆寫剛烈:
“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算平生肝膽,因人常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濕”!
在秋瑾五進院落的故居,陰冷,凝重,崇敬感在悲嘆中油然而生。一位從這里走出來的偉大女性,生命戛然而止于32歲。時光可以丈量生命的長短,卻無法丈量這位革命家的生命重量。匡時淚,醒世鐘,正義血,身后名……紹興的秋瑾,中華的脊梁。
……
魯迅街的盞盞燈籠映出一片緋紅。夜色朦朧中,人們游興依然不減,生意隨著游人火爆。落腳咸亨酒店,一式木結構,木陳設,極盡雕飾華麗之美。圍著八仙桌坐定,點了紹興特色小吃梅干菜扣肉,紅燒豬手,花生豆等,當然忘不了孔乙己的茴香豆和紹興黃酒。在這里用餐,可以與孔乙己隔著時空交流,還可以由孔乙己牽出阿Q、閏土們,少不了作“物換星移幾度秋”的感慨。這頓飯,家人吃得很舒心。
三次走紹興,這一次才算游得從容,吃得舒心。酒足飯飽,街頭散心,穿行在昔日越國都城的心臟,我對著紹興輕輕說:紹興,我還要來。水鄉、橋鄉、酒鄉、書法之鄉、名士之鄉、魚米之鄉,你知多少?你不得不承認,雖說來過三次,也不過沾了名士之鄉的邊。欲知全貌,不妨再走,圓一個游者未知的欲知的夢是再好不過的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