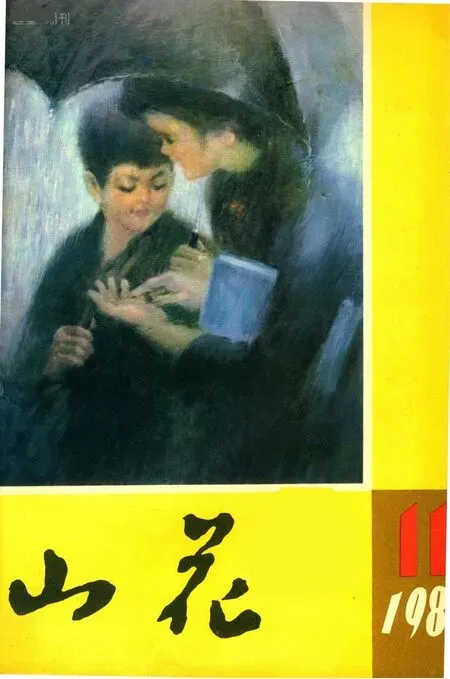遷徙中的全球化歷險:顧雄的藝術及其文化意義
楊小彥
從整體上看,顧雄的藝術實踐是一場徹底的全球化歷險。在這場歷險當中,關鍵詞是遷徙。
1977年,中國恢復了全國高考制度,讓國內的學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隔年,顧雄從西南農村一名知識青年,遷徙到了重慶,成為四川美術學院一名大學生。然后,在經歷了掙脫羅網的個人的具有象征意義的反抗之后,他又橫穿太平洋,只身遷徙到了加拿大。當顧雄重新立足在北美這一片土地上時,他又重新開始了另一場遷徙,社會地位與身份的遷徙,從一名普通移民,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最終成為真正的加拿大主流藝術家。
這是兩場相互重疊的遷徙,既包括了社會地位的改變,也包括了生活世界的更新。所以,當顧雄用“大江大海”為名組織他的展覽,試圖表達個人從長江跨越大洋來到菲莎河谷的漫長歷史時,我意識到他思想深處的那一份立意。我明白,不應該把顧雄的遷徙僅僅看成是他個人的移民,他的人生際遇恰恰就是全球化的一面鏡像,一個因子,甚至是全球化進程中的一片波浪。
我一直在想,當顧雄站在哈寧角海灘上,注視著那些來不及運回家鄉的華人先祖的遺骨時,當他堅定地走進一家接一家幾乎無人問津的加拿大國際勞工簡陋的工棚、看著那些艱辛的臉龐時,他內心所翻騰著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情感。
2015年年尾,我為湖北美術館策劃《再影像:光的實驗場》的展覽,邀請顧雄作為海外華人藝術家回來參展。他的作品是《骨屋》。細沙子平鋪在地面上,象征著海灘的存在;墻面屏幕上放映著太平洋岸邊喧騰的海浪,還伴隨著陣陣拍岸的浪聲;另一面墻則是一組照片,顧雄通過拍攝,重組了當年華人清洗先祖遺骨的生動細節。我站在展覽現場,站在顧雄的作品當中,不厭其煩地向觀眾解釋著其中非凡的內容。
當我們只是在一個國度的范圍內訴說著“葉落歸根”的古訓時,我們的感覺充其量只是在描述一種傳統,一種對家鄉的依戀。而在一個世紀以前的哈寧角海邊,華人趁著夜色,仔細清洗先人遺骨,然后包裝好,寄回家鄉重新安葬。這時,他們內心對于“葉落歸根”的固守,就不再是古訓,而是一種使命。然后,當顧雄把這一段歷史作為藝術母題再次展現在觀眾面前時,“葉落歸根”就從使命上升為永恒的信念,用以見證曾經的歷險,那個充滿著悲劇色彩的全球化歷險。
顧雄當初只身一人來到北美,過了一年家人才來團聚,他何嘗沒有體會到“使命”的殘酷含義?我猜想,從他站上北美大陸那一刻開始,其內心對于藝術的認知,就在一瞬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他來說,藝術不再意味著單純的反抗。當身體通過真實的遷徙插入到異域的土地上時,藝術也在與遷徙緊密相隨的過程中脫胎換骨,從反抗的象征性符號,轉變成了真實的生命,并迅速生長為可以每天觸摸得到的活生生的存在。
也就是說,通過這樣一種身體的遷徙,顧雄讓自己直接嵌入到了全球化的進程當中,用每天的呼吸去釋放這一過程所滋生的價值。結果是,顧雄的遷徙就演變成一場貨真價實的全球化歷險,而他的藝術,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這一歷險當中的真實紀錄與文化表達。從另一層面上看,顧雄的藝術成為敏感的個人探針,用以檢測在全球化當中,所有以藝術之名進行反抗與顛覆的真偽。
不管結果是真是偽,檢測本身無疑具有永恒的真實性,從而讓每一次的呼喊成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