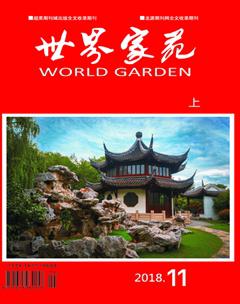從“弄璋弄瓦”看先秦女性社會地位
周媛
摘 要:“弄璋之喜”與“弄瓦之喜”是中國民間關于生男生女的不同說法。語出自《小雅·斯干》,反映了先秦時期人們對于男女的不同態度,“弄璋弄瓦”也成為了一種風俗,流傳于后世。雖然整體上來說,當時已經存在這男尊女卑的陋習,但是由于封建禮教尚未形成,社會上對女性的束縛較為寬松。總體來說,當時的女性地位高于后代。
關鍵詞:先秦;民俗;男尊女卑;女性地位
《詩經》,作為我國第一個詩歌總集,約三百零五篇,記載了西周初到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歷史。其中的《國風》部分,記載了大量的風土人情,描繪了時人的勞動、社會、婚戀生活,成功塑造了各種各樣的鮮活的女性形象。先秦時代,由于儒家思想尚未正式形成,社會還比較開放,束縛女性的封建禮教還沒有出現。盡管由于周朝以確立了男權文化為中心的社會,但總體來說,先秦時代的女性在社會、家庭中的地位高于后朝女性。這一點,在《詩經》中有著明顯的體現。
《詩經》里的女子地位
先秦時期的女子,在婚戀方面比后世有更大的自由。與后朝不同,先秦時代的人們尚未受到儒家禮教的過多約束,在表達情感的時候更加的自由、直白,通過詩歌,抒發了他們對愛情最純真的詠嘆。如《鄭風·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這首詩大體是講青年男女在水邊不期而遇,互生情愫的故事,詩句清新卻又直白,將戀愛的甜蜜描繪的淋漓盡致。在政治生活方面,先秦的女性可以一定程度上的涉足于公共領域。《載馳》一詩,據說是有戰國時期的許穆夫人所作,體現了她一心復國的決心和作為一名女子的政治責任感。總之,通過《詩經》中的大量描繪,我們可以想象出那個時代的女性在社會上有較高的地位、一定的自由。但是,先秦女性的整體地位依然低于男性,社會上依然存有男尊女卑的觀念,這點,從“弄璋弄瓦”這個典故中便可以推知。
《小雅·斯干》中有這樣的詩句:
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々,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這幾句詩如果翻譯成現代文便是:“如果是男孩,就讓他睡在榻床上,給他穿上小衣裳,拿著玉璋給他當玩具。他的哭聲如鐘響,將來一定有出息,穿上顏色鮮艷的禮服,肯定成家立業,成為諸侯,成為君王。”后一段則說:“如果生下個小姑娘,就讓她睡在地板上,給她裹一條小被,給她陶制的紡輪當玩具。教他說話謹慎,操持家務多干活,不給爹娘添麻煩。”這段詩句如此直白,毫無遮掩的描繪出了男孩與女孩在出生后的不同待遇,直接體現了當時社會的“男尊女卑”。其中的“載弄之璋”“載弄之瓦”兩句,流傳了下來,演變成了“弄璋弄瓦”的習俗,可見《詩經》對后世影響之大。
“弄張弄瓦”對后世的影響
古代民間將嬰孩降生稱為“添喜”,當祝賀別人家生孩子時,如果是男孩,要送玉器,如果生女孩,要送瓦(一種陶制的紡錘)。“璋”與“瓦”成為了男孩與女孩的代指,顯示了性別間的云泥之別。誰家生了孩子,親朋好友街坊領居前去探望,便會問“弄璋乎,弄瓦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洵在二十六歲的時候,妻子生了第二個女兒,邀請了他的朋友劉驥前來赴宴。席間劉驥趁著酒興,吟了一首打油詩,調侃了蘇洵。詩句是這樣的:“去歲相邀因弄瓦,今年弄瓦又相邀。弄去弄來還弄瓦,令正莫非一瓦窯?”民間百姓將只生女兒的婦女,戲稱為“瓦窯”,體現了對女性的不尊重。現代著名女作家張愛玲在她的短篇小說《琉璃瓦》中有這么一個情節:“姚先生有一位多產的太太,生的又都是女兒。親友們根據著‘弄瓦,弄璋的話,和姚先生打趣,喚他太太為‘瓦窖。姚先生并不以為忤,只微微一笑道:“我們的瓦,是美麗的瓦,不能和尋常的瓦一概而論。我們的是琉璃瓦。”張愛玲是位優秀的女性,以這樣一種巧妙的方式為被稱為“瓦”與“瓦窯”的女性進行了平反。一方面體現了當代女性平等意識的崛起,另一方面體現了“璋瓦之別”對傳統社會的影響之大。
《詩經》中的大多數作品成于周,周公制禮,某種程度上奠定了男權文化的中心地位。史學家評論說:“周文化是以男耕女織的分工定居的自然經濟形態為物質生活方式和以男子本位、男婚女嫁的外婚個體婚制為主導的婚姻家庭形態為特征的。”這種文化也決定了女性較低的社會地位。這種低地位,在當時女性的婚戀生活、政治生活中皆有體現。在男女嫁娶中,雖然女性有一定的自由戀愛的權力,但是依然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中,孟子說:“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可以看出當時整個社會的輿論對于不按章法的婚戀依然苛責。《齊風·南山》中有一句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另有《鄭風·將仲子》一詩,描述了一個女孩因畏懼父母之言,不敢與心上人約會的故事。“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這三句,可以看出當時的女性在選擇配偶是已經受到了一定的束縛。
作者簡介
[1]程志著:《詩經國風詩性解讀》,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版,第191頁
[2]閔家胤著:《陽剛與陰柔的變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頁
(作者單位:中共蘇州市吳中區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