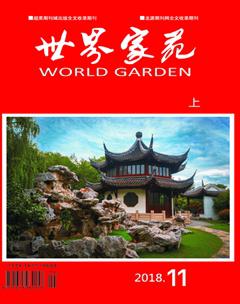論庫切《恥》中的身體書寫
摘 要:J.M.庫切是南非當代著名小說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文學教授,也是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庫切于1999年發表的小說《恥》聚焦一位南非本土的白人教授的個人生活,揭示了南非后殖民時期白人知識分子所面臨的生存困境。本文借助后殖民主義理論及其語境,通過《恥》中對女性身體、膚色差異的身體,及動物身體的書寫來闡釋小說文本中內蘊的后殖民問題與現狀。
關鍵詞:庫切;《恥》;身體書寫;后殖民主義
《恥》是庫切1999年出版的作品。小說的主人公盧里是一名52歲的白人教授。小說第一部分敘述盧里的個人生活:小說開頭部分通過盧里與妓女索拉婭的雇傭關系來表現盧里對婚姻、愛情、性的態度。后來,他因和自己的女學生梅拉妮發生情愛被指控性騷擾,他因拒絕對此事懺悔被迫離開大學,來到女兒露西在鄉下的農場幫忙打雜;第二個部分通過盧里的視角敘述了盧里與露西在鄉間的生活,是小說的主要意圖所在:盧里來到農場后不久,父女二人就遭到了當地三名黑人的搶劫,致使盧里被燒傷,露西被強暴,事后盧里與女兒露西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及處理方法,盧里認為應該馬上報警,女兒露茜則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她最后嫁給了自己的黑人雇工佩特魯斯。
一、膚色差異的身體間的暴力循環
膚色作為一種生理的顯在差異,在殖民主義歷史中被扭曲成了文化差異,白人通過膚色政治,使身體成為殖民機制運作的物質基礎,認為白色代表干凈、美麗與文明,黑色代表骯臟、丑陋與野蠻,從而進行對黑人的身體規訓。而后殖民時期,種族隔離政策被廢除,黑人獨立后成為了新的社會主人,黑人與白人文化迅速交融。黑人權利得到更多實現的同時,文化觀念的不同導致了社會秩序的混亂。在充滿復仇心理的后殖民社會,階級統治和種族不平等似乎又以新的形式復制著殖民主義模式的恥辱,從而呈現出暴力循環的復雜社會現象。
一方面,庫切通過黑人暴行對盧里和露茜造成的身體創傷和精神創傷指出了南非傳統惡習造成的殘酷傷害,揭示了種族隔離制度的必然性及其畸形后果;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后殖民時代白人和黑人微妙的關系變化。小說中,露茜作為一個白人,住在黑人的包圍之中。曾經是雇主的露茜,曾經是大學教授的盧里,現在也都給黑人佩特魯斯打下手。南非白人已經失去了權力上絕對的養尊處優,白人文化優勢不再,但思想文化上仍然保留著先在的優越感。盧里就有著濃重的殖民主義思想余毒,他心底里帶著一種文化優越感,喜愛華茲華斯、拜倫等浪漫主義詩人,就像一個老派的歐洲知識分子。
盧里看待黑人雇工佩特魯斯也是如此,在女兒建議他給佩特魯斯打下手時,他說他“喜歡帶點歷史味的刺激”;在經歷暴力事件后,他立刻帶著固有偏見地懷疑佩特魯斯。盧里所代表的白人所具有的文化優越感失去了社會地位的優勢保障,在身處黑人文化中時,就顯得十分尷尬。小說中描寫了盧里與佩特魯斯之間的溝通不暢,揭示了異質文化之間的深刻隔膜。而女兒露茜正好與父親相反,能夠融入黑人的圈子,面對黑人的暴行,露西認為這是想要在黑人圈子里生存必須付出的代價,她以身體與尊嚴為代價,做佩特魯斯的第三個老婆,從而獲得了被保護權。佩特魯斯認為露茜采取的對策是懂得向前看,而盧里卻不懂。小說通過盧里與露茜二人觀點的交鋒,揭示了后殖民時代南非白人遭遇的文化沖突與尷尬的生存困境。
露西接受了“一無所有”的事實,接受了白人必須付出的代價。白人為了取得黑人圈子的認可,必須付出代價,按照他們的文化方式行事。南非的白人知識分子之所以遭到對話困境,被逐出圈外,原因是他們仍堅持用自己的固有觀念來應對已經變化了的時代,想要達成和諧,就需要白人知識分子與時俱進,接受黑人與白人已經平等的現狀。
庫切看到了政治權利上的平等隱藏下的深刻矛盾。通過身體視角,他將盧里對有色人種學生的身體傷害與女兒露西遭到黑人強暴兩個身體暴力性事件并置起來,后一次事件是對前一次事件的再現,前一次事件的加害者變成了后一次事件的受害者,將主人公放置在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位置上,是在告誡人們歷史不應在暴力中循環前進的同時,倡導建立一種新的歷史倫理規范:只有建立起一種新的體現人性價值的歷史倫理,才能使深陷暴力泥潭的南非走出歷史的陰影,使整個人類的歷史擺脫暴力的輪回。
二、動物身體的隱喻
動物話語一直充斥在小說文本中。首先,庫切將人類的權力架構通過動物身體的隱喻活生生地展現出來。在前半部分中,盧里教授作為強權一方侵入了弱勢一方的身體。他的第一次越界行為就運用了動物的隱喻,將自己的越界比喻為猛獸闖入幼狐的窩。類似的比喻也出現在盧里與梅拉妮的關系中。
庫切通過動物行為突出了作為弱者的動物身體,一方面將這種強弱對比放置在動物群體本身,一方面又放置在與人類群體的共處之中。在人類社會中,動物不屬于權利構架的政體,它們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決定根本沒有發言權。小說中,露茜家的幾條狗被黑人闖入者殘忍屠殺,這在某種程度上與露茜遭到暴行是一樣的——面對暴力,弱者都束手無策,所以盧里才會說“像狗一樣”生活。盧里與露茜保護不了動物的生命,也捍衛不了自己的尊嚴。對于動物,盧里只能掩埋它們的尸體;對于女兒露茜,盧里也只能忍受這份恥辱。
小說中對盧里道德提升的標準也是透過他與動物的相處來體現的。一開始,盧里對動物的態度是認為動物沒有地位,認為人與動物屬于不同層次,但逐漸的,盧里在不知不覺中與動物變得親近,甚至在狗籠里睡著,任由狗嗅著自己的臉。他也開始將動物與人進行比較,認為它們“沒有階級區別”。
動物充當著救贖人類的角色。當暴行發生時,是狗與施暴者搏斗來保護受害者,自認為“高層級”的人類被“低層級”的動物所拯救,與盧里被白人文化圈驅逐后來到露茜所在的黑人文化圈尋求庇護是相似的。庫切通過動物身體隱喻,對殖民暴力給殖民地人民造成的傷害給予了人性關注,批判了西方文明中淺薄的道德感與殖民主義賴以存在的傳統理性哲學,并倡導人類彼此之間、與他者(包括動物)之間建立平等、友善、相互尊重的和諧關系。
“恥”表示恩寵不再,人失去了上帝的庇佑的狀態,這與后現代人意義的不確定性恰好相合。這個“恥”是盧里的“道德之恥”,是露西的“個人之恥”,也是小說結尾白人尋求黑人庇護的“歷史之恥”。黑人在歷史中承受了恥辱,由此對反過來給白人以恥辱,對他們施行報復的原因,可能就是要看到白人的這份恥辱。人無時不在“恥”之中,“恥”既束縛了人類,也因其存在而引導人保持高貴性。庫切通過這幾種“恥”的身體書寫,對權力侵越及暴力循環的南非后殖民問題進行揭示與批判,他的意圖是深刻的,不僅僅是在后殖民大歷史背景有著言說意義,在整個人類歷史進程中,在后現代的社會語境下,庫切都有著洞悉現實的力量。
參考文獻
[1]J.M.庫切.恥[M].北京:譯林出版社,2003.
[2]張勇.話語、性別、身體:庫切的后殖民創作研究[D].山東大學,2013.
[3]彭盛盛.南非轉型與庫切之“恥”[D].東北師范大學,2011.
[4]鄧禎.庫切《恥》中的動物文化功能[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14(11).
[5]沈賢淑,王燕.意識·身體·沉默——庫切小說語言的歷史性探索[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6(4).
作者簡介
周易(1994.03-),性別:女,民族:漢族,籍貫:浙江余姚,學歷:本科,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作者單位: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