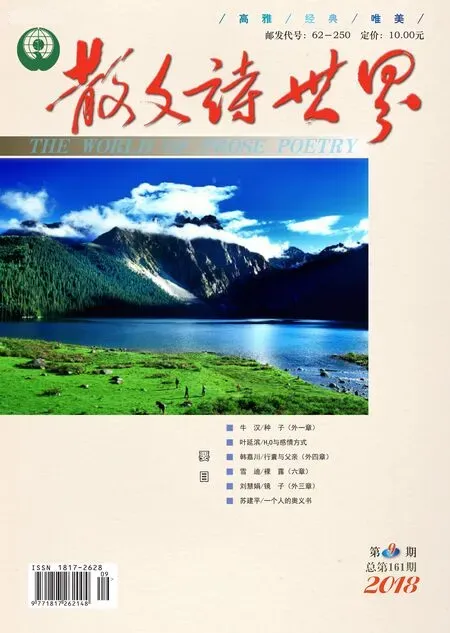古典漫游(四章)
四川 史 鷙
在中原大地尋找一位女子
我用目光作座下的白馬,在地圖上把中原一次次走遍,遇見平原我走得很快,面臨高山我行動遲緩。挨家挨戶我都上去敲門,客氣地問,“可曾見過一個白衣女子?她有美麗的笑靨,明亮的眼睛,眉眼間帶著憂郁三分。”所有開門的都聽我客氣地說完,然后說沒見過,吱呀關上門。只有一個人答說見過,可是她向東已走了五個時辰。
我尋你已有八年,在所有的村落一一打聽,棄我而去的北方姑娘,只因你說你是中原大地的女兒,我就注定對中原滿懷深情。我走得很艱難,很累,馬兒焦燥地趵著蹄子,我不知是否能在一個落日黃昏,一扇門突然打開,你出來,撫去我頭上的風沙,說:茶飲已燒好,我等你很久了。
朱雀橋邊尋訪一位古代女子的故居
我夢見八月的月光如水銀瀉地,香霧沉酣,桂樹婆裟的舞影在欞廊之間搖曳,清風送來鳳幃之后的琴聲。我,一個現代的書生,在夢里被古代的看門人疏忽,輕易進入了你長滿誘惑的后花園,在恍惚的月夜,窺見了你前朝閨秀月光一樣皎潔的臉,和極度溫柔的一瞥。一瞥之后,你低下的頭再也沒抬起來,你的纖纖秀足,在欞廊之間很快消失,裙裾飄舞,像愛情一樣恍惚。我呆呆地看著你像仙女一樣出現,而又消失,心旌搖蕩,不能自持。我的心隨你拐過左邊的欄桿,又拐進右邊的月亮門,有盈盈的笑語,和遠遠的紅燈。我繼續跟著你走,直到迷失在大片的木槿樹邊。桂花的香氣讓我迷醉,而愛情更讓我心醉神迷,難辨東西,你已經在八月月光和香氣渾和的輕霧間躲得無影無蹤。
我醒來,昏沉的瘴氣讓人窒息。披衣起床,看見現代女子的肚皮在朱雀橋邊白得晃眼,商販的吆喝一如往昔。枕邊并沒有你有意遺失的手帕或者詩巾。我張皇失措,向路人詢問,沒人知道你去了哪里。我茫然若失,失魂落魄,腰插一柄木劍,遍尋不見你幽怨的眼睛,誰來慰我猶懷古典的心?
在五里湖險些撞入采蓮女懷里
五湖桔紅的暮色里,我的船駛進了一處蓮塘,茂盛的荷葉像一面厚厚的墻。荷花朵朵,蓮蓬在我的前后左右縈繞,驚起的野鳥撲楞楞飛入遠處的高樹。我忽然失去了方向,東張西望。這時,荷塘深處傳來陣陣笑聲,一只小船兒從荷葉中穿出,船上的妙人兒輕輕地哼唱,脆生生地笑。她們輕快地彎腰摘下蓮蓬,水紅的衣衫像是褪下的蓮衣。她們看見了我,吃吃地偷笑,有人故意向我撩水。我看見她有清秀的臉,我不知該說什么,也不會唱她們的歌,傻愣愣地看著她們從身邊駛過。我說我是來自二十世紀的款哥,可有誰愿當我的小蜜,我的寶馬車可勝過一葉蚱蜢舟。
她們笑了,那些在夕光中回頭時美麗的臉龐啊充滿詫異,滿布疑問,她們說她們可不稀罕薄情的官家子弟,只愛水鄉自由的兒郎——
深夜的水邊遇見飲酒的漁父
夜色如此深沉!我呼吸困難。燭火黯淡,光亮弱不禁風,一棵稻草就快要被世俗壓死。而你那邊月明風清,江上泛著千年的光,不系之舟自由散漫。漁父!干渴的心期待深夜的水,深陷塵世的人,已快被濁流淹沒了頭頂。而你在江上飄灑的釣絲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嗎?可是我無法成為江中自由的游魚,我必須成為有腳的走獸,脊背是我們無法卸下的包袱。我是父親,兒子,和丈夫,挺住,他們說挺住就是一切,我于是就挺住,彎曲的脊梁像是彎曲的釣桿,誰是持我在手的漁父?你不發一言,顯得那么渺遠。我永遠只看見你在月光下飲酒,你衣帶飄逸,歌聲嘹亮,在江湖上越去越遠,越去越遠,成為后世書生無法企及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