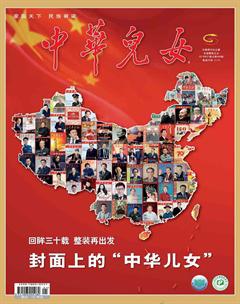莫言 紅的不僅僅是“高粱”
張小華
2012年10月11日晚上7時(北京時間),瑞典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莫言。消息傳來,中國文壇沸騰了,“恭喜莫言”的聲音四起,“MO”也迅速成為全球各大媒體的頭條熱詞。
《中華兒女》記者余瑋在莫言獲獎后寫了一篇封面文章《莫言 諾貝爾獎得主的苦難輝煌》,發(fā)表在雜志2012年第20期上。

在中國當代文壇,莫言的寫作特色十分鮮明。他受到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和美國南方作家福克納等影響,吸收西方文學營養(yǎng)講述中國鄉(xiāng)土故事。同時,他始終一腔熱血地關注當下現(xiàn)實,又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作家要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
“尋根文學”作家
在媒體公開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前20分鐘,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彼得·恩隆德用電話給正在山東高密家中吃晚飯的莫言,這時他才獲悉自己獲獎,反應是“overjoyed and scared(驚喜并惶恐)”,微微地點了點腦袋、晃了晃身子。“(之前)沒有太多的期待,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全世界有那么多優(yōu)秀作家,中國也有很多優(yōu)秀作家,一年只頒一次獎,只頒給一個人,我覺得好像排了一個漫長的隊伍一樣。”
與往年相似,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就年度文學獎向媒體提供的新聞稿僅一頁紙,實際內容僅兩行文字。這段文字的核心內容涉及對莫言的評價,即這位中國作家“以魔幻現(xiàn)實主義融合民間故事、歷史和現(xiàn)實”。
在與新聞稿同時發(fā)布的4頁紙背景資料中,評審委員會提及莫言的個人信息,包括生長和成長環(huán)境、職業(yè)經(jīng)歷以及寫作歷程。
資料尤其提及,以家鄉(xiāng)山東省高密為寫作素材,莫言的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以二十世紀幾十年為跨度,述及日本侵略軍對作者家鄉(xiāng)的占領。
莫言的“高密東北鄉(xiāng)”,如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一樣,成為一個奇特藝術世界。獲諾獎后,莫言表達了對故鄉(xiāng)的一往情深:“我的故鄉(xiāng)和我的文學是密切相關的。”莫言十分鐘愛故鄉(xiāng),視故土為“精神的根據(jù)地”,將自己對故土的愛戀化為藝術元素,這是莫言創(chuàng)作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莫言一系列鄉(xiāng)土作品充滿“懷鄉(xiāng)”、“怨鄉(xiāng)”的復雜情感,被稱為“尋根文學”作家。他曾提出“所有的文學都是鄉(xiāng)土文學”的觀點。“過去鄉(xiāng)土文學只是指農村,現(xiàn)在看來是偏狹義的,時代在發(fā)展,鄉(xiāng)土的內涵也在變化。現(xiàn)在鄉(xiāng)村在發(fā)生變化,鄉(xiāng)村與城市的差別在縮小。另外鄉(xiāng)土與故鄉(xiāng)是同義詞,每個人都有故鄉(xiāng),即便是我住在北京也和故鄉(xiāng)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所有的文學都依賴鄉(xiāng)土,荒郊野村是鄉(xiāng)土,繁華都市也是另一種鄉(xiāng)土。”
“我曾經(jīng)對高密東北鄉(xiāng)極端熱愛,曾經(jīng)對高密東北鄉(xiāng)極端仇恨,長大后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我終于悟到:高密東北鄉(xiāng)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我的父老鄉(xiāng)親們,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種植。”這是莫言曾寫下的一段文字。在50歲后,莫言越來越戀家,每年,他都要回到高密住上一段時間,尋找創(chuàng)作靈感。
有位作家說,莫言的小說都是從高密東北鄉(xiāng)這條“破麻袋”里摸出來的。但莫言認為,正是這條“破麻袋”,讓他的文字有了獨有的風格,為他贏得了諾貝爾獎,“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原因。”
《豐乳肥臀》通往莫言的文學世界
1988年,電影《紅高粱》獲得西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金熊獎,引起世界對中國電影的關注。“當時,我在高密東北鄉(xiāng)的一個供銷社倉庫里寫作,我一個堂弟跑來,搖晃著一張報紙對我大聲喊叫:‘《紅高粱西行》!《人民日報》整整一版!”
小說《紅高粱》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后取得巨大成功,成為中國第一部走出國門并榮獲國際A級電影節(jié)大獎的影片。這使得莫言成為當時最炙手可熱的作家。
《紅高粱》創(chuàng)作始于1985年。一次,總政在北京西直門招待所舉行軍事文學創(chuàng)作座談會。一批老作家憂心忡忡地說:“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只打了4年,可是描寫衛(wèi)國戰(zhàn)爭的優(yōu)秀作品一批又一批。我們中國有這么長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28年的戰(zhàn)爭歷史,解放以后有這樣那樣的邊境戰(zhàn)爭,為什么我們寫不出自己的偉大的軍事文學作品?眼看著我們就寫不動了,而青年作家又沒有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怎么辦呀!”
怎么辦?莫言接過話頭,說:“我們雖然沒有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但參加過演習;我們雖然沒有打過鬼子、殺過人,但在家不還殺過豬、宰過雞,咋就寫不出來呢?放心吧,我們不是吃白飯的。”當場就把老人家頂了回去。一位著名的老作家顯然生氣了,站起來斥責莫言說:“年輕人呀,別太狂妄!”
理論解決不了的問題,只好交給創(chuàng)作了。莫言說,當時就憋了一股氣,非要寫幾部戰(zhàn)爭小說給他們看看。于是,便有了《紅高粱》、《奇死》等一系列戰(zhàn)爭小說。
“《紅高粱》大概就寫了一個星期,草稿就出來了,然后一邊抄一邊改又用了一個星期,累計起來一共是兩周。寫完了以后我心里很不踏實,因為當時軍藝有個很好的習慣,就是一旦作品出來以后同學們之間會互相交流看作品。當時我的《紅高粱》也給幾個比較要好的同學看了,他們的反映比較差,說《紅高粱》還不如《透明的紅蘿卜》好。”于是,當年莫言就想,可能是走得太遠了,但是后來這部小說的火爆程度出乎他的意料。1995年春天,莫言花83天完成了他最具爭議的作品《豐乳肥臀》。“1993年母親去世之后,我一直想寫一部關于母親、生殖、大地的厚重小說,《豐乳肥臀》寫完以后覺得如釋重負。”在《豐乳肥臀》的扉頁上寫著“獻給母親在天之靈”。
洋洋50萬言的小說《豐乳肥臀》因內容尖銳而引起軒然大波。在他獲得“大家文學獎”10萬元獎金后,各種冷嘲熱諷接踵而至,批判、挖苦源源不絕。但也有人說這是一部杰作。對于爭議,莫言曾說:“我覺得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如果要了解我的文學世界,你應該看看《豐乳肥臀》。”
莫言的文學創(chuàng)作,風格獨特、語言犀利、想象狂放、敘事磅礴,在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中獨具魅力。《紐約時報》書評曾說:莫言是一位世界級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對莫言的文學成就很推崇,認為他的創(chuàng)作代表了亞洲的最高水平。
迄今為止,莫言和他的作品榮獲了海內外諸多獎項:1987年全國中篇小說獎、1988年臺灣聯(lián)合文學獎、1996年首屆大家·紅河文學獎、2001年第二屆馮牧文學獎、2001年法國儒爾·巴泰雍外國文學獎、2002年首屆鼎鈞文學獎、2004年第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成就獎、茅臺杯·人民文學獎、法國“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勛章”、2005年第十三屆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2006年日本第十七屆福岡亞洲文化獎、2007年“福星惠杯”《十月》優(yōu)秀作品獎、2008年香港浸會大學師姐華文長篇小說紅樓夢獎、2011年獲因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大地上喚醒了人們沉睡已久的文學熱情。由“莫言熱”帶動起了“讀書潮”。他也被追問“你幸福嗎”?他回答“不知道,我從來不考慮這個問題”。在他看來,“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莫言還在努力放下,但他已經(jīng)把諾獎由神話變成了中國人的身邊故事,讓中國人和中國作家有了一顆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