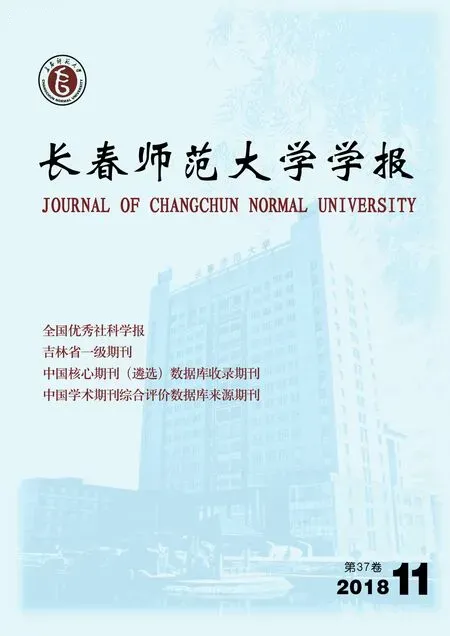自住型商品房政策的經濟法分析
石 晶,曹 喆
(1.人民教育出版社 戰略發展部,北京 100081;2.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 100029)
在住房制度改革中,我國基本確立了以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為主的供應體系和以住房公積金制度、貨幣化補貼和商業信貸供給為主的配套支撐體系,并出臺了大量房地產調控政策,包括產業政策、土地政策、財稅政策、貨幣政策等常規手段,甚至在一些熱點城市出現了標準各異的限購政策以及向特定對象供應政策性住房等非常規手段。2013年北京正式推出具有共有產權屬性的自住型商品房,即房地產開發企業通過“限房價,競地價”的出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按照限定銷售對象、限定銷售價格(比周邊商品房低30%左右)的原則,開發的一種戶型以90平方米以下為主的政策性住房。其功能以平抑房價、解決政策“夾心層”住房問題為主,目的是實現“居者有其屋,弱者有保障,保障有限度”,緩和由房價居高不下帶來的社會矛盾。自住型商品房政策作為政策鏈條中的一環,是對現有法律體系下房產所有與占有、使用與流通的關系作出的突破性發展。因此,深入研究自住型商品房政策的制度內涵,科學評估其實施效果,進而有針對性地提出完善對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自住型商品房政策的出臺背景
(一)高漲的民生訴求
目前,房價超過普通家庭的購買承受力已是不爭的事實。世界銀行認為,房價收入比的比例應該控制在5倍以下,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一般在1.8~5.5倍為合理,發展中國家控制在3~6倍較為合理。然而,我國在2005年就已經超過了8倍。[1]不難發現,供需關系尤其是一線城市住房的供需關系失衡十分嚴重,直接導致房價畸高。
(二)過熱的房地產投資
房地產行業利潤豐厚,投資標的穩定成為投資者規避風險的目標。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環境中,資本流動與資本投資均是正常的市場經濟現象,但過度投資可能會給居民正常居住需求帶來不適當的抑制。畢竟,“居者有其屋”表征了社會個體的基本權益,房價過高會凸顯市場投機的濃重氣氛。對房地產市場呈現出的過熱現象,政府方面不能坐視不管,必須兼顧社會秩序及個人權益的維護。
(三)開發結構缺乏合理性
在理想的自由競爭市場環境中,對利益的追求是基本的發展動力。市場主體將逐利性作為自己生存、發展的第一動因。硬性要求企業開發照顧中低收入群體利益的低端房地產項目而不顧其利潤考量是不現實的,也是有失公允的。就當前形勢而言,應進一步落實政策性住房的相關決議,完善多層次住房供給體系,積極探索共有產權、階梯型房產消費等新的模式。
(四)房地產調控政策的法律效力
中國現有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多以“通知”“意見”“實施細則”等文件形式出現,在行政法上被稱為抽象行政行為,區別于狹義的法律法規,因而政策性大于法律性,臨時性大于穩定性。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制定主體相對多元化,且多數制定主體的位階低于法律法規的制定主體,意味著政策效力低于法律法規效力。我國目前相關法律法規的貫徹、實施往往滯后于政策推行,相關部門在相關通知性文件方面往往顯現出更大的積極性與主動性。[2]就當前的房地產市場而言,宏觀與微觀的調控政策往往發揮著重要作用。政府相關部門一般圍繞相關政策來推進相關措施,同時也在推動由政策主導向法律主導的轉變。就行政力量而言,應更加注重民眾福祉,更加審慎地對待政策的制定與推定。在這一背景下,自住房政策具有更加充分的穩定性與預期性,應該在整個格局中占據更加重要的地位。
(五)房地產調控政策和經濟法的聯系
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體現了多領域政策組合的特質,也為經濟法制定提供了基礎。房地產調控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聯系政府、企業、個人三方主體的紐帶,是規制、調節相關經濟關系的手段。此時,政策工具和法律工具的界限也在逐漸模糊。另一方面,政府相關部門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及推行相關舉措,也并不完全屬于宏觀調控的范疇。所謂的宏觀調控,是指政府著眼于社會經濟運行的宏觀層面,通過經濟政策及調節手段,實現其引導與規制社會經濟活動的目的,實現決策者所預期的社會發展愿景。以此觀之,當前的許多所謂宏觀經濟政策或經濟調節政策已經遠遠超出了宏觀調節的范圍,直接對市場主體的行為進行不當干預。在充分尊重與保障社會主體行為自由與經濟自由的前提下進行適度及合理的經濟干預,還需要各界的共同努力。
二、自住型商品房政策的效果評估
房地產市場具體可分為四個市場,即保障性住房、自住型商品房、普通二手房和新建商品住房。本文依據住房“過濾模型”,分析自住房政策推行中房地產市場價格的變動情況。

圖1 保障性住房供給曲線

圖2 自住型商品房供給曲線
如圖1,基于各種因素的介入,在自住房市場中保障性的輪流等候家庭和首次購買的無房家庭會受到優先購買的政策性優惠。從這個角度來看,住房供應增加會觸發相關購買需求的增加,那么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就會相應下降,即需求曲線從D1左移至D2。保障性住房受政府最高限價為P0,當需求曲線實現左移之后,供給缺口會減少,進而最終消失,市場均衡得以實現。
如圖2,在一個理想的市場中,如果自住房供應獲得提升,則供給曲線SA1右移至SA2。由于自住房受到價格限制,其相關價格是相對穩定的。如果相關價格沒有變動,而實際相關需求獲得提升,則需求曲線DA1右移至DA2。由此觀之,自住房政策推動的房地產市場中衍生出的主要效應也就等同于相關房產成交量的增加,即由QA1增長到QA2。當自住房政策的推行獲得一定的實際效果后,基于自住房質量和配套設施不盡如人意的因素,自住房市場會出現購買需求不足的現象,即需求曲線由DA2左移至DA3,由此可能導致需求缺口的出現。
如圖3,新建商品房價格的降低導致一般二手房源的數量遞減,市場購買群體對價格的觀望加劇了一般二手房源的供應降低,即供給曲線由SB1左移至SB2。新建商品房市場的短缺導致一部分需求被轉移到普通二手房市場,使普通二手房需求增加。但是,自住房的需求群體可能會將一般二手房源替換為自住房源。待自住房源獲得實現以后,對一般二手房源的要求會遞減。因此,普通二手房價格由PB1上升至PB2,交易量由QB1下降至QB2。

圖3 普通二手房供給曲線

圖4 新建商品房供給曲線
如圖4,自住房屬于二手房的替代品,目前諸多自住房開發項目被要求搭配籌建,所以如果自住房供應量增加,新建商品房供應就會減少,供給曲線由SC1左移至SC2。自住房的目標人群大多購買能力有限,自住房數量提升后,新建商品房的需求會減少。由于新建商品房供給減少、需求不變,價格就由PC1上升為PC2,交易量由QC1減少至QC2。
在上述假設成立的情況下,自住房政策主要對普通二手房和新建商品房的價格和成交量產生影響。普通二手房市場價格升高,則成交量減少;新建商品房市場價格升高,則成交量減少。所以,自住房政策并不能起到平抑房價的功能。
現實證明,自住房政策并不能起到降低或者穩定房價的作用。一方面,自住房政策沒有全面鋪開,推出的自住房套數在同期上市的保障性住房、二手房、新建商品房總數中占比極少,產生的效果微乎其微。另一方面,自住房政策的宗旨并非穩定或者抑制房價,而是解決“夾心層”的住房問題,面向的是個體的個性化需求,而并沒有著眼于宏觀調控。
相關政策在推行的過程中也會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擾。例如,北京市住建委發布的《關于對〈自住型商品住房規劃設計方案審查要點〉(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的通知》明確指出自住型房源應與一般商品房源在建筑密度、居住密度、綠化指標等方面保持一致。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將這兩種房源予以區別對待的現象不在少數,進而導致需求群體對自住型房源的興趣不高。可見,政策制定是一回事,實際執行及最終效果卻可能呈現出另一種景象。
三、自住型商品房政策的完善路徑
(一)完善自住型商品房立法
自住型商品房推出不久,相關規定還停留在意見階段。應盡快制定自住型商品房管理條例,對自住型商品房的各項規定通過立法形式確定下來。對在自住型商品房的申購、使用和退出環節中出現的欺騙行為,應按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嚴肅處理,對情節較為嚴重的要追究刑事責任,保證自住型商品房政策的有效貫徹、實施。
(二)完善自住型商品房產權制度
自住型商品房是受保障人和政府共同出資擁有產權的住房,其中受保障人出資額占較大部分。作為共有產權房,北京市自住型商品房在最初界定產權的過程中牽涉到合法性問題。如對于北京市自住型商品房,2013年推出時規定:“自購房人取得房屋所有權證后,5年內不得轉讓。”但《物權法》明確規定:“處分共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以及對共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作重大修繕的,應當經占份額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體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間另有約定的除外。”自住型商品房相對而言是新生事物,有關其產權問題的規定還需要不斷細化、調整。
(三)合理確定產權份額分配比例
英國共有產權的制度設計中,最低購買份額為25%,也可以選擇50%、75%的購買份額,直至完全購買產權。我國地方政府在共有產權等保障性住房項目上通常采取減免土地出讓金和稅費等“暗補”的方式。由于政府財力較為有限,發展高政府產權配比的共有產權住房難以吻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因此,在共有產權住房運作前期,可規定較高的個人購買產權比例,使建設單位取得合理收益,使政府不需要直接投入財力進行補貼。政策發展較為成熟后,可依據市場情況合理調整產權比例分配。
(四)加強行政監管
政府有關部門應加強對自住房的監督、管理。在國土資源部門拍賣自住房的土地時,在同等條件下應該優先供給信譽良好的開發商。在自住房上市前,住建部門應會同規劃部門嚴格審查設計方案,督促開發商優化戶型和配套設施。在項目建設階段,住建部門應強化監管,增加對項目的施工現場的檢查頻次,確保工程質量。自住房交房后,應該定期檢查,排除自住房中的投機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