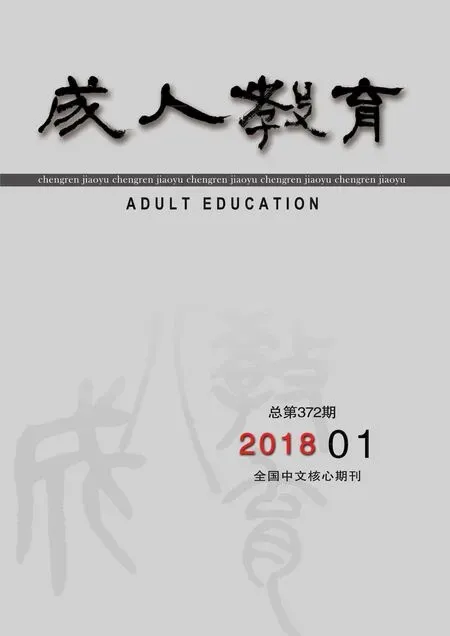再認識和思考高等職業教育人才規格與培養目標的定位
邱 磊,趙 磊,管大為
(武漢船舶職業技術學院 電氣與電子工程學院,武漢 430050)
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必然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適應,重新認識和思考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規格和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有利于實現高等職業教育的健康、協調發展。“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以及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力要創造更多的價值,這個價值來自教育,最直接的就是職業教育。世界上但凡制造精良的國家,如德國、日本,無不是職業教育非常發達的國家。瑞士全球競爭力和世界品牌占有量第一,其職業教育和培訓制度為其綜合競爭力作出了重要貢獻。5世紀至15世紀中國的一系列科技成就,正是由民間無數的能工巧匠的不懈創新傳承的結果,而非科舉制度下讀書人研習經典的產物,因此,中國的高等職業教育有理由在未來重塑輝煌。[1]新形勢下,著眼于“中國制造2025”、“工業4.0”、“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精準扶貧”、“一帶一路”等重大國家戰略對高等職業教育培育技術技能人才的新要求,高等職業教育的使命是為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實的人力智力保障。
只有深入開展高等職業教育的基礎理論研究,才能制定科學的政策方針指導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培養什么人”以及“怎樣培養人”的人才培養模式問題是高等職業教育理論研究永遠無法回避的問題,而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又是該問題的核心。也許我們走得太遠,忘記了當初出發的理由,為了實現高等職業教育的又好又快發展,有必要再認識和思考中國特色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規格與培養目標,回歸原點去反思和追問高等職業教育的元問題。
一、國內外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比較
世界上高等職業教育發達國家的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各不相同:美國定位為當技術員或能從事半職業性工作;英國旨在培養技術工程師;法國旨在培養既有理論基礎又有實踐能力的高級技術員;日本則以終身職業教育為目標;德國的培養目標是“橋梁型”和“企業型”工程師;澳大利亞的培養目標則是技能型人才、高級技術應用型和管理人才;丹麥的目標是發展個性化的職業技能、增加就業能力;韓國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具有先導未來能力的韓國人;芬蘭成立多科技術學院培養高級技術人員;加拿大的社區學院目的是培養具備新經濟時代所需的新技能人才。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從表述到內容經歷了逐步規范、不斷完善的演變歷程。其演變歷程中有幾個重要的節點:(1)1991年10月27日國務院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明確將高等職業教育培養目標表述為“培養技藝性強的高級操作人員”。(2)1995年8月,原國家教委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研討會,明確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是屬于高中階段教育基礎上進行的一類專業教育,是職業技術教育體系中的高層次,目標是培養“高層次實用人才”。(3)2000年1月教育部印發了《教育部關于加強高職高專教育人才培養工作的意見》明確高職高專教育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培養定位為培養“高等技術應用型專門人才”。(4)2005年《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將高等職業教育培養目標確立為“高素質高技能專門人才”。(5)2006年教育部16號文《關于全面提高高職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明確高職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一個類型,肩負著培養高技能人才的使命。(6)2010年7月制定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滿足經濟社會對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7)2011年8月教育部頒布了《教育部關于推進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協調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了高等職業教育培養目標為“高端技能型人才”。(8)2012年6月教育部發布的《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將我國高職教育目標定位在培養“發展型、復合型和創新型的技術技能人才”;(9)2014年5月,國務院印發了《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
二、人才類型的劃分及職業帶理論
在定位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之前,必須明確人才類型的劃分,由此才能準確定位。人才類型的劃分是由社會分工對不同類型人才的需求狀況決定的,對人才類型的劃分有不同的觀念和提法:(1)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活動主要包括兩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亦即對應兩種人才類型:認識世界的人才和改造世界的人才。(2)按人力資源在社會活動過程中的主要功能可將人才類型劃分為學術型(或理論型)人才和應用型人才。普通高等教育旨在培養發現客觀規律、認識世界的學術型人才;高等職業教育則主要培養運用客觀規律、改造世界的應用型人才。[2]應用型人才根據不同層次或工作范圍又可以劃分為三類:工程型人才、技術性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工程型人才把科學原理演變成設計、規劃、決策以及新技術的研發;技術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都是在生產一線或工作現場把工程型人才的設計、規劃、決策以及新技術等轉換成物質形態,二者區別在于技術型人才主要應用智力技能,而技能型人才主要依靠操作技能。(3)“人才四分說”是指社會人才可劃分為研究型(或科學型)人才、工程型人才、技術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然而這四類人才類型之間并非截然分明,存在一定的交叉與重疊現象。(4)因工程型人才的主要任務不是技術應用和現場實施,所以有學者認為技術型和應用型人才屬于應用型人才,而工程型人才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應用型人才。(5)依照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小組2002年發布的報告,當今社會人力資源能力可按體能層次、技能層次和智能層次三個主要層次劃分,并且這三個層次人才對社會發展進程做出的財富貢獻度的比值是1∶10∶100,且隨著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這個比值會日趨拉大。
H·W·French提出的職業帶理論(Occupational Spectrum)是一種體現人才結構伴隨著生產力發展而不斷進化的理論,它將工程領域中的技術工人、技術員和工程師三種類型人才從左向右依次分布在職業帶的三個不同連續區域上。不同區域代表理論知識與操作技能兩個方面的不同能力結構要求。愈靠職業帶的左邊,對操作技能要求愈高,對理論知識要求愈低;愈靠右則與之相反。[3]技術的不斷升級促使職業帶上三種類型人才的結構與分布隨之演化并向右移動(提升)。14—18世紀,職業帶的結構比較單一。18世紀60年代,職業帶上開始出現技術工人和工程師的分化,兩類人才在職業帶有交叉區域。20世紀上半葉,技術的發展促使工程師在職業帶上右移,技術工人和工程師之間開始出現空隙,技術員類人才應運而生,開始填補這一空隙并與上述兩類人才交叉。人才類型的變化決定著教育類型的分化,三種類型人才對應三種教育類型:即培養技術工人的“職業教育(技能教育)”,培養技術員的“技術教育”和培養工程師的“工程教育”。三種類型的教育與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分工密切相關,其區別主要在于“理論知識”和“操作技能”兩個方面所占的比例關系。
三、技術技能人才的認識
高等職業教育要貼近社會和市場,以促進經濟的發展為己任,在新技術革命席卷全球和人才類型需求多元化的背景下提出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要成為適應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要求的現代化技術技能人才,其產生是適應技術進步變化和社會人才需求的必然結果,并符合我國人才類型發展的歷史邏輯。我國的人才類型從技術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再到技術技能人才的演變過程,體現了技術的進步對人才類型演進的影響及社會分工變化對人才類型訴求的變遷。技術技能人才是一種新的人才類型,它的提出促使了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對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改變,是對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類型的最新定位。技術技能人才代表的是既懂技術又會操作的人才:一方面需要具備相關的工程、技術方面的理論知識;一方面需要將這些知識轉換為實際的操作技能。
(一)技術型人才長期缺失的影響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作為職業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技術教育逐漸淡出了職業教育體系,技術教育的長期缺失導致技術型人才出現了斷檔,企業出現大面積技術型人才的缺口,給我國社會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阻礙了中國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我國的高職院校大部分以“職業技術學院”命名,因此其培養的人才類型就不能只局限于技能型人才而不包含技術型人才。技術型人才是客觀存在的獨立人才類型,具有特定的內涵并處于社會人才體系的較高層次,對其忽視會嚴重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競爭力。目前,我國社會人才體系中仍沒有技術型人才的專業技術職務系列,缺乏從“技術員”到“技術師”再到“高級技術師”的專業技術職務上升渠道,導致技術型人才的獨立性地位和重要性容易被忽視,阻礙了技術型人才的培養和成長。盡早地完備專門針對技術型人才的專業技術職務系列,將有利于保障技術型人才的獨立發展,將是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頂層設計中的重要內容。
隨著科技的進步及產業的不斷升級,在職業崗位(群)的分工細化不斷加劇、對人才能力的專門化要求日趨提高的同時,職業崗位(群)的交叉滲透日益增多、對人才能力的復合性要求日趨強烈,使相關職業崗位(群)的工作領域之間存在大量交叉重疊現象,技術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在知識能力結構上同樣存在重疊現象,且沿著技能型人才的“智力技能”成分比例不斷上升、“操作技能”成分比例不斷下降的趨勢發展,這與“職業帶”理論相吻合。科學技術的空前發展導致了產業結構的變革,從而對社會職業崗位(群)產生了重大影響,職業崗位(群)技術含量不斷增加,促使部分崗位由技能型向技術型轉型,進而刺激了整個社會對技術型人才的大量需求。在知識經濟時代,技術型人才及技術創新能力是發展經濟的關鍵要素,技術型人才的重要性不斷攀升,因此需要大力發展技術教育并培養大批技術型人才。使技術型人才在整個社會人才結構中占比適當,是保持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和各產業長期處于中高端發展的制勝武器。
(二)技術教育回歸的意義
技術技能人才的提出表明科學技術發展對傳統定義的技能型人才產生了沖擊,體現了高等職業教育從技能化體系中找回了技術,意味著技術教育的回歸,反映了職業教育對社會人才需求變化的回應,迎合了社會技術革新進步的要求,是職業教育為滿足社會對技術型人才類型的時代需求而做出的必然選擇。技術教育恢復到與職業教育(技能教育)并駕齊驅的關系,不是對當年技術教育缺失的糾偏,而是在新技術革命浪潮的驅動下,對職業教育體系的改造升級,并在其中具有基礎性作用和統領性地位,對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構建和中國特色現代職業教育發展道路的形成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技術技能教育融合了技術教育和職業教育(技能教育)、完善了職業教育類型,作為一種新的、蘊含自身規律的教育,不僅覆蓋了原來的單純的職業教育(技能教育)和技術教育的范疇,而且必將拓展職業教育的發展空間。[4]
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在對技術技能認識時須準確把握技術與技能的關系。技術技能不是技術與技能簡單的物理合并,而是二者深度的化學整合并因此形成一個新的共生體,是關聯互動的關系。[5]技術與技能也沒有層次高低之分,技能水平越高越能推動技術創新;反之,技術的提升會帶動技能訓練水平的提高。技術注重科學理論,技能注重實踐經驗,技術需要技能配合,技能需以技術為依托,技能是應用技術的能力。
四、人才規格與培養目標定位的再認識和思考
(一)人才規格的內涵
人才規格是指對培養對象所需具備的勞動素質、身心素質、能力素質和知識素質的基本要求和規定,反映的是人才的知識結構、能力結構和素質結構三部分應達到的水平和程度,并闡明了相應的人才類型和人才層次的特性要求,是對所培養出的人才質量的規定。制定人才規格時要處理好知識、能力、素質三者協調發展的關系。人才規格的不同從根本上反映的是教育理念的差異,學術型人才的培養規格折射的是理論研究的注重,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規格折射的是實踐技能的注重。人才規格是人才培養目標的細化或具體化,它包含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指的是國家對人才規格的統一性要求;第二層次指的是學校為適應社會的多樣性需求而制定的各種人才規格。對于人才規格的構成要素,二要素法認為包括專業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三要素法認為包括復合知識結構、綜合能力結構和人格素質結構;四要素法認為分為知識、能力、素質和價值。
未來高等職業教育將從只代表專科層次向應用型本科、專業碩士甚至專業博士層次方向發展,最終形成完整的縱向學歷層次體系,不同學歷層次的人才培養目標反映在其定位基準的不同,其規格標準的差異無非是理論知識結構和技術能力結構的權重比例分配不同以及職業性、崗位性要求不同而已。現代高等職業教育的“高”要體現在人才規格的“高素質”上,而“職”要體現在人才規格的“技術技能”上。科學的人才規格定位是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基礎,高等職業教育在人才規格的定位應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人才規格要能有效反映真實的職業崗位(群)要求;二是應以初學者而非成熟從業者的職業崗位(群)要求為參照系推演人才規格;三是人才規格應包含培養對象應該“追求什么”等價值的思考。[6]
(二)人才培養目標的內涵
我國的教育活動一直被列入計劃范疇,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也不例外,其宏觀層面的定位大多由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制定,高等職業院校按其規范和要求進行人才培養活動。人才培養目標是高等教育類型劃分的基本依據,對于高等職業教育來說,是其內在要求和本質特征的體現。所謂人才培養目標是對教育活動的預期結果,是設計出的一種有關受教育者成長的合理性且理想化的未來圖景,[7]規定了培養對象的培養方向以及相應人才規格的基本要求,是教育實踐活動的行動指南,亦是檢驗教育實踐活動成效的標準,決定著教學活動的性質、方向以及人才培養模式。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決定著高等職業院校的價值方向,是辦學的根本性問題,其定位是對其培養對象人才規格的界定,是對培養對象在知識、能力和素質三個維度的預期發展狀態所作的規定。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是人才類型、人才層次和人才規格三個層面的統一。人才類型決定著高等職業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的任務分工與使命;人才層次決定著高等職業教育內部的層次差異;人才規格決定著人才應具備的資格標準。人才培養目標在我國高等職業院校辦學指導中處于較為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或意義可以概括如下:人才培養目標是高等職業院校開展所有教育教學工作的首要思考問題,也是其基本依據;是高等職業院校開展一切教學活動過程的目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落腳點;是高等職業院校開展各類人才培養計劃的總方針原則。
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總是跟隨時代的脈搏而產生相應的變化,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與科學技術進步的客觀要求,其演進過程體現了高等職業教育改革發展與理論研究的水平。興起于20世紀初葉的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思潮,對后來職業教育的發展產生了許多積極的影響,中國職業教育先賢們提出了“德正”、“術高”、“技長”的人才培養目標,堅持技能傳授與人格塑造并重,為我國現代職業教育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基礎性貢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其表述和內容經歷了以培養技能型人才為主基調、不同時期又會轉向其他人才類型的陳述的演變發展過程,并逐步趨于清晰與規范。新時期,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的核心是“技術技能人才”,技術型人才培養的重新回歸是當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方向定位的最大亮點,黨和國家把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從高技能人才聚焦到技術技能人才,為當下徘徊中的人才培養目標定位開啟了嶄新方向。未來由于高等職業教育的大眾化發展趨勢必然促使人才培養目標下移并使其內涵更具包容性。
(三)人才培養目標的確立依據和影響其變化的因素
1.人才培養目標的確立依據
關于高等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從目標定位主體的角度來說,可劃分為國家層面在政策文件中明確的人才培養的總目標、高等職業院校層面在教育實踐中確立的人才培養目標和各個專業層面在行業或區域定位基礎上提出的人才培養目標,它們的確立遵循相對固定的確立依據。人才培養的總目標是以大職業教育觀為指導的宏觀定位。首先,它的確立是以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及產業結構狀況為其根本依據,人類歷次生產組織的變革都伴隨著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的調整,[8]因此其定位必定是與社會生產力水平相匹配的人才規格需求的主動反映;其次,它的確立是以一定的理論為其理論依據,諸如受教育目的論、馬克思人的全面發展理論、多元智能理論的影響;最后,它的確立是以學者在該研究領域的相關提法為其學術依據,學術界對人才培養目標的學術討論一直在持續,并已經取得相當豐碩的理論成果。學校層面確立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各教育機構在實踐中確立的,它勾勒了學校的崇高理想與美好愿望,體現了學校的精神與性格,可以折射學校的辦學水平,就像是學校的一張名片。首先,它的確立是以國家相關政策文件的界定為其基本依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職業教育政策經歷了恢復(1978—1984年)、發展(1985—1996年)、滑坡(1997—2001年)、重振(2002—2008年)、調整(2009至今)五個階段。三十多年的歷程表明: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深受職業教育政策的影響;其次,它的確立是以高等職業教育的自身發展水平為其基礎依據,[9]人才培養目標是否能順利實現,離不開高等職業教育自身的高水平發展為后盾;最后,它的確立是以學生個體發展的需要為其內在依據,只有滿足了個人的成長需求,實現了人的全面可持續發展才是高等職業教育的根本目的。專業層面提出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基于服務區域經濟發展需要、行業崗位需求確立的。首先,它的確立是以服務地方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為其核心依據,因此需要適應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區域行業的變化,形成與區域經濟良性互動的人才培養機制。其次,它的確立是以勞務市場對職業崗位(群)從業者的標準為其關鍵依據,高等職業院校只有準確把握市場對崗位的需求,才能為市場培養出符合行業要求標準的技術技能人才。
2.影響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變化的因素
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產生至今,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經歷了基于不同人才類型的界定,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的變遷受諸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其定位的變化:其一,社會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影響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變化的根本因素。與社會經濟發展尤為密切是職業教育的一個重要特征,促進經濟發展與繁榮是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第一推動力,社會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根本性地影響著人才培養目標的演進。其二,產業的轉型升級及市場需求的變化與要求是影響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變化的決定因素。當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和建設制造強國所需求的技術技能人才給高等職業教育提出了創新人才培養目標的時代要求,因此其定位要在反映市場需求的基礎上兼顧時代特征,實現與產業轉型升級同步對接。其三,高等職業教育自身的基本規律是影響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變化的內在因素。高等職業教育的基本規律與社會發展及人的發展相互影響和相互規約,不是一成不變的,受教育對象、人才市場和行業崗位變化的影響。其四,高等職業教育自身的價值追求是影響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變化的關鍵因素。[10]高等職業教育是堅持經濟性價值取向還是教育性價值取向?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還是工具人?人才培養目標是從社會的發展需求出發,還是從人的發展需求出發,還是兩者兼顧?其五,社會人才觀的轉變是影響人才培養目標定位變化的重要因素。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讀書做官為榮,讀書謀事為恥”等封建價值觀的影響,高等職業教育被視為是“低等教育”,其培養的人才被視為是“二等公民”,社會職業地位也尚未平等。然而,中國教育的大道在于職業教育,隨著“努力讓每個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輕技術、重理論”的錯位現象將會改變,勞力與勞心將都是神圣的。
[1]張力.重新思考職業教育定位[N].光明日報,2016-03-10(15).
[2][6]黎荷芳,查吉德.職業教育培養目標三要素[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3(9):20—23,27.
[3]黃波,于淼,黃賢樹.職業帶理論與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J].職業技術教育,2015,36(1):23—27.
[4][5]喬為.技術技能:技術的技能還是技術與技能[J].職業技術教育,2016,37(4):14—20.
[7]王嚴淞.論我國一流大學本科人才培養目標[J].中國高教研究,2016(8):13—19,41.
[8]查吉德.高職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的新思考[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1(18):12—19.
[9]何應林.高職院校技能人才培養目標確立的依據與程序[J].職教論壇,2015(27):31—35.
[10]閔建杰.高職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再思考[J].湖北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17(3):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