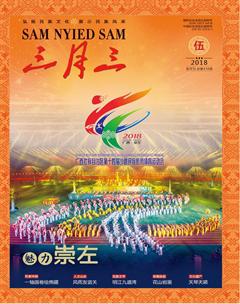懸崖上的伊甸園
周耒



崇左亞熱帶植被繁茂的巖溶地區,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最典型、最集中的喀斯特地貌分布區域之一。這里石山連綿,山雖不高,但山峰挺拔陡峭,拔地而起,懸崖絕壁、巖溶洞穴隨處可見。在這隨處可見的懸崖峭壁中,棲息著一個瀕臨滅絕的物種——白頭葉猴。
白頭葉猴是我國特有的物種,在我國現有的6種葉猴(黑葉猴、白頭葉猴、長尾葉猴、菲氏葉猴、戴帽葉猴和白臀葉猴)中,只有白頭葉猴為我國所獨有,并且僅僅分布在廣西左江和明江之間一個十分狹小的三角形地帶內,面積不足200平方公里,具體地點包括廣西龍州縣的上金鄉,寧明縣的亭亮、馱龍鄉,江州區的羅白、漱湍、馱盧鄉(鎮),扶綏縣的岜盆、山圩、渠舊、渠黎、東門鄉(鎮)。
20世紀50年代初,動物學家譚邦杰在廣西南部龍州縣發現了一張身體修長、頭部和兩肩白色、其余部分為黑色、尾部長度超過體長的靈長類動物毛皮,初步判斷這是一種從未被報道、從未被外界認知的靈長類動物。幾年后,在當地人的幫助下,他在龍州縣發現了這種猴子,于是根據體形和體色命名為白頭葉猴,英文名為white-headed langur,拉丁名為presbytis luecocephalustan,并于1955年在《生物學通訊》上發表報告。白頭葉猴成為世界上第一種由中國人命名的靈長類動物。
因為生態環境改變和來自人類生活的影響,白頭葉猴在相當長一段時期里種群不斷萎縮。1996年,北京大學潘文石教授深入原崇左縣(現崇左市江州區)羅白鄉弄官山,開始展開對白頭葉猴研究的時候,統計發現該區域只有200多只白頭葉猴。2003年,廣西師范大學、北京大學和西南林業大學三個單位共同組成科學考察隊對白頭葉猴的數量進行全面考察,得到的數據是600多只。這600多只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比大熊貓還稀少。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白頭葉猴這一物種逐漸被廣泛認知。國家同時積極開展對白頭葉猴的保護,先后在崇左市扶綏縣和江州區設立了廣西崇左白頭葉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弄官白頭葉猴生態園(北京大學崇左生物多樣性研究基地),白頭葉猴種群得到有效保護,截至2016年年底,數量已升至1000只左右。
如今,白頭葉猴仍是全球25種最瀕危的靈長類動物之一,被公認為世界最稀有的猴類。白頭葉猴在國外至今沒有發現活體和標本。在我國《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中,白頭葉猴被列為一級保護動物;在《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獸類》中被列為瀕危物種。專家研究表明,白頭葉猴與人類的親緣關系更近,具有更多與人類相同的遺傳基因,有著更加復雜的社會形態。白頭葉猴的研究價值并不亞于大熊貓,正愈來愈受到生物學界的關注。
成長的顏色演變
白頭葉猴的頭部、肩部為白色,頭頂立著一撮白色的毛發,尾部下半段為白色。白和黑的毛色因不同的個體、比例略有差異。這種黑白兩色的毛色與喀斯特裸露的崖壁顏色十分相似,成為白頭葉猴很好的保護色。在懸崖峭壁上,白頭葉猴與巖石混為一體,遠距離很難發現。初生的幼崽全身金黃色,鮮艷而耀眼,很遠就能看見。一個月后金色的毛發開始慢慢變成灰黃色。半歲后灰黃色慢慢褪去,逐步被黑白兩色取代。一歲半后毛色與成年的白頭葉猴基本無異,但是身形要比成年的白頭葉猴小一半。
為什么白頭葉猴幼崽的毛色是金黃色?有動物學家認為幼年白頭葉猴的金黃色毛發反映了白頭葉猴本來的面目,也就是說有可能白頭葉猴祖先的毛色都是金黃色的,后來遷移到喀斯特石山地區后,金黃色的毛發與環境極不相稱,很容易被天敵發現而喪命。長期進化的過程中,白頭葉猴的毛色逐漸演變成現在的黑白兩色,以便更好地隱藏在喀斯特石山的環境中。不過這種說法目前并未得到充分的科學證明。而在同一片區域里,還存在另一種相近的生物——黑葉猴。黑葉猴幼年時期毛色同樣是金色,形態跟白頭葉猴幼崽非常相似,出生半年后全身毛色變成黑色。所以這很難解釋,同樣生活在喀斯特山區,同樣有躲避天敵的需要,為何黑葉猴選擇了黑色作為成年毛色,白頭葉猴卻選擇了“黑白色”?只能說,每一種生命的存在都有其深刻的內在聯系,大自然中還有很多未知需要我們不斷去探究,即使很難得到確切的結論。
還有一種說法是,白頭葉猴幼崽的金色毛發是為了吸引母親的注意力,激發母愛。這種說法顯得更溫情些。渾身金色毛發的白頭葉猴幼崽的確非常可愛。在目前可見的記錄里,白頭葉猴母猴的“母愛”不乏泛濫之嫌——從出生之日起,母猴就會緊緊地把幼猴摟在懷中,半歲后幼猴能夠獨立生活,自由采食了,但仍然會在母猴的懷里睡覺。
懸崖上的自由王者
在自然界,天生就具備高超嫻熟攀巖技巧的動物非猴類莫屬,而白頭葉猴的攀爬技術尤其令人驚嘆。它們不需要任何輔助或保護措施就能嫻熟地在懸崖邊上下左右移動。從生存的角度來說,為了適應喀斯特石山的環境,白頭葉猴不得不接受大自然的挑戰,掌握好嫻熟的攀巖技巧,讓企圖偷獵它們的天敵望塵莫及。
白頭葉猴具有地面四肢爬行、爬樹、跳躍和攀爬懸崖等四種移動方式,其中攀爬懸崖的移動方式是最困難和最需要技巧的。在懸崖上攀爬時,白頭葉猴一般沿著粗藤下方的裂縫手足并用地慢慢爬行,只要有凸出的可以抓握或踩踏的巖石,它們就能巧妙地加以利用。白頭葉猴總是果斷穩健、一蹦一跳地往上攀爬。如果雙足實在沒有踩踏的地方,就用兩只手輪換著往前攀爬。不難設想它們的前肢是多么的有力。
對于帶著幼猴的母猴來說,每天攀爬懸崖更是艱難。一旦遇到懸崖峭壁,母猴會立即把幼猴抱在懷中。當然,母猴一有機會便會鍛煉幼猴,在一些容易攀爬的路徑上,母猴會把幼猴放下來讓它們嘗試攀爬,盡管幼猴不斷地發出叫聲,向母猴求救,母猴們仍然會很堅定地拒絕幼猴,直到它們能夠勇敢地邁出步子。
丈量人類文明的一把尺子
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崇左地區還留存著狩獵的傳統,白頭葉猴遭到經常性的獵殺。同時,隨著人類活動范圍擴大,更多的山地被人們開墾,白頭葉猴的生活領地逐漸萎縮。
原來連成一片的群山被分割開來,山體分裂成了各自獨立的山之孤島,白頭葉猴只能生活在相對狹小獨立的山體之中,失去了遷移的能力,種群逐漸減少。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這些曾經呼嘯山林的龐大種群只存活200多只。
20世紀90年代中期,潘文石教授第一次來到崇左江州區的弄官山谷,見到了白頭葉猴。這位因為對秦嶺的野生大熊貓進行長達17年的研究而被譽為“熊貓之父”的生物學家敏銳地意識到白頭葉猴的生物價值。從此,他和白頭葉猴結下不解之緣。在長達20年的時光里,他駐扎在崇左這片石山之中,建立起了北京大學崇左生物多樣性研究基地,對白頭葉猴進行專門研究和保護。正是潘文石教授的不懈努力,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白頭葉猴的意義和價值,更多的人投身到對白頭葉猴的保護之中,建立起了白頭葉猴自然保護區。保護區周邊的村民們也放下獵槍,退出部分耕地,學會使用沼氣、燃氣等環保能源,這片曾經被蠶食的喀斯特山區重新煥發生機。白頭葉猴們終于可以結束東躲西藏的命運,再次回到面向村莊的寬闊巖洞上安居,可以放心登上山頂的樹叢,一邊嬉戲一邊眺望人間的裊裊煙火。
“研究告訴我們,所有被認為是瀕臨滅絕的動物,絕大多數都是年輕健康的個體。只要給它們足夠的時間和棲息地,它們就能生存并繁衍下去。”潘文石教授如是說。
越來越多的人慕名前來一睹白頭葉猴的風采,為之癡迷的不乏其人。其中一位是東北人尤杰,他不遠萬里從中國最北端來到中國西南邊境這片山區中,一待就是數個年頭。他以山洞為家,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觀猴。他拍下大量的猴群視頻和照片,他的志向是要拍出最精彩的白頭葉猴紀錄片。另一位“猴癡”是紀錄片導演顧鐵流,他放棄了待遇優厚的工作,來到保護區當起了全職志愿者,一干就是10年,每天背著七八十斤重的攝影儀器進山,目的是要拍下一只白頭葉猴從出生到衰老、死亡的過程。
那么多人甘愿為了白頭葉猴投入一生的精力,因為他們深諳其中的意義:白頭葉猴其實是人類的一面鏡子,它見證了人類的過去,映照著人類的現實處境,還昭示著人類的未來。如何對待和我們在同一個星球上生活的白頭葉猴,其實是丈量人類文明程度的一把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