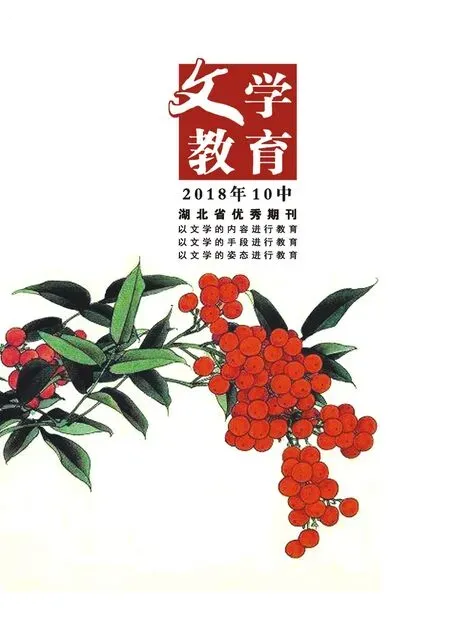胡瑗姓名淺考:基于瑗、璦、璦三字的訓詁分析
雷 鵬
一.“胡璦”的誤用
百度是當今使用最多、最大眾化的搜索引擎之一。筆者搜索關鍵詞“胡瑗”后,出現詞條數約為459000個。搜索“胡璦”,出現詞條數約為46500個。仔細分析這些詞條,兩個關鍵詞所搜索出的資料都是關于同一人的。而搜索“胡瑗”的詞條數要遠多于“胡璦”。同時,筆者還注意到,“互動百科”中還出現了“胡璦-胡瑗”的帶有“退讓性”與模糊性說法,堂堂一個古代名家,居然有兩個不一樣的名字,且讀音相差甚遠,豈不怪哉?這就說明:一方面,百度詞條的編輯者沒有做細致入微的甄別和考證;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學術界,可能依然缺乏對于“胡瑗”和“胡璦”姓名的考辨與確認。然而百度畢竟是一個大眾性的搜索引擎,所提供的闡釋說明并不能完全作為學術上的依據。
不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國知網上的一些學術性論文居然也出現了將“胡瑗”訛誤為“胡璦”的錯誤,而且這樣的錯誤還不是個別現象。近十年來,約有五十多篇出現該錯誤的文章被陸續發表。[1]在此例舉一二,如孫小迪《易學圖象思維中樂律闡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中的樂律思想探析》[2]、蔣澤標《實踐教學視角中胡璦教育思想》[3]。這就不止是一件令人發笑的事情了,更應該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學術問題。從論文撰寫的角度出發,不難猜想當今許多學者或許會隨意地借鑒已有的論文及研究,又或是輕易地借鑒百度等搜索引擎所檢索出的資料,對內容不加辨別,甚至把核心人物的名字都弄錯。這是值得我們去反思的。這種錯誤如繼續發展下去,勢必將嚴重影響知識的傳承。若是論文中連一代名家的姓名都沒有寫對,又何談其后的學術介紹呢?
二.“瑗”“璦”“璦”的訓詁考辨——形、音、義
胡瑗(993~1059),字翼之,中國北宋理學先驅、思想家和教育家。因世居陜西路安定堡,世稱“安定先生”,又與孫復、石介并稱為“宋初三先生”。其名目前存在兩種說法:一作“胡瑗”,另作“胡璦”。經考證,“胡璦”一說為誤。
讀者可查閱大量相關的古籍資料,絕大部分古籍資料中必當以“胡瑗”為準,而本文僅就“瑗”“璦”“璦”三字,進行訓詁學上的考辯分析。
從字形出發,“瑗”字在《說文·玉部》載:“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陛以相引。從玉,爰聲”[4]。“瑗”字是一個形聲字,“玉”表意,其形像一串三塊玉,表示“大孔玉璧”;“爰”表聲,具有“引”義,說明“瑗”是古代帝王升陛下陛時,侍臣用以相引之璧。至于“璦”和“璦”二字,“璦”當為“璦”的簡體字,目前尚無確切的字形來源資料。當屬形聲造字。兩字在字形上,與“瑗”十分接近。同時,筆者又查找了“愛”的異體字,發現存在與“爰”十分接近的字形。據明代郭一經著《字學三正》(體制上·時俗杜撰字)[5]載,“愛”俗作。字形已和“爰”字十分相近。筆者認為存在后世在使用時,因字形相近而抄錯的可能性。
從字音角度出發,“瑗”字從各種聲韻系統看,自上古到中古,直到現代,其發音變化并不大[6]。反切注音基本上都作“于愿切”,又“王眷切”[7]。在現在漢語拼音中,作:“yuan”第四聲,與古音相近。至于“璦”和“璦”二字,“璦”字從古至今發音變化也不大[8]。反切注音基本都作“烏代切”。在現在漢語拼音中,作:“ai”第四聲。亦與古音相近。[9]因此,就字音的歷史演變來說,三者皆保持著較為穩定的字音,且相差較大。
從字義角度出發,“瑗”字在眾多字典中,都解釋為“孔大邊小的璧”,或“玉名”[10]。至于“璦”和“璦”二字,在眾多字典中,“璦”與“璦”為繁簡字關系,“璦”本義為美玉。而“璦”的除了有美玉的意思之外,還用于地名“璦琿”(亦作愛輝)[11]。所以,三者都作“玉”講,無非是“璦”、“璦”泛指美玉,而“瑗”特指“大孔璧”。而且,三者若用于人名之中,當作“玉”講,這一點似乎是很符合情理的。
基于以上三個角度的訓詁分析,古人名與字的關聯性,也是我們不可避免要考慮的一方面。對于姓名的考證不應該僅僅局限于原字,更應看到古人的名和字之間的關聯性。關于名與字之間的聯系,清代學者曾把它歸納為“五體”(同訓、對文、連貫、指實、辨物)、“六例”(通作、辯訛、合聲、轉語、發聲、并稱)。[12]運用這種理論來審視“胡瑗”的名與字,就可以發現其相關聯性。胡瑗,字翼之。前文已經從字形的角度分析過“瑗”是古代帝王升陛、下陛時,侍臣用以相引之璧,且為環狀。“翼之”一詞,見于《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翼之”為匡扶幫助之意,這其實是暗合“瑗”的本義“相引之璧”的。很明顯,這一點是“璦”與“璦”所不具備的。故而從古人姓名訓詁的角度來說,這也是有利的支撐證據,宋儒的姓名當作“胡瑗”,而且名與字的關系當屬意義相同相近類和詩文典故類[13],即前文所說“五體”中的“同訓”類。從古人名和字的關聯性這一角度,的討論其實也就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大儒“胡瑗”的名字由來,具有可靠性。
通過一系列比較,三者在“字形”上,相差不大,只有微小的差別,唯獨在“字音”上相差深遠。而字音上的差別,這和著同屬“象形字”的構字法有關。“瑗”其聲旁為“爰”,讀作:yuán,與“瑗”(yuàn)相近。“璦”、“璦”二字,其聲旁為“愛”、“愛”,皆讀作:ài,與原字同音。
三.訛誤之因及反思
上文中提到這三個字在使用上的訛誤,筆者認為,這與這三個字的“字形”有很大的關系。
從字形上,我們能夠很明顯地看出,這三個字是十分相近的,尤其是“瑗”字的印刷體“”,若在字體較小的書籍中,稍不留心就會看成“璦”字。
合理的猜想應該是建國以后簡體字的大量使用,“璦”簡化成了“璦”,自然就會出現想當然地將“瑗”字訛誤為“璦”,兩者又同樣都屬于形聲字的造字法,字讀半邊也就是自然出現了訛誤。
另外,我們要認識到“在網絡信息化時代,人們大都用鍵盤敲漢字,失去很多手寫漢字的機會,造成漢字的認知識別和書寫運用能力越來越弱”[14]。故而電子科技發達的今天,人們在做科學研究時大量地引用各種資料,且不注意這兩個字的區分,進一步導致了其“瘤毒”在電子版本的資料中擴散開來。
同時,人們也沒有完全注意到并重視這個問題,學術界也并無著重強調這個錯誤,導致即使是用錯了也全然不知情。就如說上文所舉的一些論文的例子,在這些文章發表之前,文章作者以及其指導老師都沒有看出來,期刊的責任編輯也沒有察覺到,發表后,也沒有過多的人正式地指正出來,所以導致問題一直留在那里。就連百度也采取“退讓性”的通融,將兩個字“混為一談”,讓人們造成了誤解,強化了毒瘤的傳播。
這里我們就不由得想起了大學里的學術精神,陳寅恪先生在《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中寫道:“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當代也有學者提出了“誠篤的精神”,“獨立的精神”,“超越的精神”。[15]與陳先生的觀點不謀而合。“余雖不敏,然余誠也”,誠是做學問的第一要義,也是為人的要義,著實發人深省。
最后,希望這篇尚不成熟的文章能夠給部分讀者以啟發,不光是希望大家能夠認清一代宋儒胡瑗其姓名究竟為何,更重要的是希望學者在做學術研究時,能夠做到足夠的負責與細密,真正發揚學術研究精神。
一字之差,足夠令人深思啊!
注 釋
[1] 中國知網.http://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2018-3-11.
[2]孫小迪.易學圖象思維中樂律闡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中的樂律思想探析.[J].當代音樂,2016,20:1.
[3]蔣澤標.實踐教學視角中胡璦教育思想.[J].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雙月刊),2013,4:60.
[4]《說文解字》大徐本·宋本·第28頁.
[5]《字學三正》(體制上·時俗杜撰字)[明]郭一經著.清抄本.第60頁.
[6]董同龢系統(上古音、中古音)、周法高系統(上古音、中古音)、李方桂系統(上古音、中古音)、王力系統(中古音)、高本漢(中古音)等.
[7]《廣韻》、《集韻》、《中州》、《洪武》等.
[8]王力系統(上古音、中古音)、董同龢系統(中古音)、周法高系統(中古音)、李方桂系統(中古音).
[9]《廣韻》、《集韻》.
[10]《漢語大字典》第1207頁、《漢語大詞典》第5677-5678頁、《現代漢語詞典》第1605頁.
[11]《漢語大字典》第1222頁、《漢語大詞典》第5710頁、《現代漢語詞典》第6頁.
[12]暴希明.論古人名字的關系及其文化信息價值.[J].中州學刊,2008,5:277.
[13]賴榮生.古人的名與字.[J].閱讀與寫作,1995,12:24.
[14]楊倩.信息化時代漢字錯別字調查分析.[J].語文教學與研究,2015,104:31.
[15]朱萬悅.學術論文如何體現學術精神.[J].文教資料,2011,10(下):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