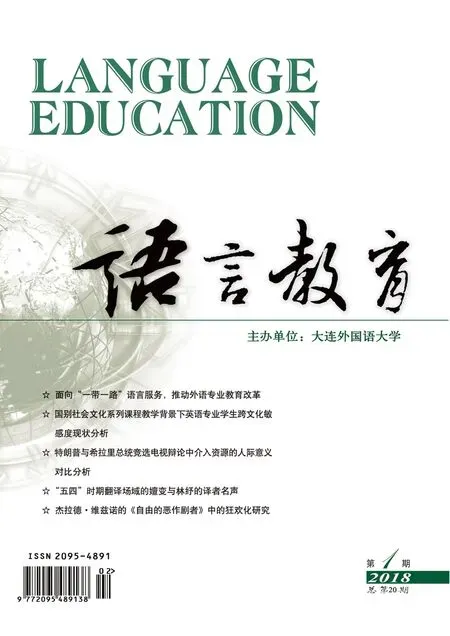“五四”時(shí)期翻譯場(chǎng)域的嬗變與林紓的譯者名聲
廖 濤
(電子科技大學(xué)中山學(xué)院,廣東中山)
1.引言
林紓是近代中國(guó)譯介西洋文學(xué)的先驅(qū),卻成為“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眾矢之的。他的譯者名聲在“五四”時(shí)期發(fā)生逆轉(zhuǎn)。不少論者認(rèn)為林紓的后期譯作較之前期遜色的原因是其個(gè)人思想退化。林紓生活在一個(gè)劇變的時(shí)代,新舊思潮在“五四”時(shí)期激烈交鋒。“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對(duì)中國(guó)思想界和文學(xué)界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當(dāng)時(shí)的翻譯場(chǎng)域亦隨之嬗變。林紓作為翻譯活動(dòng)的實(shí)踐者,同樣受到場(chǎng)域力量的影響。本文擬從翻譯場(chǎng)域的角度分析林紓在“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前后譯者名聲變化的原因。
2.翻譯場(chǎng)域
“場(chǎng)域”(field)是布迪厄(Bourdieu)社會(huì)學(xué)的核心術(shù)語(yǔ)之一,指的是“擁有相對(duì)獨(dú)立運(yùn)作規(guī)則的社會(huì)空間”(Bourdieu, 1993: 162)。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越來(lái)越多的翻譯研究者借鑒布迪厄的社會(huì)學(xué)理論來(lái)研究翻譯問(wèn)題。場(chǎng)域并非可觸及的實(shí)體,而是用來(lái)描述和解釋社會(huì)關(guān)系的一個(gè)概念。人具有社會(huì)屬性,在社會(huì)中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影響人的行為和思想,人也反過(guò)來(lái)影響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形成和發(fā)展。布迪厄認(rèn)為階級(jí)背景、環(huán)境、語(yǔ)境對(duì)于個(gè)體的影響從來(lái)不是直接的,這種影響總是以場(chǎng)域結(jié)構(gòu)為中介(斯沃茨,2006: 138)。任何場(chǎng)域都是相對(duì)獨(dú)立的關(guān)系系統(tǒng),與周邊場(chǎng)域相互滲透。所以,我們要考察翻譯場(chǎng)域之中的規(guī)則,就需要觀察它與周邊相關(guān)場(chǎng)域的關(guān)系和互動(dòng)(王悅晨,2011: 9)。場(chǎng)域是行動(dòng)者爭(zhēng)奪有價(jià)值的支配性資源的空間場(chǎng)所。譯者在翻譯場(chǎng)域中所占位置的高低取決于其占有的資本(capital)。翻譯場(chǎng)域與權(quán)力場(chǎng)域及文學(xué)場(chǎng)域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權(quán)力場(chǎng)域和文學(xué)場(chǎng)域中力量格局的變化會(huì)導(dǎo)致翻譯場(chǎng)域規(guī)則的變化。場(chǎng)域概念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gè)社會(huì)學(xué)的視角,有助于我們深刻解讀與翻譯活動(dòng)相關(guān)的種種關(guān)系和規(guī)則。
3.林紓在“五四”前翻譯場(chǎng)域中的位置
林紓是我國(guó)文學(xué)翻譯史上一位不審西文,卻享有盛譽(yù)的西方文學(xué)翻譯家。他以合作翻譯的方式走向了文學(xué)翻譯之路。“林譯小說(shuō)”已成為中國(guó)翻譯文學(xué)史上的一個(gè)專有名詞。該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有著深刻的社會(huì)文化背景。林紓在翻譯場(chǎng)域中的位置取決于其占有的文化資本。資本與場(chǎng)域是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資本的價(jià)值取決于它所處的場(chǎng)域,場(chǎng)域也離不開(kāi)資本,場(chǎng)域只是一種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如果沒(méi)有資本,空洞的結(jié)構(gòu)也是沒(méi)有意義的(宮留記,2009: 105)。
3.1 林紓的文化資本
布迪厄的資本概念來(lái)源于馬克思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他對(duì)馬克思及韋伯的資本理論進(jìn)一步改造后,把資本的表現(xiàn)形式分為四種基本類型,即經(jīng)濟(jì)資本、文化資本、社會(huì)資本和象征資本。不同的資本類型之間存在可轉(zhuǎn)換性。行動(dòng)者在特定場(chǎng)域中所處的位置是由其在該場(chǎng)域中擁有的資本決定的。翻譯場(chǎng)域和文學(xué)場(chǎng)域相互交融。在林紓生活的時(shí)代,大部分讀者不能直接閱讀原作,譯作往往被當(dāng)成原作來(lái)閱讀。林紓不諳外文,其作為譯者的象征資本主要從文學(xué)場(chǎng)域轉(zhuǎn)化而來(lái)。
文化資本包括非正式的人際交往技巧、習(xí)慣、態(tài)度、語(yǔ)言風(fēng)格、教育素質(zhì)、品味與生活方式(特納,2001: 192)。林紓的文化資本是其在所處的社會(huì)文化制度中被認(rèn)可的文化能力,特別是語(yǔ)言能力。林紓出身寒門(mén),要博取功名,唯有走科舉應(yīng)試之路。1882年,林紓中舉。舉人頭銜讓他獲得了制度化文化資本。制度化文化資本是指在學(xué)術(shù)上得到國(guó)家合法保障的、認(rèn)可的文化資本,它表現(xiàn)為行動(dòng)者擁有的學(xué)術(shù)頭銜和學(xué)術(shù)資格(宮留記,2009: 127)。這種頭銜讓他結(jié)交到更高層次的人士,更多地參與文學(xué)活動(dòng),從而擴(kuò)大了影響力,獲得了更多的文化資本。
林紓中舉后曾六次參加禮部試,均告落第,從此不再圖仕進(jìn)。放棄科舉之后,他篤學(xué)古文、研治宋學(xué),終成晚清古文殿軍。他的古文能力獲得桐城派清末領(lǐng)軍人物吳汝綸的贊賞。桐城派以“以古文為時(shí)文”,在清末文壇占統(tǒng)治地位。吳汝綸稱贊林紓的古文,“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林紓,1927: 25)。布迪厄認(rèn)為任何一個(gè)社會(huì)場(chǎng)域都有隸屬于自己的正統(tǒng)文化。它是區(qū)分場(chǎng)域內(nèi)各行動(dòng)者處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則。位置指的就是行動(dòng)者在場(chǎng)域中根據(jù)握有的資本數(shù)量和結(jié)構(gòu)的差別被分配的地位(宮留記,2009:52)。林紓卓爾不群的古文表達(dá)能力便是一種正統(tǒng)文化,這使其在晚清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中處于有利位置。
3.2 開(kāi)文學(xué)維新風(fēng)氣之先的翻譯家
“林譯小說(shuō)”開(kāi)文學(xué)界維新風(fēng)氣之先。維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為曾賦詩(shī)“譯才并世數(shù)嚴(yán)林,百部虞初救世心”(馬祖毅,1998: 424) 。從中我們可以窺見(jiàn)林紓反帝救國(guó)的翻譯動(dòng)機(jī)。這一點(diǎn)與維新派變革維新,救亡圖存的政治主張是一致的。
1894年甲午戰(zhàn)爭(zhēng)戰(zhàn)敗后,中國(guó)陷入了嚴(yán)重的民族危機(jī)。1895年康有為率梁?jiǎn)⒊葦?shù)千名舉人發(fā)起了“公車上書(shū)”,在社會(huì)上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維新思潮迅速傳播開(kāi)來(lái),進(jìn)而發(fā)展為愛(ài)國(guó)救亡的政治運(yùn)動(dòng),影響了晚清政壇。在進(jìn)行政治改良運(yùn)動(dòng)的同時(shí),維新派也發(fā)起了文學(xué)改良運(yùn)動(dòng),先后提出了“詩(shī)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shuō)界革命”的口號(hào)。其中,“小說(shuō)界革命”的影響最為深遠(yuǎn)。而譯介西方小說(shuō)又是“小說(shuō)界革命”的重中之重。1897年嚴(yán)復(fù)和夏曾佑在《國(guó)文報(bào)》發(fā)表《本館付印說(shuō)部緣起》,力倡譯介歐美小說(shuō)以開(kāi)啟民智。梁?jiǎn)⒊鲝垺疤夭赏鈬?guó)名儒所撰述,而有關(guān)切于中國(guó)時(shí)局者,次地譯之(張俊才,2007: 60)。”
梁?jiǎn)⒊紫仁俏徽渭遥浯尾攀俏膶W(xué)家。他的文學(xué)活動(dòng)直接為其政治目的服務(wù)。維新派對(duì)晚清權(quán)力場(chǎng)域的影響力在1898年“戊戌變法”時(shí)達(dá)到頂峰。布迪厄把場(chǎng)域所處的社會(huì)空間稱為“權(quán)力場(chǎng)域”(field of power),指的是在社會(huì)中具有分配資本和決定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能力的結(jié)構(gòu)空間(Bourdieu, 1993: 37-40)。權(quán)力場(chǎng)域是所有場(chǎng)域中最重要的一種,發(fā)揮著類似于“原場(chǎng)域”(metafield) 的功能,在所有場(chǎng)域中起分化與斗爭(zhēng)的組織原則的作用 (Bourdieu, 1992: 111-112)。文學(xué)場(chǎng)域在權(quán)力場(chǎng)域中屬于被支配的地位(Bourdieu,1993: 37-40)。維新派憑借在權(quán)力場(chǎng)域的影響力,獲得了文學(xué)場(chǎng)域中的話語(yǔ)權(quán),構(gòu)建了當(dāng)時(shí)文學(xué)及翻譯場(chǎng)域的主要規(guī)則。林紓積極響應(yīng)當(dāng)時(shí)的維新潮流,在詩(shī)集《閩中新樂(lè)府》中表達(dá)了反帝愛(ài)國(guó)、變法圖強(qiáng)和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思想。1900年,他在上海《譯林》雜志的創(chuàng)刊號(hào)序言中寫(xiě)道:“謂欲開(kāi)民智,必立學(xué)堂;學(xué)堂功緩,不如立會(huì)演說(shuō);演說(shuō)又不易舉,終止唯有譯書(shū)”(王宏志,2007: 92)。
林紓進(jìn)入譯界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王壽昌、魏易等合作譯者看中的是林紓具有的而他們所欠缺的翻譯場(chǎng)域中的象征資本——良好的古文功底和文學(xué)界的影響力。王壽昌邀請(qǐng)林紓共譯《巴黎茶花女遺事》時(shí)對(duì)他說(shuō):“吾請(qǐng)與子譯一書(shū),子可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于中國(guó),不勝于蹙額對(duì)坐耶?”(楊蔭深,1939: 486)于是,《巴黎茶花女遺事》就通過(guò)這種獨(dú)特的翻譯方式在中國(guó)面世了。該譯本行世后即引起轟動(dòng),“一時(shí)紙貴洛陽(yáng),風(fēng)行海內(nèi)”,“不脛走萬(wàn)本”(郭延禮,2005: 211)。文學(xué)界名流對(duì)該譯本的贊嘆不可勝數(shù)。嚴(yán)復(fù)作了“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的高度評(píng)價(jià)(陳平原,1989:28)。鄒振環(huán)把《巴黎茶花女遺事》列為影響近代中國(guó)的一百種譯作之一,認(rèn)為它是對(duì)中國(guó)士人產(chǎn)生影響的第一部西方小說(shuō),其意義不僅僅在于開(kāi)創(chuàng)了一代翻譯西方文學(xué)作品的風(fēng)氣,還在于這部小說(shuō)的譯刊,從一定意義上使清末士人的觀念發(fā)生了重要的轉(zhuǎn)變(鄒振環(huán),1996: 122)。首部譯作的成功奠定了林紓在譯界的地位,為他在翻譯場(chǎng)域積累了文化資本。從此,林紓在譯壇耕耘了二十多年,共譯書(shū)179種,涉及11個(gè)國(guó)家的98位作者,被公認(rèn)為中國(guó)新文學(xué)的開(kāi)山祖師及譯壇泰斗(張俊才,2007: 77)。
“林譯小說(shuō)”引發(fā)了國(guó)人對(duì)西方文學(xué)的興趣,不僅引入了新的文學(xué)觀念,還傳播了西方資產(chǎn)階級(jí)自由、民主的思想,在促進(jìn)中國(guó)社會(huì)向西方學(xué)習(xí)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代表人物胡適晚年談到他在1915年寫(xiě)的《康南耳君傳》時(shí)說(shuō)道:“我那時(shí)還寫(xiě)古文……那時(shí)敘事文受到了林琴南的影響。林琴南的翻譯小說(shuō)我總看了上百部”(胡頌平,1993: 280)。周作人稱晚清譯界代表人物嚴(yán)復(fù)、林紓、梁?jiǎn)⒊酥校钕矚g的是林譯小說(shuō),甚至還曾經(jīng)模仿過(guò)他的譯文(陳平原,1989: 177)。他在翻譯集《點(diǎn)滴》的譯序中寫(xiě)道:“我從前翻譯小說(shuō),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響”(鄭振鐸,1935: 1228)。錢(qián)鐘書(shū)坦言自己就是讀了林紓的翻譯而增加學(xué)習(xí)外國(guó)語(yǔ)學(xué)的興趣,《林譯小說(shuō)叢書(shū)》帶他進(jìn)入了一個(gè)在《水滸》、《西游記》、《聊齋志異》以外另辟的新世界(錢(qián)鐘書(shū),1981: 22)。
林紓的翻譯推動(dòng)了中國(guó)文學(xué)的革新,孕育了新文學(xué)的胚芽,為“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奠定了文學(xué)基礎(chǔ)。受新文學(xué)形式的影響,文學(xué)場(chǎng)域和翻譯場(chǎng)域的規(guī)則也隨之發(fā)生變化。這一點(diǎn)是林紓始料未及的。
4.“五四”后的翻譯場(chǎng)域與林紓的譯者名聲
場(chǎng)域是相對(duì)獨(dú)立的社會(huì)空間,完全自主和孤立的場(chǎng)域是不存在的。權(quán)力場(chǎng)域和文學(xué)場(chǎng)域?qū)Ψg場(chǎng)域有著不可忽視的制約作用。辛亥革命后的幾年,中國(guó)思想界新舊思潮交織糾纏,一度處于混亂的狀態(tài)。雖然封建帝制被推翻,但在思想領(lǐng)域內(nèi)占統(tǒng)治地位的仍舊是封建思想。“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是政治革命在思想界的延續(xù)。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改變了權(quán)力場(chǎng)域和文學(xué)場(chǎng)域中的力量格局。受制于權(quán)力場(chǎng)域和文學(xué)場(chǎng)域的翻譯場(chǎng)域亦隨之變化。林紓在“五四”前翻譯場(chǎng)域中擁有的文化資本逐漸衰落。
4.1 “五四”時(shí)期翻譯場(chǎng)域的嬗變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中國(guó)建立了現(xiàn)代的政治體制,但國(guó)民的思想觀念卻與之相去甚遠(yuǎn),思想文化領(lǐng)域的反封建任務(wù)尚未完成。軍閥勢(shì)力繼續(xù)利用封建思想禁錮人的頭腦,維護(hù)自己的統(tǒng)治。袁世凱極力推行尊孔復(fù)古,為帝制復(fù)辟運(yùn)動(dòng)提供思想文化支持。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在這種形勢(shì)下應(yīng)運(yùn)而生,因而,一開(kāi)始便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新文化人高舉“科學(xué)”和“民主”兩面旗幟,弘揚(yáng)與傳播新思想、新觀念,猛烈抨擊封建禮教,對(duì)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教育等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
1915年創(chuàng)刊的《新青年》是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策源地。《新青年》以思想啟蒙為辦刊方向,創(chuàng)刊之初并沒(méi)有引起多大反響。1917年初,胡適和陳獨(dú)秀分別在《新青年》發(fā)表了《文學(xué)改良芻議》和《文學(xué)革命論》,引發(fā)了舊文化派和新文化派的論戰(zhàn),拉開(kāi)了文學(xué)革命的序幕。新文化派提倡新文學(xué),反對(duì)舊文學(xué),提倡白話文,反對(duì)文言文。在中國(guó)幾千年的封建社會(huì)中,文言文一直是士大夫階級(jí)的專利品,是一種文化資本。士大夫階級(jí)憑借這一資本壟斷了知識(shí)場(chǎng)域和文學(xué)場(chǎng)域。文言文和白話文之間存在意識(shí)形態(tài)的沖突。白話文運(yùn)動(dòng)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貴族的文學(xué),發(fā)展大眾的文學(xué),為思想啟蒙運(yùn)動(dòng)鋪路。陳獨(dú)秀在《文學(xué)革命論》中提出“三大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xué),建設(shè)平易的抒情的國(guó)民文學(xué);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xué),建設(shè)新鮮的立誠(chéng)的寫(xiě)實(shí)文學(xué);推倒遷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xué),建設(shè)明了的通俗的社會(huì)文學(xué)”(陳獨(dú)秀,1987: 95)。新文化派對(duì)舊文學(xué)展開(kāi)了顛覆式的批判。這一現(xiàn)象印證了場(chǎng)域中的斗爭(zhēng)占位規(guī)則。在特定場(chǎng)域中掌握更多資本,處于支配地位的行動(dòng)者傾向于采取保守性策略來(lái)維護(hù)場(chǎng)域中的力量格局;而掌握較少資本的行動(dòng)者則傾向于采取異端的顛覆策略來(lái)打破現(xiàn)有的力量格局(布迪厄,1997: 147)。白話文運(yùn)動(dòng)是五四文學(xu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推行白話文,科學(xué)知識(shí)和民主思想就不能普及到普羅大眾,思想啟蒙運(yùn)動(dòng)也就無(wú)法展開(kāi)。經(jīng)過(guò)激烈的“斗爭(zhēng)”,新文化派最終獲得“五四”時(shí)期的話語(yǔ)權(quán)。“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使白話文成為通行國(guó)語(yǔ),確立了白話文學(xué)的正宗地位,推動(dòng)了中國(guó)文化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且動(dòng)搖了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思想和文化基礎(chǔ)。
傳統(tǒng)文學(xué)的典范以文言文為正統(tǒng)語(yǔ)言,要選取古人的白話文作品作為新文學(xué)的典范并非易事。胡適斷言“中國(guó)文學(xué)的方法實(shí)在不完備,不夠作我們的模范”,認(rèn)為創(chuàng)造新文學(xué)唯一的法子“就是趕緊多多地翻譯西洋的文學(xué)名著做我們的模范”(胡適,1998: 56)。因此,他和陳獨(dú)秀等人在文學(xué)革命之初提出了以翻譯為文學(xué)革命先導(dǎo)的主張,希冀通過(guò)文學(xué)翻譯輸入西方文學(xué)的價(jià)值標(biāo)準(zhǔn)、體裁、文學(xué)思潮、創(chuàng)作技巧等等。在這一方針的指導(dǎo)下,翻譯作品在《新青年》上占了相當(dāng)大的比例。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成立最早的文學(xué)團(tuán)體文學(xué)研究會(huì)便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xué)、整理中國(guó)舊文學(xué)、創(chuàng)造新文學(xué)”為宗旨。文學(xué)翻譯在文學(xué)革命中的地位得到進(jìn)一步認(rèn)可。新文化派提出的用白話文創(chuàng)作、只譯名家名著、用白話文翻譯、以及“直譯”等主張成為“五四”時(shí)期中國(guó)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文學(xué)翻譯的主流規(guī)范,晚清以來(lái)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和翻譯場(chǎng)域的格局得以轉(zhuǎn)變。
4.2 林紓文化資本的喪失與譯界地位的沒(méi)落
林紓在“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中遭到新文化派的口誅筆伐,成為眾矢之的。新文化人痛批林紓使用文言翻譯、漏譯誤譯、隨意改寫(xiě)和刪減原作、選擇不入流的原作等問(wèn)題。1918年,劉半農(nóng)在《新青年》上發(fā)文批評(píng)林紓的翻譯“謬誤太多,把譯本和原本對(duì)照,刪的刪,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 (陳福康,1992: 209) 。1919年4月,傅斯年在發(fā)表于《新潮》上的《譯書(shū)感言》一文中批評(píng)林紓:“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調(diào)”(陳福康,1992: 217) 。梁?jiǎn)⒊u(píng)論林紓的翻譯說(shuō):“有林紓者,譯小說(shuō)數(shù)百余種,頗風(fēng)行于時(shí),然所譯本,率皆歐洲第二三流作者。紓治桐城派古文,每譯一書(shū),輒“因文見(jiàn)道”,於新思想無(wú)與焉”(梁?jiǎn)⒊?989: 72)。
林紓的翻譯在“五四”時(shí)期遭人唾棄固然與其循常習(xí)故的文化立場(chǎng)相關(guān)。倘若我們把這一現(xiàn)象放到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場(chǎng)域中審視,可以發(fā)現(xiàn)林紓和新文化派之間的爭(zhēng)斗,實(shí)質(zhì)是對(duì)當(dāng)時(shí)文學(xué)場(chǎng)域中話語(yǔ)權(quán)的爭(zhēng)奪。單就翻譯問(wèn)題而言,林紓按理不應(yīng)被新文化派如此痛恨。至于林譯小說(shuō)中出現(xiàn)的誤譯,林紓在1913年的《荒唐言》的《跋》中寫(xiě)道:“紓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所口述而譯,此海內(nèi)所知。至于謬誤之處,咸糾粗心浮意,信筆行之,咎均在己,與朋友無(wú)涉也 ”(錢(qián)鐘書(shū),1981: 30)。林紓的口授譯者校核不嚴(yán),對(duì)誤譯問(wèn)題也難辭其咎。意譯是晚清的翻譯風(fēng)尚,不少譯者在改寫(xiě)原作方面和林紓相比有過(guò)之而無(wú)不及,“尤其是所謂上海的翻譯家;他們翻譯一部作品,連作者的姓名都不注出,有時(shí)且任意改換原文中的人名地名,而變?yōu)樗麄兯灾模挥械娜穗m然知道注明作者,然其刪改原文之處,實(shí)較林先生大膽萬(wàn)倍”(錢(qián)鐘書(shū),1981: 19)。林紓使用的古文體有別于桐城古文,介乎嚴(yán)復(fù)和梁?jiǎn)⒊咧g,不太古奧,也不太通俗,不太新也不太舊,大體可以用“平正簡(jiǎn)潔”四字概括(陳平原,1989: 177)。在白話文運(yùn)動(dòng)開(kāi)始之前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新青年》刊載的譯文還是以文言文為主。晚清翻譯的刪節(jié)改寫(xiě),在初期《青年雜志》以至《新青年》仍有遺留(趙稀方,2013: 39)。1915年的《青年雜志》上刊登了陳獨(dú)秀用五言古體翻譯的泰戈?duì)栐?shī)《贊美》。新文化派另一領(lǐng)軍人物劉半農(nóng)在《新青年》誕生之前的若干翻譯作品中基本上是用的淺近的文言文,直到1917年后才改為以白話文為主,在翻譯方式上也是從意譯轉(zhuǎn)為直譯(郭延禮,2005: 397)。此外,新文學(xué)派對(duì)林紓原著選擇和林譯小說(shuō)意義的指責(zé)也有夸大之嫌。林紓前期選擇的原作中不乏一些名著,即便是后期,分明也有塞萬(wàn)提斯的《魔俠傳》,有孟德斯鳩的《魚(yú)雁抉微》等書(shū)(錢(qián)鐘書(shū),1981: 38)。
林譯小說(shuō)影響了“五四”時(shí)期的一批作家,促進(jìn)了中國(guó)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的發(fā)生。場(chǎng)域是充斥著斗爭(zhēng)的社會(huì)空間,而斗爭(zhēng)可以改變或者維持場(chǎng)域中的力量格局。在“五四”前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中,林紓的翻譯是反封建的、激進(jìn)的力量。1905年出版的林譯《迦茵小傳》,因未刪去迦茵未婚先孕,并生下私生子的情節(jié),而遭到衛(wèi)道者的攻擊。文學(xué)翻譯為林紓在晚清文學(xué)場(chǎng)域積累了文化資本,提高了個(gè)人影響力,從而使其獲得了正統(tǒng)文化的認(rèn)可。他在1906年被聘為最高學(xué)府京師大學(xué)堂的教員。林紓早年接受的是封建教育,身上留下了傳統(tǒng)文化觀念的烙印,雖然后來(lái)步入維新派的行列,但始終認(rèn)同君主制度。他在文學(xué)場(chǎng)域獲得話語(yǔ)權(quán)后,便從激進(jìn)力量轉(zhuǎn)變?yōu)榫S持場(chǎng)域格局的保守力量。在新文化派推動(dòng)民初文學(xué)場(chǎng)域變革的運(yùn)動(dòng)中,林紓擔(dān)扮演了封建衛(wèi)道士的角色,表示要“拼我殘年,極力衛(wèi)道”(陳平原,1989: 9)。他站在封建正統(tǒng)文化的立場(chǎng),呼吁“力延古文之一線”,譏諷白話文運(yùn)動(dòng)說(shuō)“若盡廢古書(shū),行用土語(yǔ)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yǔ), 按之皆有文法,…… 據(jù)此, 則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鄭振鐸,1935: 6)。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統(tǒng)治,改變了權(quán)力場(chǎng)域格局,受權(quán)力場(chǎng)域支配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和翻譯場(chǎng)域的格局隨之變化。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思想廣泛傳播,林紓?cè)耘f抱住所謂的正統(tǒng)文化不放,站在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對(duì)立面,因而他成為新文化派“文學(xué)革命”的首選對(duì)象。他在譯界的名聲終于隨著其文化資本的喪失而逆轉(zhuǎn)。
5.結(jié)語(yǔ)
在“五四”前的文學(xué)場(chǎng)域和翻譯場(chǎng)域中,林紓出色的古文能力是其博得名聲的文化資本。林譯小說(shuō)傳播了西方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思想,順應(yīng)了當(dāng)時(shí)在權(quán)力場(chǎng)域和文學(xué)場(chǎng)域掌握話語(yǔ)權(quán)的維新派以文學(xué)改良促進(jìn)政治改革的主張,是進(jìn)步和革新的力量,因而獲得了很高的名聲。“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推動(dòng)了文學(xué)場(chǎng)域的變革,使古文失去了正統(tǒng)文學(xué)語(yǔ)言的地位。林紓在翻譯場(chǎng)域中的名聲隨著其文化資本的喪失而沒(méi)落。場(chǎng)域概念為研究林紓翻譯現(xiàn)象提供了一個(gè)新的視角,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地分析社會(huì)空間中與翻譯活動(dòng)相關(guān)的各種力量博弈對(duì)譯者的影響。
[1]Bourdieu, P.& L.Wacquant.1992.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Bourdieu, P.1993.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 on Art and Literature[M].Cambridge: Polity Press.
[3]陳獨(dú)秀.1987.獨(dú)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4]陳福康.1992.中國(guó)譯學(xué)理論史稿[M].上海:上海外語(yǔ)教育出版社.
[5]陳平原.1989.20世紀(jì)中國(guó)小說(shuō)史(第一卷)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6][美]戴維·斯沃茨.2006.陶東風(fēng)譯.文化與權(quán)力:布爾迪厄的社會(huì)學(xué)[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7]宮留記.2009.布迪厄的社會(huì)實(shí)踐理論[M].開(kāi)封: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
[8]郭延禮.2005.中國(guó)近代翻譯文學(xué)概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9]胡適.1998.建設(shè)的文學(xué)革命論 [A].歐陽(yáng)哲生編.胡適文集2·胡適文存[C].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10]胡頌平.1993.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C].北京:中國(guó)友誼出版公司.
[11]梁?jiǎn)⒊?1989.飲冰室合集(專集34)[M].北京:中華書(shū)局.
[12]林紓.1927.畏廬續(xù)集[M].上海:商務(wù)印書(shū)館.
[13]馬祖毅.1998.中國(guó)翻譯簡(jiǎn)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訂版)[M].北京:中國(guó)對(duì)外翻譯出版公司.
[14][法]皮埃爾·布迪厄.1997.包亞明譯.文化資本與社會(huì)煉金術(shù)——布爾迪厄訪談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5]錢(qián)鐘書(shū)等.1981.林紓的翻譯[M].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
[16][美]喬納森·特納.2001.邱澤奇 張茂元等譯.社會(huì)學(xué)理論的結(jié)構(gòu)[M].北京:華夏出版社.
[17]王宏志.2007.重釋“信、達(dá)、雅”——20世紀(jì)中國(guó)翻譯研究[M].北京: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
[18]王悅晨.2011.從社會(huì)學(xué)角度看翻譯現(xiàn)象:布迪厄社會(huì)學(xué)理論關(guān)鍵詞解讀[J].中國(guó)翻譯,(1):5-13.
[19]楊蔭深.1939.中國(guó)文學(xué)家列傳[M].上海:中華書(shū)局.
[20]張俊才.2007.林紓評(píng)傳[M].北京:中華書(shū)局.
[21]趙稀方.2013.新青年的文學(xué)翻譯[J].中國(guó)翻譯, (1):38-44.
[22]鄭振鐸.1935.導(dǎo)言[A].中國(guó)新文學(xué)大系·文學(xué)論爭(zhēng)集[C].上海:上海良友圖書(shū)印刷公司.
[23]鄒振環(huán).1996.影響中國(guó)近代社會(huì)的一百種譯作[M].北京:中國(guó)對(duì)外翻譯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