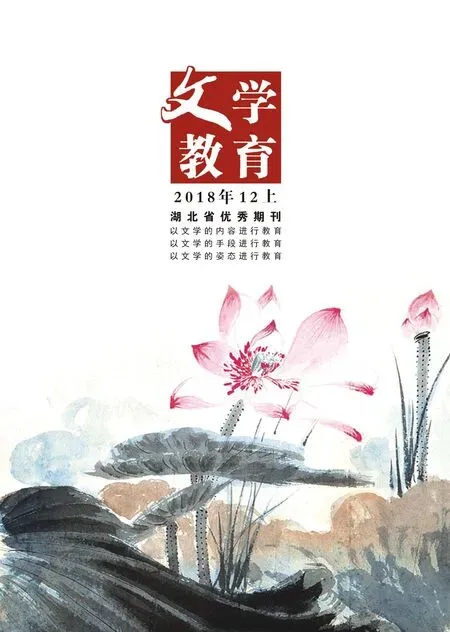被異化的當代生活
——評喬葉的《隨機而動》
曹 霞
喬葉的短篇小說《隨機而動》題目頗有智慧,此處的“機”指的是手機,它作為敘事脈絡完美地融合進了這個成語里,使之不僅成為女主人公格子生活的最好寫照,也勾勒出了當代都市人的內心密室。
在馬克思那里,“異化”指的是作為生產者的“人”與其生產目的、生產過程和生產產物相分割,從而感受到生產這一實踐的非自愿性與非自發性。如果將這一過程與《隨機而動》進行比照,我們就會發現,在當代社會中,“人”的主體性與其生活的本真面目之間,也正在或已經發生嚴重的斷裂。
小說的敘事設置很用心。既然人被手機控制了,那么生活的秩序就不再依賴日常三餐和工作、休息時間,而是根據不時從手機里跳出來的信息而展開的。格子的一天從手機里的鬧鐘開始:“如果不依靠鬧鈴,她一般不會知道早晨長什么樣兒。”這一天,她起床,安排瑣事,看微信公號,去單位開會,佯裝認真開會實則通過手機學齊白石,會后指示快遞小哥放置包裹,同意外賣小哥給好評的要求,接受姐姐發出的玉米地被開發商推平的求助,找到正在曖昧的二婚對象何幫忙,晚上與遠在加拿大的女兒分享微信文章,最后與手機共眠……。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手機,甚至主人公的情感也被手機主宰了。何每天早上發來一朵瘦小的玫瑰,讓已經領悟歲月深淺的格子明白,即使是一朵虛幻的花,有個男人天天堅持送,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愛情離不開手機的虛構,幸福也成為虛構的結果之一。

不得不說,這是一種被嚴重異化的生活,“人”被“物”所指引,所宰制,其主體性不僅遭到分裂和損毀,更因為外部力量的擠壓而發生了變形,最后無聲無息地被褫奪,被吞噬。有意思的是,在“格子”與“格子外”之間存在著一種奇妙的對稱:格子是小說中唯一“可見”的人物,她生活中的其他人都是“不可見”的,包括姐姐、女兒、何。手機猶如鏡像,折射出的他者之存在帶上了虛幻而恍惚的色彩。這種設置實際上也在不斷地強化小說主題。
我以為,作者通過這一敘事設置在表明其態度與立場:既然手機可以決定一切,那么,自我之外的人與生活也都可以隱藏于手機之后。這種生活嚴重地背離了人的主體性。格子的女兒說,手機是讓人使喚的,就叫它“阿奴”吧。實際上,通讀全篇,我們得出的是相反的結論:不是人在使喚手機,而是手機在使喚人。人才是真正的“阿奴”,手機是“阿奴”的主人。從這一層面來看,與其說手機提升了我們的生活,毋寧說它掏空了我們的生活,懸置了我們的精神。就像格子幫助姐姐解決玉米地被推平一事,她找何通過一個自媒體報道了事件,對開發商進行隱晦的批評,親朋好友和網絡閑人紛紛轉發,閱讀量很快飆上了讓人感到“舒服”的5000+。在他們看來,姐姐的事能否真正得到解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數據,數據就是結果,就是“交代”:“何對她有了交代,她對姐姐也有了交代,姐姐更是對全村人都有了交代。因為這個閱讀量,他們都覺得交代得很漂亮。”其中的反諷意味是顯而易見的。對于“手機”帶給當代人的影響及其召喚而來的諸多戲劇性與可能性,作者始終葆有著清醒的反思與警覺。
喬葉的敘事美學即在于此:通過格子的一天,展現出了當代人的一天,也展現出了當代人習焉不察的生活陷阱與精神黑洞。格子看似有滋有味、有情有趣的生活,不過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就連她的名字,也暗合著手機電量的滿“格”狀態。不過,如果我們由“手機”而及“其他”,或許我們會想到,對于當代中國人來說,異化一直存在著,只是在不同的時代,異化物不一樣而已。而作為當代人,什么時候能夠擁有完整的主體性,能夠不假借于他者而完成自我的完善,這確乎是一個需要思考也需要等待的問題。
手機是當代城市生活的產物。喬葉選擇了這一極具典型性的物象來展開敘事,展現當代人“病態”的生活和精神,無疑是敏銳且有難度的。我曾經說過,關于當代生活,作家們雖有所表現,但依然不夠,遠遠不夠,在深度與數量上都處于貧乏狀態,作家們還需要不斷強化寫作的“當代性”。
當然,《隨機而動》也并非完美。當作者以“流水帳”展現生活時,它既是一個便利和易于操作的結構,也帶來了不少的限制和桎梏。小說通篇比較“平”,不起波瀾,缺乏敘事的“引爆點”和“加速器”。如此看來,作者還需要拓展和深化對于當代生活的理解,并將這種理解以審美化的形式植入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