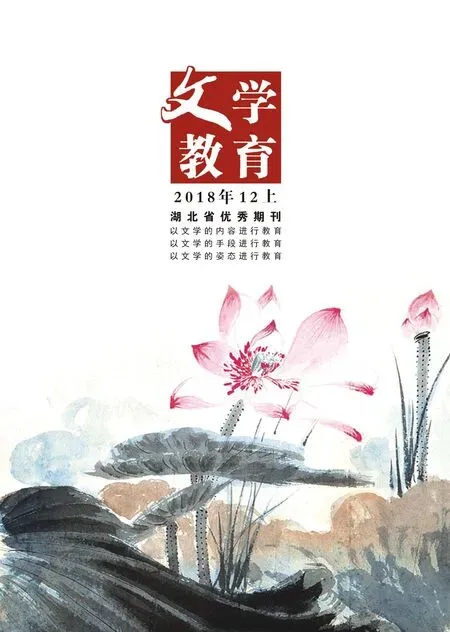每個植物都是一首詩
——評衣水的《醒著的植物》
高維生
當下寫作有關植物的散文多如牛毛,大多模塊式寫作,只是做了一個文字的搬運工,在組合拼接,缺少獨特的風格。在大量的同類體載中,作家衣水的《醒著的植物》,特點鮮明,彰顯自己的個性。
作為一個八〇后的作家,創作過詩歌、劇本和小說,多維寫作構成他的文本。從不同的角度觀察生活,審視人性的美與丑,更重要的是打磨出先鋒的思想。衣水的作品陌生化突現,對于日常的小事情,不會白開水似的記錄,積大堆的文字,壘成垃圾樣的長篇大論的作品。
《醒著的植物》一共寫了三種平常的植物,不是什么名花。它們不是栽在溫室中,依靠園丁的精心護理才能生存。而是長在大地上,頭頂天空,根須深扎泥土中,面臨各種自然變化,頑強的生存。 柳樹適于各種不同的生態環境,在各地都可見到的樹種。但衣水通過自己的觀察發現,與別人不一樣的感受。“一年四季走過潔凈的嘩嘩聲,繁榮興衰都在落花流水里,都鑲在我的皮膚上,都嵌在我的年輪里。一棵柳樹駕馭不了人間的愛與恨,只能明哲保身藏在流水里;一河憂傷讓世人吟詠了多少個世紀,到頭來只有一棵彎腰柳是它的知音。”作家的描寫,絕不是隨意的記錄,按著套路抒情一番,給柳樹拔高,折騰出哲理,變成一篇勵志小文。作家以獨特的視角,寫出對柳的陌生化感覺,就不同于一般寫法。陌生化就是要喚起人們感受事物、感受世界、感受生活,而不是把人變成毫無情感的機械人。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藝術永遠是獨立于生活的,它的顏色從不反映飄揚在城堡上空的旗幟的顏色。”文學不僅模仿外的部生活,它有其自身的內部定律。

隨著時代的變化,導致許多人脫離大自然,他們在快餐文化的浸染下,只能在電腦上游覽寫作,甚至有一批專為各種征文寫作的專業戶。他們沒有價值標準,只是征文的“粉絲”,蒼蠅似的嗅到一點氣味,便撲過去。收集各種征文啟示,在網上搜出當地的圖片,歷史資料,剪輯合成,配幾段蒼白失血性的文字串聯,一篇征文出爐。嗅著電子的風,看著電子的畫面,在寫出帶著電子血緣的人與自然的文字。而非現實的生活,人性的美與丑。
樸素的文字,不可能似一張老照片,隨著時間流逝,漸漸地變得泛黃褪色。經典葆有精神品質,因為時代的劇變,而出現降低的標準,淪為遭淘汰的次品。后現代工業下,人類的精神面臨困窘,喪失自己的家園。人們盲目追求商品的名牌,裝扮自己,眼睛中名牌,思想中名牌,花費大量的錢財,投入到水泥構筑的家中,人失去自我。把流行的文字當作經典來談,通俗的文化作為宗教,每天的新聞碎塊充斥生活。當代的精神危機進入跳樓式的危機中。道德倫理的混亂,價值標準被世俗沖得潰敗。
蓮花作為花中的君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更用來象征理想的人格:“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作家深知這種道理,他沒有循老路子走,在一朵蓮花中,用生命的情感去感受,他選擇“引度”,度化自己的行為。“我清楚,蓮花會緩緩放下重重心事,散開一瓣瓣濕潤的香吻,它在第一縷清香的陽光里,讓我放慢腳步,讓我在干凈的時光里看見自己,引度自己,一身潔白,一生潔凈。”當人的思想潔凈,情感不復雜,潔白了,那么一切的功利,將成為泡影。
人在天空下,去大自然中,才不會感覺孤獨,植物的清新是福音,滋養生命,這時獲得自由,找到家的感覺,這個家是本性,內在的心靈世界。
面對自然時,所有的語言顯得蒼白無力,所有的行動顯得無力。在植物面前,卸下一切的虛偽和俗氣,一枚樹葉,一面清晰的紋絡,就是生命檔案中的痕跡,漫出風雨和陽光的日子。一滴晶亮的露珠,濃縮夜晚的精華。
天空的光線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它們投映植物上,各不相同。一個寫作者無法捕捉,捉住瞬間的美。植物的天然美,不是擺排場的,摻雜任何虛假,它們身上散發純凈的精神之光,文字不可能全部表達出來。它們不僅是鮮活的生命,,傾述自己的情感。這是無法復制的,也不能模仿。當人的情感經過植物的蒸餾,產生出來的藝術晶體,才是寫作者所追求動力的來源。
R.W.愛默生說道:“如果一個人是摯愛自然的,那么他的內在感官與外在感官就總是息息相通的,縱然他已進入成年,但其童心仍然不泯。他與蒼天和大地的神交成為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他與自然獨對時,一股激越的欣喜將流遍周身,即使他本來正不勝傷悲。”植物不是工藝品,憑人的想象和熱愛,創造出來的作品。植物大地的孩子,當一粒種子埋進泥土中,經過溫度、濕度和陽光的哺育,它破土而出。它拒絕媚俗,經受大自然的教導。植物是一座教堂,人們站在它的面前,心靈虔誠,充滿敬畏之情,而它教給我們特殊的宗教精神。
作家衣水的《醒著的植物》,散發著清新的氣息,在浮躁的現實生活中,讀每一個字,都有深厚的意義。經過植物培育的情感,塑造出的精神,生長在作家的生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