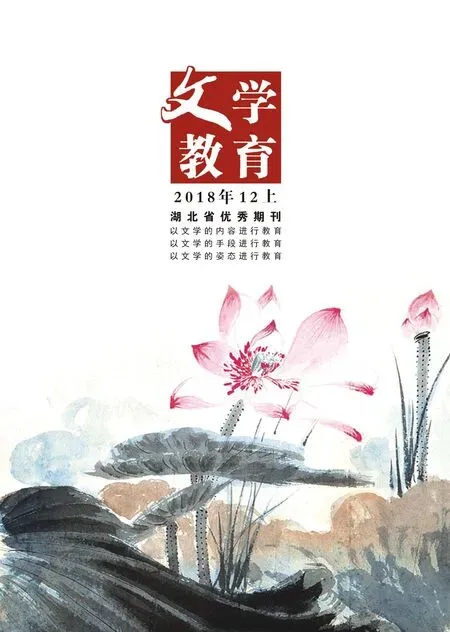淺論《聊齋志異》中的書生形象
段鈞譯 楊 萍
作為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的巔峰之作,《聊齋志異》(以下簡稱《聊齋》)從清初誕生以來便備受世人矚目。從詩壇盟主王士禎的題贈以及清中葉的馮鎮巒、何守奇、但明倫數家評點,直至今日蔚為大觀的蒲學聊學,三百多年過去了,研究領域涉及蒲松齡的生平家世、文本內容、藝術手法、創作心理等等,堪稱無所不在。《聊齋》為我們展示出了一個豐富、世俗、真實的清代社會,塑造了一個“上至帝王將相,下至乞丐妓女的龐大的形象系統”。①在林林總總的人物中,書生的形象十分突出,構成了《聊齋》中一個特殊的群體。
《聊齋志異》中的書生是一個很引人注目的群體。從《聊齋》科舉題材的作品來看,他們是當之無愧的主人公,體現了作者對當時科考制度的思考和看法;從愛情題材的作品來看,雖然他們在各具特色的“花妖狐魅”面前不免有些黯然失色,但仍是備受青睞的對象;從社會題材的作品來看,他們的生存狀態和境況遭遇,也深刻反映了那個時代復雜的社會現實。②由于《聊齋》是一部短篇小說集,是蒲松齡在幾十年的生活中慢慢積累創作而成,因此,其中的書生形象有時不免顯得庸俗,但整體來看,他們都離不開同一種模式:科舉路上的艱難跋涉,屢戰屢敗,使得他們謀生無計,窮困潦倒,而經濟地位的低下又使得他們在社會生活中飽嘗世情的冷暖。雖然如此,飽讀圣賢之書的他們仍然能夠堅守儒家傳統的倫理道德修養,用孝悌、仁義禮智信等美好品質來維護自己精神世界的獨立與高潔。
一.書生類型
明清之際,科舉制度是書生進入仕途的唯一途徑。在科舉制度這個活力磁場的吸引下,書生把一生中大部分光陰投擲在八股之中。《聊齋志異》中出現的精神心理狀態各異的書生,恰好成為這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科舉制度所造就的社會縮影。
《聊齋志異》中“花妖狐魅,各具人情”,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反觀作為愛情另一陣營的龐大書生群體也毫不遜色,與之相映生輝。《聊齋志異》中的書生形象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性情癡狂重義氣的書生
在《聊齋》中有些書生為了自己的紅顏知己的安危和幸福,可以不顧一切、舍生忘死。《阿寶》中的孫子楚是個窮讀書人,而美麗的阿寶卻是個富家少女。有人就捉弄“性遷訥”的孫子楚,讓他去向阿寶求婚,阿寶戲言:“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沒想到孫子楚竟毫不猶豫地自斷其指,痛得幾乎死去。阿寶再次戲弄他,“戲請再去其癡”,孫子楚就有點灰心喪氣,后來他見到美麗的阿寶之后,靈魂竟隨之而去,后來,又化成鸚鵡依偎在她的身邊。孫子楚的一片赤誠之心終于打動了阿寶,最終她深深愛上了這個出身貧賤但感情真摯的“孫癡”。
《連城》中連城的父親史孝廉拿她的“倦繡圖”“征少年題詠,意在擇婿”。喬生獻詩后連城非常喜歡,“對父稱賞”。但史孝廉卻嫌貧愛富,把連城許給鹽商的兒子。不久連城患病奄奄一息,有個西域番僧說要青年男子心頭的一錢肉做藥引子才能治好病,連城的父親就“使人詣王家告婿”。女婿卻露出自私面目,嘲笑史孝廉:“癡老翁,欲剜我心頭肉耶!”在此關鍵時刻,喬生“聞而往,自出白刃,膺授僧。血濡袍褲,僧敷藥始止”。喬生為了挽救心上人的性命,割去心頭之肉也毫不在意。
《嬌娜》中的孔生跟皇甫生交往,亦友亦師。孔生胸前生了腫塊,皇甫生請妹妹嬌娜前來醫治,“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頻呻頓忘,精神為之一爽”。孔生立即喜歡上了嬌娜,孔生對嬌娜一見鐘情,向皇甫家求婚,卻因嬌娜年齡小,而娶了嬌娜的表姐。嬌娜和孔生既已成為親戚,他們之間的感情似乎就永遠埋在心底了。但是,當嬌娜一家面臨雷霆之災時,孔生卻毅然挺身仗劍保護,不顧自己的安危,被雷霆擊暈也在所不惜。
“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儒家所提倡的“仁愛”思想的一種體現。蒲松齡自己就是個儒生,因此他的作品都滲透著儒家的仁愛思想,他所塑造的這幾位重情重義書生形象無不是“仁愛”的化身。
(二)不仁不義的書生
這一類書生都是些忘恩負義、見異思遷的典型,與上一類書生完全站在了對立面上。《武孝廉》中的石某進京求官,中途暴病,“唾血不起,長臥舟中”。他為行賄準備的“囊資”也被仆人偷走,“資糧斷絕”。這時他遇到了服飾炫麗的狐婦,狐婦“自愿以舟載石、以藥餌石”。正是有了狐婦幫助,石某才避免了必死無疑的下場。年長于石某的狐婦救活石某后,向石某求婚:“如不以色衰見憎,愿侍巾櫛。”石某歡天喜地同意。但是等石某謀得官職之后卻露出了真面目:先偷偷納妾,再常于寢后使人嗣聽狐婦的動靜,最后終于在狐婦醉酒后露出原形時想殺死她。石某的負心,不僅僅是喜新厭舊,還有忘恩負義,不仁不義成分在里面。
《韋公子》中的韋公子有錢有勢,縱情聲色,家中仆婦、丫鬟,稍有姿色的,他都不放過,結果在尋歡取樂時先碰到自己的親生兒子,又碰到自己的親生女兒,最后為了掩蓋自己的丑行,韋公子竟然喪心病狂地毒死了親生女兒,最終韋公子受到了最深重的懲罰,他家里有五六個大小老婆,沒一個生過孩子。
《丑狐》中的穆生家里很窮,冬天連棉衣和棉被都沒有,突然來了個衣服炫麗、又黑又丑、自稱“狐仙”的女子要求同榻。穆生不樂意,丑狐拿出元寶,穆生見錢眼開,“悅而從之”。靠了丑狐接濟,穆家成了小康之家,有了田產,使喚上了丫鬟。依靠丑狐過上好日子的穆生開始嫌棄丑狐,最后竟然請了術士驅趕丑狐。丑狐罵他背德負心,抱了個貓頭狗尾的小動物來,把穆生的腳咬得爽脆有聲,啃掉了兩個腳指,把當初她帶給穆生的財物全部索回。忘恩負義的穆生遭到了報應,“家清貧如初矣”。
(三)女性化的書生
自明中葉后期,隨著俗文學的不斷文雅化,小說領域中的主人公身份也在不斷的發生變化,代表下層知識分子群體的文人逐漸從幕后走到了臺前,成為了文學作品中的重要角色。《聊齋志異》中書生形象總體上都陽剛不足,呈現出了較為明顯的女性化的傾向。從他們的外貌形象來看,這類書生具有一定的女性化特征。
如《胭脂》中的鄂生“白服裙帽,豐采甚都”,《嘉平公子》中的嘉平公子“風儀秀美”,《陳云棲》中的真毓生“能文,美豐姿,弱冠知名”,《顏氏》中的順天某生“年十七,不能成幅。而豐儀秀美”。《香玉》中的黃生,他與花精香玉相處一段時間之后,突然遭遇變故,白牡丹被一游客移去,黃生明明知道白牡丹就是香玉所化,但卻束手無策,只會“作哭花詩五十首,日日臨穴涕咦”,而坐視自己心愛的人枯萎而死。
小說對這些書生美貌的描繪多用“美如冠玉、美豐姿、豐儀秀美、齒白唇紅、眉清目秀”等詞語,帶有明顯的陰柔美傾向。他們除了在外在形象上有女性化傾向,在內在心氣和行為上也帶有明顯的女性化特征。這些書生形象喪失了男人應有的勇敢、陽剛、主動和責任心。在性格方面,他們大多膽小怕事、怯弱自私,缺乏與惡勢力抗爭的勇氣。
封建禮教一直強調“男尊女卑”,以男子為中心的封建倫理綱常制度過于壓制女性,縱容男性,使得男女性格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錯位,男性喪失了對女性的平等、尊重意識,導致男性弱化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懦弱、被動、缺乏責任心等后果③。因此,《聊齋志異》中的部分書生形象由于受其影響,出現了男性性格的弱化與女性化傾向。
二.書生的性格特征
在《聊齋》中,男主人公一般以書生的形象出現,即使不是官宦子弟,也是出于商賈之族,都能詩善文,能彈善對,我們將這類愛好高雅,喜歡讀詩書的男主人公統稱為書生。筆者總結《聊齋》里面的書生,大致有以下幾種性格特征。
(一)知書達禮
故事中的書生剛開始多貧困潦倒,但是很有上進心,苦讀詩書,因而即使眼下一文不名,但還是能夠得到鬼狐仙女的青睞。如《白秋練》中,“直隸有慕生,小字蟾宮,商人慕小寰之子,聰慧喜讀”。又如《于去惡》中,“北平陶對俞,名下士。順治間,赴鄉試……相與傾語,言論有名士風”。
(二)渴望功名
書生寒窗苦讀,為的就是考取功名,正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因而《聊齋》故事中,多記敘書生趕考,有的屢試不第;有的金榜題名加官進爵,《俠女》中的顧生,自己雖然沒有考取功名,兒子卻在十八歲就中了進士;《聶小倩》中的寧采臣,“后數年,寧果登進士”。
(三)追求公平
明清己經到了封建社會晚期,社會不公、人間不平、世風日下、吏治腐敗的現象非常嚴重。知識分子受到迫害也在情理之中,因而十分渴望天下太平長治久安。《聊齋》鞭撻了丑陋的社會現象。《司文郎》一文中,有才學的王生無法步入仕途,而碌碌無為之輩卻靠師徒關系金榜題名,作者借瞽僧的嘴道出“簾中人并鼻盲矣”。
三.結語
蒲松齡一生潦倒落魄,孜孜不倦地讀書、教書、著書,堪稱封建時代典型的落魄文人。正因為如此,他對下層書生的真實處境有著十分深刻的了解,為了抒發心中的憤懣不平,他用自己的生花妙筆,將自己的經歷理想化和浪漫化,為這些懷才不遇失意感傷的書生們設計了讓從古到今所有人都“寤寐思之”的美好結局④。雖然這一切只不過是鏡花水月,但這體現了蒲松齡作為一介落魄書生,對自己在社會現實生活中所遭受的種種精神和肉體上折磨的一種自我抒解與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