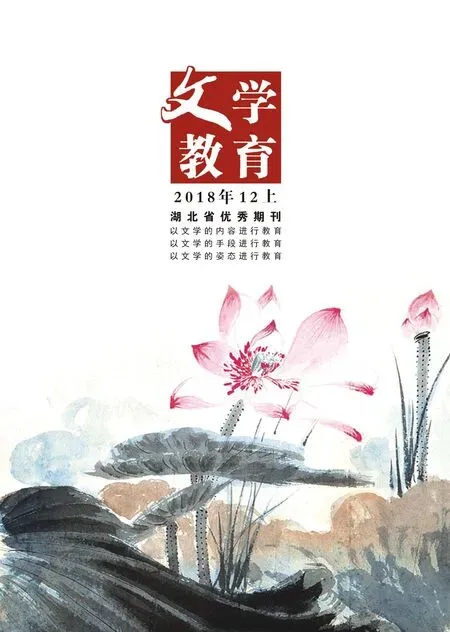余華先鋒小說對儒家文化的反叛
溫欣星
1985年開始,文壇上出現一批先鋒小說,這些小說具有現代派小說和后現代主義的特點,以馬原、洪峰、余華、格非等等為代表。余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創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說,并以其極致的先鋒符號迅速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他的小說大量描寫了暴力、苦難,整個基調都是充滿死亡氣息的。他不僅關注域外的文學形式,更重要的是他的寫作觸及到先鋒的精神,將人物置于暴力、死亡之下,去感受這個世界的荒誕。
對余華小說與傳統文化關系的研究眾多,因為不同時期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點。先鋒時期的寫作,以及后來轉向民間的寫作,余華表達的東西不同,由此可見余華是一個發展的作家。而本文將討論余華先鋒小說與儒家文化的關系。余華的先鋒小說文學觀念上顛覆了傳統的真實觀;從小說形式上看,他的敘述游戲話,結構破碎,人物不再具體;從文化影響上看,余華學習了豐富的外國文學,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外國文學的影響。綜合而言,從寫作形式到內容,余華不再是傳統的作家類型,從而談到余華先鋒小說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反叛的存在。本文將從三個方面來論述余華先鋒小說對儒家文化的反叛,極致的暴力環境、充滿暴力因子的人物與儒家宣揚的“中庸之道”背離,也通過這種暴力本能來警惕人類;先鋒小說里呈現的倫理關系是冷漠的,表明了作家對傳統倫理關系的態度;對“禮”的掙脫描寫了無序的世界,體現了作者對集體無意識的思考。余華曾說:我覺得最大的誤解是把先鋒文學變成了理論的,而不再是把它當成真正的作品。本文在研究先鋒小說與儒家文化關系時,將深入文本,不將小說符號化,從實際的文本出發。
一.以極致反“中庸”
余華寫道:“寫《現實一種》的時候,是我寫作生涯最殘酷的時候,我印象很深,那里面殺了好幾個人,還有《河邊的錯誤》、《一九八六年》。我印象中那個時候寫了一堆的中短篇小說里殺了十多個還是三十幾個,那個時候不知道為什么就不能擺脫自己一寫小說就要殺人,必定里邊有人死亡,最后是我自己都受不了了,晚上盡做這種夢,不是我在殺人就是別人來殺我,有一個夢里我在被公安局通緝,我東躲西藏,醒來是一身冷汗,心想還好是夢。”【1】其實在余華的小說中,我們經常可以看見暴力描寫,暴力的語言,暴力的行為,構成一個個暴力環境。《十八歲出門遠行》里“我”的父親給了“我”一個紅色的背包,告訴“我”,你應該去認識一下外面的世界了。行走在未知的路途,一開始的“我”很快樂,看見許多美麗的山和云,而漸漸地“我”開始害怕了,當“我”學著大人模樣與人交往,卻被村民毆打,丟棄在半道,這樣的世界讓“我”感到恐懼,渾身冰冷。余華通過初入社會的孩子的眼睛,描寫了我們生活環境的冷漠與暴力。《西北風呼嘯的中午》中,在家休息的“我”被一個陌生人打擾,他踢開“我”家的門,怒氣沖沖地講話,把“我”從被窩提出來,扔到地上,逼迫“我”去見一個并不認識的要死之人。這一系列行為是在“我”無意識的情況下發生的,它在告訴我們,只要我們生活在這個世上,積極面對也好,躲避也好,暴力會在不經意間找上你,我們生活在暴力之下,它似乎無處不在。而另一方面,典型的暴力環境還塑造了許多暴力的人物形象。《朋友》中,一開場就是昆山拿著把菜刀要去宰石剛,兩人在澡堂前用菜刀和毛巾開始了漫長的打架。《往事與刑罰》的刑法專家將自己置于暴力的空間,實驗著不同的刑罰,最后死于自己創造的刑罰。《黃昏里的男孩》里的孫福抓住偷蘋果的男孩,把他提起來,卡住他的脖子,讓男孩把嘴里的蘋果吐出來,吐到連唾沫都沒有,孫福才罷休。而后將男孩右手中指扭斷,把他綁在水果攤前,對著行人喊:我是小偷。男孩一開始是祈求孫福給自己一點吃的,不過孫福用暴力的語言和動作拒絕了男孩,無奈之下男孩才偷了一個蘋果,這就讓孫福用更加暴力的語言和動作教訓了男孩。暴力充斥著余華的小說,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場景似乎都在不同程度地遭受暴力的毒害。暴力不止是工具,它還是情緒的發酵劑,暴力會刺激到人們的大腦,讓人處于一種情感的極端,失去理智,導致很多事情失去控制。在余華的小說中,一部分人是在情感的沖擊下去傷害別人,同時還有一些人,在暴力情境下,他是清醒的,理智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余華先鋒時期的作品中,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一個話題,暴力環境下的人們試圖用暴力來解決問題,從極致的體驗中獲得滿足。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與我們儒家文化宣揚的“中庸之道”是有背的。
《論語》里記載,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2】孔子看來,過分與不足都是一樣的。子思在《中庸》中進一步發展了祖父的中庸思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3】可以說,個體情感與意志的恰切調控,決定這生命個體與群體、社會、自然的共生共榮。“中庸”是由“禮”轉化而來,是禮的理論化和哲學化。這種禮不是制度規章繁文縟節,而是從人的心理結構中透出的思想觀念和價值體系對人的基本要求。這意味著,中庸不是平庸和放縱,不是日常的放松和失度,而是用更高的合于“禮”的要求來約束自己,使人不要去追求過多的外在物質附加物。【4】余華先鋒時期的創作,筆下的人物更多的是一種冷漠狀態,對自己,對人生,對世界缺少一種自我意識,他們靠自己的第一直覺在活著,習慣性的使用暴力解決問題,以自我保護為出發點,可讓人感受到的是他們對自己生存的狀態的悲傷與絕望,余華也是通過暴力來反映人物的無意識狀態,以及人性的惡,荒誕的人生。“它是余華凝視人的生存的鏡子,通過描述特定境遇下人的內在暴力本能的迸發以致相互殘殺與毀滅,余華讓我們直面人類血淋淋的生存酷景,讓人們認識到人的暴力本能這內在之魔時時刻刻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從而引起我們高度的反思與警醒”。【5】
二.倫理關系的顛覆
生活經驗告訴我們,人與人之間相處,總有一種特殊的關系,這種關系既不是自然的、盲目的關系,也不是由權威、律令強行規定的關系,而是一種由關系雙方作為自覺主體本著“應當如此”的精神相互對待的關系。這種關系就體現著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凡是經歷過社會生活的人,都不能否認這種社會關系的存在及其重要意義。【6】它滲透于一切社會關系中,具體存在于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整體以及集體與集體之間的關系中。在古代,孔孟從人的角度建立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大廈,這種思想領導中國人幾千年,有著重要意義。而談到余華先鋒小說與傳統倫理關系,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顛覆的存在,本篇文章將重點討論余華筆下的家庭關系和兩性關系。
第一方面,家庭關系的消亡。家庭是人類道德生活的一個重要領域,就人類社會發展以及個人成長而言,家庭關系都是最初的道德關系。另外,中國是個農耕國家,這種生產方式深深影響中國人民的家庭觀念,形成了厚重的家族文化,并且建立了一套以孝為價值評價標準的家庭倫理關系模式。然而余華在創作中卻有意地消解這種關系,失去傳統的上慈下孝,家庭關系是一種冷色調的呈現。《世事如煙》中,4的父親6先后將自己6個女兒賣到天南海北,他意識到,長大的女兒已經不是一種累贅,而成為了財富。于是當一個陌生男子來到4的家時,4總是會做噩夢,4在被算命先生侮辱后不久就死了。小說中的人物家庭觀念不再清晰,大家都是極致的利己主義,欲望的膨脹,人們迷失自己,充滿著丑陋,從而余華小說中的家庭關系總是蒙上了一層灰層,冷漠的,沒有生命。《現實一種》中母親冷漠,兄弟相殘,整個家庭分崩離析。母親整天都在抱怨自己的骨頭發霉了,孫子偷吃了一點她的咸菜,竟然眼淚汪汪,喋喋不休地說:“你今后吃的東西多著呢,我已經沒有多少日子可以吃了。”【7】面對小孫子的死,只是嚇了一跳,就趕緊走回自己的臥室,仿佛與自己無關。山崗和山峰打架,母親也只是準時出現在餐桌旁,不會有任何舉動,最后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躺在床上,等待死亡。從母親就可以窺見這個家庭情感的淡薄,暗示家庭的衰敗。山峰踢死皮皮后,山崗默默地籌備殺死山峰的計劃,他將山峰綁在樹上,在腳底涂上燒爛的肉骨頭,讓撿來的小狗舔,最后山峰笑死了。兄弟之間沒有了所謂的情義,平常的風平浪靜一旦被打亂,整個人都是瘋狂的。
第二方面,兩性關系。首先,無論是愛情關系,還是夫妻關系,在余華的小說中都模糊了界限。《世事如煙》中瞎子很喜歡4的聲音,在4投江后,他在江邊坐了三天,江水里傳來4流動般的歌聲,第四天,瞎子也走進了江中。3的孫兒是一個已經十七歲的粗壯男子,可依舊與祖母同床,最后還有了孩子,在3走后,她的孫兒常常坐在門檻上喪魂落魄地看著4的房門,整個人處于一種無意識的狀態。小說中的兩性關系,余華用一種曖昧的手法展現出來,荒誕又可悲。其次,儒家文化構建了“夫敬婦齊”、“琴瑟和鳴”的夫婦倫理規范,兩性應該遵循的賢和禮,在余華小說中卻顯得很淡薄。《現實一種》中山峰面對孩子的死,他把自己的情緒發在自己的妻子身上,罵她,打她,在丈夫身邊一直小心翼翼的。皮皮學著父親打母親那樣,對準堂弟的臉打去一個耳光。在這個家庭夫妻關系充滿暴力,沒有絲毫的溫情可言。傳統文化中的夫妻關系,《孔雀東南飛》里的劉蘭芝和焦仲卿是典型的,以禮相待,相濡以沫。然而在余華的筆下,兩性關系變得模糊混亂,充滿了暴力因子。
先鋒時期,余華打破了儒家所宣揚的倫理關系,用這種方式讓人們去思考我們正在經歷的世界,然而作者在文中并未建造出新的倫理關系,只是發現了問題。九十年代開始,余華慢慢調整自己的創作,發表了《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三部小說,這三部小說對“人”以及生存問題投入更多的思考,也對傳統的倫理關系做了進一步探討。
三.對“禮”的掙脫
儒家強調克己復禮,就是一個人能夠克制自己的情感,每件事都歸于“禮”,人們不能為所欲為,從而達到“仁”。《禮記·經解》在說明禮的作用時指出:故以奉家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故制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8】這說明,儒家禮學中的朝覲、聘問、喪祭、鄉飲酒等禮,是一整套習俗和儀式,儒家的理想是通過這些儀式和習俗,養成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一定的關系觀念和倫理觀念,形成一種文明社會的理想秩序。【9】然而從余華的小說中,我們更多的感受到對“禮”的掙脫,大家處在一個沒有秩序的世界。
《古典愛情》講的是才子佳人的故事,貧寒書生柳生進京趕考,途徑一座城,遇見繡樓一位女子,兩人產生情愫之后的一系列故事。在后面的發展中,柳生再次上京趕考,卻發現萬物凋零,一路上盡是些行乞之人,偶然間,柳生發現菜人市場的存在,男人將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帶到市場,幼女被拖入棚內,將手臂放在樹樁上,店主拿起利斧猛劈下去,骨頭被砍斷,店主將砍下的手臂賣給行人,婦人忍受不了就一刀殺死了自己的女兒,然后看著女兒被肢解,一件一件賣給別人。柳生逃出這個地方,來到一個酒店,在這里他遇見了淪為菜人的小姐。一位顧客要吃新鮮的肉,伙計就去砍掉了小姐的腿,柳生跑到廚房看見了血肉模糊的繡女。余華的描寫是殘忍的,當大家都在期待美好的愛情發生,他卻安排這樣相逢,將人置于殘酷空間,讓人去思考。在作者筆下,這個世界是沒有“禮”的,太平年代,每個人都彬彬有禮,柳生寫的宋詞絕句,畫的無骨花卉被眾人追捧,而一旦處于生死存亡時刻,人們會摘掉面具,展現人性最丑陋的地方。曾經的這里,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房屋稠密,人物富庶,人人有禮。災難面前,一家之主可以為了活著,就把自己的妻子女兒送到菜人市場,任人宰割,人們也心安理得的買著人肉;為了吃新鮮的肉,伙計沒有猶豫地砍下繡女的腿。有的時候,活著真的比死還痛苦。余華對“禮”的掙脫,把殘酷的現實揭露出來,讓人們直面現實,去思考我們的人性究竟是怎樣的。
《古典愛情》體現的不止是個人的“失禮”,余華要談的是集體、整個社會的“無禮”狀態。魯迅在自己作品中塑造了“看客”形象,魯迅寫了人們的冷漠,集體無意識的狀態,《藥》看行刑的人頸項伸很長,就像鴨被無形的手捏住,向上提著。華老栓的鮮血饅頭,讓“看”與“被看”的關系慢慢走向“吃”與“被吃”。多年之后,余華通過自己冷靜地觀察,描寫人們對“禮”的掙脫,打破傳統的儀式,探討集體“無禮”的問題。
四.結語
《鮮血梅花》題材上是一部傳統的武俠小說,以“復仇”為主線,然而作者不是要講江湖恩怨、兒女情長,而是通過阮海闊的復仇之路,讓他更加清楚他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這么做,這就是作者顛覆性的解讀。先鋒時期的余華沒有按照傳統的寫作,注重小說的人物、情節描寫,反而是忽略了這些因素,寫作風格別具一格。余華小說對儒家文化一定程度上的反叛,一方面是與自己的生活環境有關,余華在醫院長大,見過很多生離死別與血腥場面,這在先鋒小說中都有所體現;接受的文化也深深影響著余華的視野與寫作。另一方面是余華與這個世界的緊張對話關系,他一直用自己的眼審視著這個世界,撕破面具,一切都是那么丑陋,所以余華打破原有的圈子,走了出去,用更加自我的方式宣泄這個世界的荒誕,先鋒小說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文學空間的可能性。作者不是傳統的作家,對儒家文化所宣揚的東西有時更是背道而馳的,余華的偉大之處在于他知道自己要拿起什么,去擊碎什么,彰顯先鋒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