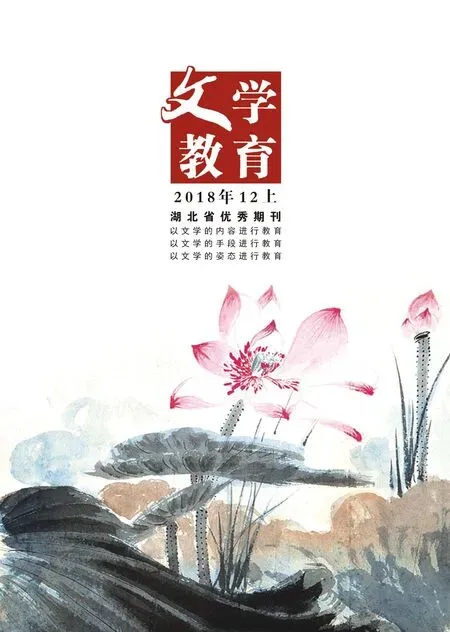論艾麗絲·門羅小說中母愛神話的破滅
魯向黎
加拿大當代短篇小說家艾麗絲·門羅擅長從女性體驗出發,書寫人性的困惑。而關注女人作為一個人的全部生命力,是門羅一慣的創作態度,也是作為一個女作家抗衡傳統性別角色的重要策略。
傳統性別角色中,女性是作為妻子、母親、女兒的形象出現的,而她作為一個人的形象則是缺失的。她是附屬的,是次要的,是邊緣的;她是客體,是他者,是第二性,唯獨不是一個完整的人。母親角色就是女人身上最沉重的一道枷鎖。在父權制社會中,生育、撫養孩子是女人不可推卸的責任,是女人最重要的工作。而用母愛的無私奉獻將女人的生命力全部耗盡,讓她安于家庭,禁錮她的欲望,扼殺她的創造力,便是傳統父權制社會固化性別角色的重要手段。母愛神話就是這樣被想象出來并被套在了女人的身上。而把女人作為一個人來塑造,無疑是沖破女性被想象、被塑造的命運,脫掉女人身上的角色外衣,展露出女人作為人的真實性。
艾麗絲·門羅在她的短篇小說中,塑造了很多不稱職的母親形象。她們在母親角色和個體欲望的痛苦掙扎中,拋棄母愛偉大無私的角色設定,追求自己的生命綻放——或事業或情欲。而從女性主義理論來看,這樣不合格的母親角色,卻正打破了傳統的女性命運,放棄了虛偽的道德綁架,讓女人以一個真實的人的形象出現,展現她的欲望,釋放她的生命力,具有沖破父權制性別桎梏的意義。在門羅的短篇小說集《好女人的愛情》中,《我媽的夢》和《孩子們留下》這兩篇小說正好從事業和情欲兩個層面書寫了女人對自己真實生命力的釋放。
一
《我媽的夢》是《好女人的愛情》這部小說集中的最后一篇。小說的女主人公吉爾從小在孤兒院長大,十二歲時因為被帶去聽了一場音樂會而愛上了小提琴,并在資助者的幫助下進入了音樂學院學習小提琴。吉爾發自內心熱愛著小提琴,“她深信,她和小提琴自然而然、命中注定彼此相連,即便沒有人為的幫助,也必然要走到一起。”[1]然而吉爾對小提琴的熱愛卻遭到過很多人的質疑。高中的一個老師就曾建議她不要太過于關注小提琴,“老師似乎認為,音樂是吉爾用來逃避或取代什么的一種東西。比如兄弟姐妹、朋友和約會。她建議吉爾多花點精力做別的,不要只關注這一件事。”[2]在男性本位的慣常思維中,一個女孩有朋友和約會就足夠了,她不需要聰明智慧,不需要知識和技術,當然更不需要有什么事業和夢想了。吉爾的熱愛遭遇了傳統性別觀念的第一次阻礙。
在音樂學院吉爾認識了喬治,在沒有畢業的情況下就結了婚懷了孕,而沒等到孩子出生,喬治就上了戰場,并在一次飛行訓練中失事身亡。吉爾在喬治的葬禮上生下了孩子,接著就開始面臨孩子與小提琴之間的激烈沖突。吉爾試圖在孩子睡著之后關著門輕輕地拉琴,但沒想到孩子聽到琴聲竟然一聲慘叫號哭起來,孩子的兩個姑姑立刻命令吉爾停止拉琴,吉爾不得不放下了小提琴。
而最為慘烈的一幕是吉爾和孩子單獨在家的那一天,吉爾無論如何都無法停止孩子的哭聲,竟然想用拉小提琴轉移自己或者孩子的注意力,結果孩子的哭聲一刻都沒消停。最后絕望的吉爾在自己吃下鎮靜藥的同時,也給孩子的奶瓶里撒了一點。吉爾和孩子因此昏睡了十幾個小時。這是吉爾的音樂夢想遭遇的最沉重的打擊。這意味著孩子與吉爾的小提琴成為了仇敵,吉爾如果要孩子,就必須割舍她的音樂。“我的哭喊像把刀子,從她的生命中割去所有沒用的東西。對我而言沒用的。”[3]一個成為母親的女人在孩子和自己的事業之間該如何權衡呢?傳統性別觀念給出的是一個絕對肯定的答案,那就是放棄事業,全身心照顧孩子。母親在傳統性別觀念中就意味著無私、犧牲、奉獻,她不能有自我,不然就背叛了母親的角色。作為一個女人,人們更關注她是否是一個稱職的母親,而并不在乎她是不是一個音樂家。但明顯的一個事實是,人們絕對不會以孩子為理由剝奪一個男人的事業的,于是,父權制社會對待性別的雙重標準便顯露出來。吉爾給孩子喂鎮靜藥這件事情雖是在萬般無奈幾乎絕望的情況下發生的,但其實卻包含了吉爾對自己性別角色的反抗,為什么要讓一個女人為了孩子犧牲自己所熱愛的事業呢?僅僅就因為她是一個女人,她是一個母親,她就必須無私犧牲自我嗎?當人們把一個女人真正作為一個人來看的時候,這樣的不公平就顯而易見了。
在小說的結尾,孩子最終醒過來了,并且在這一次事故之后,孩子竟然奇跡般地和吉爾和解了,吉爾如愿以償地從音樂學院畢了業,并且能夠作為音樂家被聘用,養活了自己和孩子。這個結局其實表達了門羅的一個美好的愿望,即一個女人既能擁有母親身份也能展現一個人的價值。但現實的殘酷也只能讓這個結局成為一個愿望罷了。門羅并不堅定。她只能讓吉爾和孩子和解,或者說,讓吉爾的事業和自己的母親身份和解,因為她別無選擇,她不想魚死網破,那太慘烈了。門羅不忍心拋棄孩子,因為她也是一個母親。
二
《孩子們留下》這篇小說的女主人公鮑玲是一個年輕的母親,有兩個年幼的女兒,故事開始于她和丈夫全家一起去海邊度假。鮑玲參加了一場業余的戲劇演出,所以雖是假期,但她不得不在照顧孩子的間歇復習臺詞,幾乎沒有什么空閑。“假期中,鮑玲設法擠出獨處的時間——照顧瑪拉時,她幾乎相當于在獨處。清早的散步、早上遲些時候她洗晾尿布的一個小時。下午,她原本可以利用瑪拉睡覺的時候再擠出個把小時。”[4]“鮑玲沿小路推著瑪拉時,果真在背臺詞。”[5]而這就是一個有自己愛好的母親的慣常姿態,沒有完整的時間,沒有獨處的空間,在孩子和家務的縫隙中尋找內心的聲音。而男人卻可以完全拋開這一切專注于自己的興趣和事業。
但這篇小說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寫女人的愛好,而是寫了女人的欲望。鮑玲在排演戲劇時和導演杰弗里相愛了。“和布萊恩……是絕不可能出現這種魂飛天外,這種無可抗拒的飄飄欲仙,這種她無需努力爭取,只用安心承受,就像承受呼吸或者死亡一樣的情感的。她相信,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有可能:這皮膚得長在杰弗里身上,這動作得由杰弗里做出,壓在她身上的重量里得有杰弗里的心,還有他的習慣、他的思想、他的特性,他的野心和孤獨。”[6]“引用杰弗里的話的時候,鮑玲感覺子宮,或者胃的底部一陣虛弱,一股奇特的震顫朝上傳遞,直擊聲帶。”[7]在這些細膩的描寫中,女人的欲望被真實地展露了出來。欲望是一種生理反應,因而它是最真實的,和道德無關。但在父權制的思維里,女人被祭在高高的神壇上,被剝奪了一個人的豐滿后,塑造成了一個無性的等待男人賦予生命的犧牲。“這些女人沒有真實人的生活,她們只是一個美好但沒有生命的對象。將女性神圣化、理想化的行為,無疑是對女性形象的歪曲。”[8]“不管她們變成了藝術對象還是圣徒,她們都回避著她們自己——或她們自身的舒適,或自我愿望,或者兩者兼而有之——這就是那些美麗的天使一樣的婦女的最主要的行為”[9]女人是不應該有欲望的,女人的欲望是罪惡的,一旦女人有了欲望,她就反被動為主動,在生理上駕馭男性了,這當然是男權所不允許的,所以極力塑造純潔無知無性的女人并使之安于母親的角色,是父權制禁錮女人身體的重要策略。而鮑玲卻是一個敢于正視自己欲望的女人,她為了自己的欲望甚至拋棄了家庭和孩子,和另一個男人私奔了。在傳統的性別視角中,鮑玲這樣的女人顯然是自私的,無恥的,她玷污了母親的神圣光環,當然要受到輿論的譴責。可是,女人是人,她有欲望,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既然是事實,那就只能說明父權制的歷史是怎樣殘忍地扼殺了女人的身體。所以小說的目的并不在于為婚外情辯護,而在于寫出一個真實的女人,一個女人真實的欲望。
鮑玲曾想過回到孩子們身邊,“要回到她們身邊,她并不需要鑰匙,并不需要那車。她可以在公路上請求搭車。屈服、屈服,千方百計回到她們身邊,她怎么會做不到?”[10]可是如果為了孩子勉強回去,之后的生活將會是什么樣子呢?“像一具行尸走肉。”[11]鮑玲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楚以后的婚姻。但是不回去,對孩子的牽掛和思念卻又成為一種永遠的折磨。“這是一種銳痛。它會變成慢性病。慢性意味著它將揮之不去,不過不一定會頻頻發作。也意味著你不會因它而死。你沒法擺脫它,但也不至于送命。你不會每分鐘都感覺到它,但不可能一連好多天都免遭它打攪。你會學會一些伎倆去掩蓋或驅逐這種痛,避免徹底毀掉你當初不惜承受它來換取的東西。”[12]女人是有欲望的真實的人,當然女人也是母親,作為一個女人的個體情欲和作為一個母親的母愛就這樣發生了尖銳的沖突,它在女人的身上發作,成為了一種揮之不去的痛,成為了一種慢性病。門羅呈現出了女人的痛,呈現出了女人的兩難之境,呈現出了女人作為人的真實性,這正是這篇小說的意義所在。
艾麗絲·門羅的很多小說中都出現了母親形象,但門羅筆下的母親往往不是傳統意義上溫柔慈愛、無私忘我的母親,而常常是執著于自己內心的女人。就像《我媽的夢》里吉爾執著于小提琴夢想,就像《孩子們留下》里鮑玲執著于愛情的欲望。她們也有母愛,但卻不愿為了僅僅遵從母親的責任而放棄作為一個人的生命力,她們要實現個體的價值,她們要張揚自己的個性,她們要釋放女人的欲望。在重重阻力下,在矛盾糾結中,門羅筆下的女人們掙扎著,痛苦著,選擇著,艱難地打破了父權制加在女人身上的沉重的枷鎖,撕開了罩在女人身上的神圣的母愛神話,從而呈現出女人真實復雜的生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