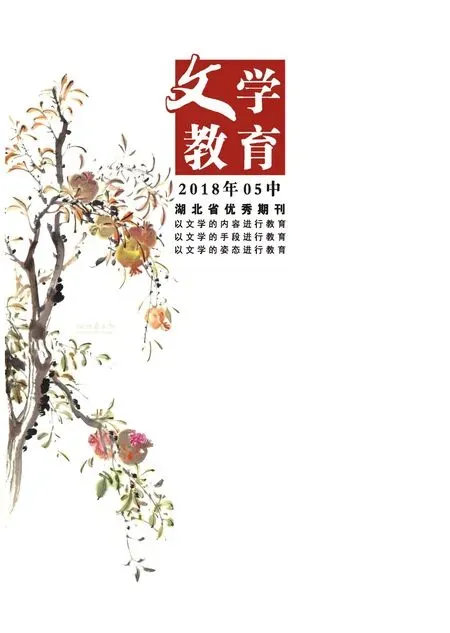唐代佛教信仰用香
李松柏
香的使用,來源已久。早在中國殷商時期就已有痕跡可以追溯,《尚書·舜典》記載舜祭天活動中燔木升煙,這被看作是后世用香的源頭。其后歷代,香的使用范圍逐漸擴大,至唐代時已經涉及到人們生活的多個方面,佛教生活自然也是其一。本文擬探討唐代佛教用香的基本形式以及用香的原因。
一.唐代佛教用香形式
佛教信仰,源生印度,本非中國所有,其記載最遲是在東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國。明帝于洛陽建造白馬寺,迎佛法、譯佛經,佛教始入中國。后經諸代興衰,至唐時佛教已較為興盛。而作為佛教中的重要物品“香”,在此時也被廣泛使用。
唐代佛教常見的用香形式有燒香供佛、焚香修行。如《白孔六帖》引陸龜蒙詩:“焚香禮真像,盥手披靈篇。”[1]唐義凈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卷六載:“應取諸香,所謂安息、旃檀、龍腦、蘇合、多揭羅(零陵香)、熏陸,皆須等分,和合一處,手執香爐,燒香供養(佛世尊)。”[2]此二者皆為燒香供佛這一用香形式的體現。同時,崔顥《贈懷一上人》云:“說法金殿里,焚香清禁中。”[3](卷130,P1322);姚合《寄默然上人》云:“幾生通佛性,一室但香煙。”[3](卷497,P5649)此二者為焚香修行這一用香形式的體現;此外唐代佛教的用香形式還有焚香祈祝。《酉陽雜俎》載“玄宗又召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挍功力。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香氣。”[4]不空乃唐代高僧,其應玄宗要求同道家名士羅公遠比試法術,使用焚香祈祝的方式以求雨。《冊府元龜》又載:“大歷初,(杜鴻漸)自劍南回,請千僧齋于資圣寺,仍請魚朝恩、李抱玉同行香許之,以使蜀地無恙徼福也。”[5](卷927,P10748)此處記載是焚香為地方祈福,也屬于焚香祈祝;除此之外,唐代佛教用香的使用形式還常見涂身、涂地、涂墻等。唐代有名的高僧玄奘在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夜半圓寂,當時有僧人用旃檀香末涂其身體。《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二載:“……(玄奘)遂右脅安臥而逝……俄異僧奉旃檀末香至,用涂法師之體。”[6]另外,唐不空譯《如意寶珠轉輪秘密現身成佛金輪咒王經·大曼荼羅品第四》載“佛告虛空藏菩薩言:持誦行者欲作曼荼羅成大悉地,……以白檀香、甘松香、郁金香、龍腦香……涂治嚴飾壇上。”[7]唐般剌蜜諦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七載:“佛告阿難若末世人愿立道場。……取其黃土,和上旃檀、沉水、蘇合、薰陸、郁金、白膠、青木、零陵、甘松及雞舌香,以此十種為細羅粉,合土成泥,以涂場地。”[8]此三者分別為用香涂身、涂墻、涂地。由此可見,唐代佛教用香的主要形式有燒香供佛、焚香修行、焚香祈祝、涂身、涂地、涂墻等。
二.唐代佛教用香的原因
前文談到,佛教由古代印度傳入中國。而古代印度暑熱非常,人們往往以當地盛產的香涂身、熏衣、涂地及墻壁,以消除身體體臭以及酷熱的苦惱,從而有了用香的習俗。隨著佛教的發展,這種用香習俗又融入了佛教教義之中。唐菩提仙譯《大圣妙吉祥菩薩秘密八字陀羅尼修行曼荼羅次第儀軌法》載:“復說速疾救難立成壇法:……以白檀香磨作涂香如面,更取精白、龍腦、薰陸香等,浸取汁如乳,如涂香磨涂地。”[9]這證明了以香涂身、涂地的習俗進入了佛教信仰的規定之中。而用香從印度人民為消除體臭和酷熱到逐漸融入佛教教義和佛教儀式的過程,這也暗和了涂爾干等人對于儀式的解釋(結構功能派)。早期佛教儀式的用香具有解決酷熱和體臭的功用,后來隨著佛教傳入中國,雖然這一功能在一些地區消失了,但是又產生了另外的功用。這種功用簡單來說和最開始的“神話—儀式”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性。按照美國“歷史學派”代表人物博厄斯的觀點來看,一個儀式就是一個神話的表演“人類學分析表明,儀式本身是作為神話原始性刺激產物”。而新的功用則是通過佛教焚香儀式來再現佛教傳說中佛所居住的環境,以達到修行的目的。同時,又通過焚香產生的煙霧升空來傳達自身意愿給天界居住的佛。(某種意義上說,焚香之后的煙霧就有點類似今日的無線電,起到了溝通交流的功用。)實際上,無論是模擬環境還是傳達意愿,這都是佛教信仰者借由模擬神話的象征儀式,獲得自我身份確認和群體認同的形式。另外,不得不說的是一些香本身是具有藥用成分的(特別是一些外來香藥),它們具有使人神清氣爽,精神愉悅,飄飄欲仙的功用,這就有助于佛教信仰者的佛教修行。而以上香的特點又是其它物品所無法替代的,這也正是香在佛教信仰中扮演重要作用的原因所在。
除此之外,這一時期絲路貿易的興盛使得大量外來香藥涌入唐帝國,也是原因之一。如《冊府元龜》載:“(開元十二年)三月,大食遣使獻馬及龍腦香。”[5](卷971,P11239)“(開元二十二年)六月,林邑國遣使獻沉香。”[5](卷971,P11241)帝國本身能獲得的香的消費資源得到了擴充,不再是品類單一的本土香。同時外來香藥也具有一些本土香不具有的功用(比如反魂香就具有治療短暫昏厥的功效,沉香使人神清氣爽的功效特別明顯)。當然,這些外來香藥作為貴族奢侈品消費,也是貴族身份的象征。所以,社會上層貴族為了彰顯身份和表達佛教信仰常常使用也就不為奇怪了。在平民力量覺醒的宋代以前,普通的下層百姓的自然無法大量的消費價格高昂的外來香,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一些本土香。但無論使用何種香,其使用的目的和功用自是不變的,皆是表達其佛教信仰。
香的使用在中國有著很早的歷史,隨著時代的變化,用香方式和種類也有著變化。唐人燒香祈祝、供養、修行,以香涂身、涂地、涂墻等這類用香方式表達了他們的佛教信仰。而探求為何是香在佛教儀式如此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自身的功能性。初期為了適應自然環境以及香本身的藥用屬性使得用香進入了佛教教義。同時通過用香來再現佛教傳說,獲得自我身份確認和群體認同,也是其功能性的表現。最后絲綢之路的興盛,外來香藥的大量輸入為香在唐代佛教廣泛使用提供了外部可能性。
參考文獻
[1]白居易,孔傳.《白孔六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337.
[2]義凈,譯.《金光明最勝王經》[A].《大正新修大藏經》[M].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0∶430.
[3]彭定求等編.《全唐詩》[M].北京:中華書局,1960.
[4]段成式撰,方南生點校.《酉陽雜俎》.北京:中華書局,1981∶39.
[5]王欽若等編,周勛初校.《冊府元龜》[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6]念常,撰.《佛祖歷代通載》[A].《大正新修大藏經》[M].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0∶581.
[7]不空,譯.《如意寶珠轉輪秘密現身成佛金輪咒王經·大曼荼羅品第四》[A].《大正新修大藏經》[M].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0∶332.
[8]般剌蜜諦,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A],《大正新修大藏經》[M],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0∶133.
[9]菩提仙,譯:《大圣妙吉祥菩薩秘密八字陀羅尼修行曼荼羅次第儀軌法》[A].《大正新修大藏經》卷[M].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0∶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