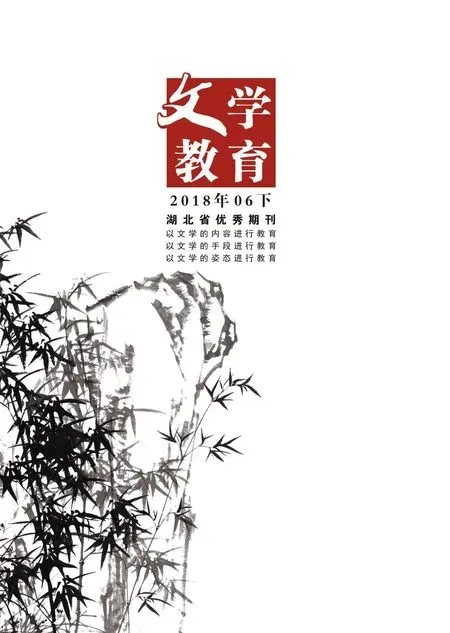淺談現代漢語語素的非語素化
鄧上清
一.語素的非語素化
現代漢語中絕大多數語素是單音節的,而這種壓倒性優勢使得我們常常把有些非語素語言單位也混淆其中。“語素的非語素化”是指語素變為非語素,即語素失去音或義的變化。以往的研究對語素的非語素化關注不夠,主要在楊錫彭先生的《漢語語素論》中有所涉及。楊先生將“語素音節的非語素化”劃分出了切頭詞、析音詞和析形詞、借用外來詞、諧音借代造成的語素音節的非語素化、因漢字記寫的原因造成的語素音節的非語素化現象這五類,并簡單解釋該現象的原因為“重新分析”,但對非語素化中的音義關系和深層原因未曾挖掘,分類也不夠完備。本文將在前人基礎上從語素的基本定義出發,將現代漢語語素的非語素化(以下簡稱“非語素化”)現象劃分為“存音失義”和“存義失音”兩種類型來做較為細致的分類剖析,并對該現象產生的原因加以探究,希望對我們今后認識非語素化和揭示詞匯構成及發展規律有所助益。
二.非語素化的兩種類型
語素是最小的音義結合體,其本質須是音義兼備,若失去其中任意一方就不能稱之為合法的語素。基于此,由于音義皆失的情況不在我們討論的范圍,所以對非語素化的研究可以從存音失義和存義失音這兩方面著手。
(一)存音失義
1.切頭詞、生動后綴
切頭詞是因音節的湊補造成了跨段切分,導致形成詞的無理據內部結構,使得語素(詞)非語素化的一類詞。“而已、的話、著吶、得慌、與否、幸而、有所、無所”等都是因跨層連用而形成的切頭詞。從內部結構來看,這類詞大都是由兩個語素結合而成。且這些語素原本是一個個獨立的詞,在漢語雙音節節律的影響下須要與另一個語素湊補為一個雙音節詞,于是從原語段層中被跨層切分而構成新詞,導致原語素最終失去其自身的意義,被虛化得只剩下讀音,變成了一個非語素音節。
另外,還有一類語源意義不清、經常合在一起整體連用的生動后綴也屬于語素的非語素化。如“咕隆咚、不拉幾、不溜秋、了呱唧、不愣登、不唧”等通常以一個整體的形式出現,我們在做詞法分析時一般處理為一個語素,因為少了其中任何一個音節,原有形式的意義就會發生改變甚至不成立。生動后綴中的各部分在進入此連用形式之后,只保留下原音節,而丟失其意義,實現了語素的非語素化。
2.析形詞、析音詞
析形詞、析音詞是因字形或字音析分而產生的一類詞。“八刀(分)”“四西(羅)”“耳東(陳)”“木子(李)”“弓長(張)”“立早(章)”等都是把一個單音合體字按字形拆分成多個獨體字后,經過約定俗成后形成一個新復音詞。而“窟窿 ”“ 蒺 藜 ”“ 窗 籠 ”“ 囫 圇 ”“ 匍 匐 ”等分 別 是“孔 ”“ 茨 ”“ 聰 ”“ 混 ”“爬 ”等字的音節雙分后,聲母和韻母分別綴以其他韻母和聲母組成新的音節而形成的詞,這是其語音分析的結果。如“孔(kǒnɡ)”的聲母k后綴韻母u形成“窟(kū)”,韻母onɡ前加聲母l形成“窿(lonɡ)”,最后二者結合形成“窟窿”。
另外,方言中還存在一類“嵌l詞”,即漢語中單音節詞在某些方言中分音成為第二個音節聲母為“l”的雙音節詞也可以歸屬為析音詞,如晉中話的“不爛(絆)、黑浪(巷)”、山東話的“都婁(兜)、出溜(抽)”等。在這些方言詞中,原本的兩個獨立語素一旦構成“嵌l詞”后,便成了只記音不表義的非語素音節。析形詞、析音詞純粹是起記形、標音的作用,沒有實在意義。于是一旦進入這兩類詞,原來的語素便被非語素化了。
3.借用外來詞
音譯外來詞的本質是把外語詞中的語素音節非語素化(楊錫彭,2003)。chocolate是以可可粉為主要原料,加糖和香料等制成的食品。它本是一個都是有意義的英語詞,但“chocolate”的音譯詞“巧克力”從字面上我們無法分析出這三個字有什么意思上的聯系。音意兼譯詞(主要是“音譯+意譯”詞)中的純表音部分也屬于語素的非語素化,如“烏托邦(Utopia)”中的“烏”“托”是音譯的部分,純粹是無實義的音節,已經被非語素化了。
意譯詞中也存在非語素化的現象。例如:“broadband”在漢語中被按照英語語素對應翻譯為“寬帶”,意思是模擬通信中指頻率大大高于話音的帶寬,數字通信中通常指傳輸速率超過2兆比特每秒的帶寬。表面看來,“寬帶”是兩個有意義的音節,其實它是“寬”與“帶”的無理組合,與傳統漢語詞“寬帶(指衣帶寬松。形容腰變瘦)”并不具有同一性。所以很多借詞其實是外來語素在漢語中的非語素化。
4.諧音借代詞
俗語詞、口語詞在書面上采用記錄方言口音的俗別字或音近字替代記寫,使得一些詞的既有結構發生“重新分析”。老南京話中的有個詞在正式的書面語中寫作“老車”,意思是“老練、老到”。追根溯源,“老車”源自上海話中的“老鬼”。南京話在借用這個詞的過程中,根據上海話的發音對照記寫,便成了“老車”。而對“老車”詞義的理解多半集中于“老”字,與“車”無關。因此“老車”一詞中的“車”只是記音的書寫符號。
除此之外,地名因需要避污穢、避忌諱、受意識形態的影響或者要求書寫簡便等原因而改換諧音字也會造成語素音節的非語素化。如“巴巴胡同”改為“八寶胡同”,“兔兒山”改為“圖樣山”,“中官村”改為“中關村”,“雞罩胡同”改為“吉照胡同”等等,后者中的“ 八 ”“ 寶 ”“ 圖 ”“ 樣 ”“ 關 ”“ 吉 ”“ 照 ”雖大致保留了“巴”“兔”“兒”“官”“雞”“罩”這些語素的音節,卻丟了它們的意義。
5.類推變詞
漢字記寫心理是習慣在每個字的形體上顯示出該字的意義類屬,但有時在造字或用字的過程中給字增改形旁恰如“畫蛇添足”,反而使最終成詞的內部結構和內部形式發生變化,導致了語素的非語素化。如“蜥易”和“師子”“駝鳥”等,它們最初為外來詞,后給“易”“師”分別加上義符“蟲”和“犭”或改義符“馬”為“鳥”,最終成為“蜥蜴”“獅子”“鴕鳥”等進入漢語詞匯,而這些新造字與原字意義無關且改變了原詞的內部結構。造字的本意是“以形顯義”,結果所造之字進入該詞后雖然保留原音,但是不光失去了字義,甚至影響了詞義,最終導致語素的非語素化。
然而,與之相對的由簡化字所構成的詞并不屬于類推變詞的范疇。因簡化前后的兩字僅僅在字形上有差別,是音和義完全一致的“等價”字,如“水溝”和“水溝”,我們一般不特意去作區分。
6.聯綿詞與擬聲詞
聯綿詞是由兩個音節聯綴成義而不能拆開的詞。擬聲詞又稱為“象聲詞”,是專門摹擬現實世界的各種聲音而自成系統的一類詞。這兩類詞中也含有非語素化的情況。如聯綿詞“婆娑”和“仿佛”中的“婆”和“佛”原本都是獨立的語素,但構成聯綿詞后便失去原義,只剩下音節。又如“篤篤”“撲通”“丁零當啷”中的“篤”“撲”“通”“丁”“零”也在進入擬聲詞后被非語素化了。
(二)存義失音
1.兒化
“兒化”是一個徹底虛化了的附加語素,在語音上表現為非音節的音素形式,在功能上具備區分詞義、區分詞性、表小指愛或增加口語色彩等作用(王媛媛,2007)。“兒化”中的虛語素“兒”不是一個獨立的音節,不具有獨立的聲調,而是附著于前一音節的末尾,與之合音生成“兒化韻”。如“花兒(huār)”“蓋兒(gàir)”“壺嘴兒(zuǐr)”“甁兒(píngr)”等詞中的“兒”的讀音已經不足一個音節,只作為一個表示卷舌動作的符號“-r”。然而由“兒”所構成的詞在意義方面卻保留了“兒”的語法意義,使得這類詞中的“兒”被非語素化。
2.合音詞
合音詞是指兩個音節合并成一個音節,合并后的音節詞義固定下來,并用一個漢字表示所合之意而形成的詞(張肖藝,2016)。傳統意義上的合音詞不少,如古代漢語中的“諸”是“之于”或“之乎”的合音詞,“盍”是“何不”的合音詞,“叵”是“不可”的合音詞,還有現代漢語中常用的“甭”“倆”和“仨”分別是“不用”“兩個”與“三個”的合音詞。
另外,還有一類網絡合音新詞也值得我們關注。網絡語言如此發達的今天,產生了一些獨特的合音形式,進而出現了一批網絡流行詞語。例如:
你造嗎?有獸為直在想,神獸我會像間醬紫古瓊氣對飲說:“其實為直都宣你!宣你恩久了,做我女 票 吧 ! ”(https://www.haha.mx/joke/2180021)
該例如果按照規范的現代漢語來書寫應為:你知道嗎?有時候,我一直在想,什么時候,我會像今天這樣子,鼓起勇氣,對你說:“其實,我一直都喜歡你!喜歡你很久了,做我女朋友吧!”這其中依次出現的“造”“獸”“為”“間”“ 醬 ”“ 古 瓊 氣 ”“ 宣 ”“ 票 ” 分 別 是“知 道”“時 候 ”“我 一 ”“ 今 天 ”“ 這樣 ”“ 鼓 起 勇 氣 ”“ 喜歡 ”“ 朋 友 ”這些詞以合音形式創制的新型網絡詞匯。
有的合音詞可以直觀地從字形上看出它與合音成分的詞義聯系,如“甭”“倆”和“仨”等等,但有些從字面上是看不出的,如“諸”“盍”“叵”等,尤其是那些網絡合音新詞,更是相去甚遠。不論是傳統意義上的合音詞還是網絡合音新詞,其本質都是在保留原來語義的基礎上發生了音節的合并。然而,當我們把這些詞回歸于語法功能,便能夠分析出合音詞可以代替合音成分在句中的位置,同時并未改變語義。所以,合音詞是屬于存義失音類型的的非語素化。
三.非語素化的原因探究
(一)漢語音形義的互動特性
古漢語單音詞多,通常字就是詞,形、音、義三者牽一發而動全身。現代漢語在它基礎上發展而來,雖復音詞多,但字(詞)的音、形、義聯系緊密,若一方改變,很可能影響其他。非語素化的產生是音、形、義間互動影響的結果,如切頭詞的非語素化是雙音化的產物,析音詞、借用外來詞、諧音借代詞等非語素化也充分體現音義間的互相影響;析形詞和類推變詞的非語素化也與字形密不可分。
(二)語言經濟性與語法作用
語言經濟性原則是語言應用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原則。一般情況下,人們能使用簡單明了的表達形式來傳達完整的信息,便不會優先選擇復雜的語言形式。兒化與合音詞都是因我們在發音時將幾個詞的音節進行經濟性地合并而最終產生了語素的非語素化。在做語法分析時,生動后綴經常被當作一個整體來處理。從而在語法作用的影響下,幾個語素進入生動后綴后便發生了非語素化。
(三)民族的文化心理與個性
中華文明在發展的同時也形成了漢民族獨特的文化忌諱、避諱等,因而產生了一批諧音借代詞。漢民族具有特殊的記寫心理習慣,喜歡把字加上能顯示出它意義的形旁,以便達到“目擊道存”的目的。合音詞自古以來就存在于漢語之中,而網絡合音新詞的出現則是人們在實際運用中想要以一種新奇的語言形式來凸顯個性、博取眼球的結果。這些民族文化心理與個性造成了一批漢語詞匯出現非語素化的現象。
(四)社會發展對語言的影響
語言產生于生產、生活中的交際活動,然后在廣泛的語用中約定俗成,始終與社會的發展亦步亦趨。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化、對外交往的需要與科學技術的進步等都會影響到語言,使其變化發展。不論是“舊瓶裝新酒”“新瓶裝舊酒”還是“新瓶裝新酒”,社會的發展對語言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現代漢語語素的非語素化,如借用外來詞、網絡合音新詞等的非語素化現象,是社會的發展影響到語言的重要表現。
四.結語
若從音義結合的實際情況重審語素,我們就會發現詞中的語素并不一定是一個標標準準的“語素”,有可能是失了音或義的非語素單位,這正是現代漢語語素的非語素化現象的實質。呂叔湘(1980:3)提出“漢字對詞形的影響”是漢語語法特點之一,即漢字的書寫形式可能改變詞的內部結構和內部形式。這一觀點基本上解決了“存音失義”這種類型的語素的非語素化問題。至于“存義失音”這類語素的非語素化,這主要是由口語發音習慣造成的。這兩個因素導致詞的結構、功能、讀音和意義發生“重新分析”——即不改變表層表達形式的結構變化,使語素產生非語素化。
漢語音節語素化是漢語語素構成的主要趨勢,而語素的非語素化是一種逆向變化,雖然較少,但是很有特點。語素的非語素化,從內部原因來看,它與漢語音形義的互動特性、語言經濟性與語法作用密不可分;從外部影響來看,它是民族的文化心理與個性和社會發展的共同結晶。對語言中這一現象的認識和分析可以對我們的漢語方言、漢語語音、漢語詞匯以及漢語語法等方面的研究產生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呂叔湘.語文教學中的指導原則[J].漢語學習,1980(1).
[2]楊錫彭.漢語語素論[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89-94.
[3]楊錫彭.漢字與“重新分析”[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4):7-9.
[4]笪遠毅.切音詞和析音詞[J].安徽師范大學學報 (人文社科版),1986(1):114-119
[5]師玉梅.論“嵌l詞”的起源[J].中州學刊,2007(3):249-251.
[6]王媛媛.漢語“兒化”研究[D].暨南大學,2007:16-17.
[7]張肖藝.網絡合音新詞語探析[D].青島大學,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