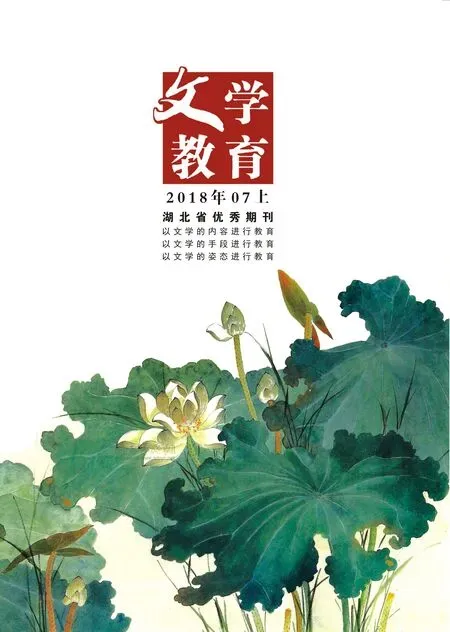海外文壇
●丹·布朗首次來中國暢談《本源》與創作心路
從《達·芬奇密碼》中令人嘆為觀止的真相揭露,《失落的秘符》中百轉千回的陰謀,《地獄》中迫在眉睫的人口爆炸危機,再到新作《本源》里對人工智能的探討,丹·布朗的蘭登教授系列小說,受全球讀者歡迎。日前,丹·布朗首次來到中國在上海書城與讀者見面。見面會上,丹·布朗回憶說:“我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第一本小說《數字城堡》,在美國出版初期只賣掉了12本,其中6本還是我媽媽偷偷買下的。”說起初出茅廬時候的窘迫,丹布朗并不掩飾,他用“血、汗、淚”來形容從文學新人到暢銷作家的進階之路。“成功的秘訣并不復雜,要花費很多心血,要努力工作,當然我的幸運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碰到了對的編輯、對的出版社,讀者也愿意讀我寫的東西。但我永遠不會忘記曾經只賣出12本書的日子,我感激這段經歷。”新書《本源》中繼承了他此前小說的特色,憑借獨特的“掉書袋”“冷知識”敘事手法,將文學、藝術、建筑、哲學、物理學等各種跨領域知識點融合在一起,引誘讀者一起解碼。為何對密碼學情有獨鐘?“實際上,這跟我小時候的生活習慣有關,我的父母親過圣誕節時給孩子準備禮物的方式很特別,圣誕樹下放的不是禮物,而是一串紙條,上面寫著密碼線索。比如先去廚房打開冰箱,冰箱里又埋藏了下一個線索,直到最后找到寶貝。我很喜歡這種找禮物的方法,相信讀者也會在小說中獲得同樣的樂趣。”
●巴西詩人克里切利認為詩歌給予生活力量
“詩歌是鏈接精神、情感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媒介。隨著社交媒體和新聞對文字語詞的侵蝕,我們正在慢慢失去對它們的掌握。詩歌是賦予文字力量并進一步給予生活力量的東西,我們可以通過文字來形塑生活,詩歌是一種抵抗的形式。”1982年出生的巴西詩人弗朗切斯卡·克里切利是巴西年輕一代詩人在國際舞臺上最有知名度的一位。近日,她來到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成為該館“詩歌來到美術館”活動第49期的嘉賓。克里切利的父親是巴西人,母親是意大利人,在巴西、意大利、馬來西亞、墨西哥、西班牙多國成長生活過,天然是一位擁有全球化背景的詩人。“在一段時間內,我在猶豫我究竟是意大利人、巴西人,抑或世界公民?那個階段可以稱之為我的身份危機時期。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意識到國籍并不是那么絕對。在意大利、巴西或者世界各地所生活的經歷實際上都是幫助我去理解這個世界。”而她對于詩歌語言的選擇也經歷了一個困惑到澄明的過程,曾分別用意大利語、英語、加泰羅尼亞語寫作過,但最終她鎖定了葡萄牙語作為詩歌語言。克里切利也是一位活躍的翻譯者。她翻譯了很多意大利語重要的詩人作品,包括朱塞佩·翁加雷蒂、馬里奧·盧齊、皮埃爾·保羅·帕索里尼、賈科莫·萊奧帕爾迪、雅科波內·達·托迪等人。
●“龔古爾獎”得主蕾拉為女性發聲
近日,浙江文藝出版社聯合京東圖書、聽道沙龍在京舉行了一場題為“當代女性面臨的誘惑、困境與突圍”的對談活動。出席嘉賓有法國“龔古爾獎”獲獎作家蕾拉·斯利瑪尼,中國當代作家張悅然、評論家楊慶祥,以及蕾拉兩部小說的譯者、華東師范大學外語系主任袁筱一。對話從中法作家筆下的保姆形象談起,共同探討當代社會女性面臨的問題。蕾拉·斯利瑪尼的《溫柔之歌》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中文版。這個從結局起筆的小說揭示了女性生存的艱辛、小人物的命運、愛與教育觀念以及支配關系與金錢關系。該書在斬獲龔古爾獎之前就是享譽法國的暢銷書,出版一年后法語版銷量超過60萬冊,其英文版推出后,甚至被《紐約客》贊譽為“一部征服了法國的小說”;其中文版出版后入選新浪讀書2017年度十大好書、《深港書評》非虛構年度十大好書等多個年度好書榜。緊隨《溫柔之歌》后,蕾拉又推出《食人魔花園》,該書講述了一個巴黎都市女性在欲望中沉迷和掙扎的故事。正如譯者袁筱一在后記中所說,蕾拉這位米蘭·昆德拉的追隨者,觸碰到女性內心深處的“不能承受之輕”,觸碰到“我們身下那片空虛里發出的聲音”。而對于蕾拉來說,她堅信文學的力量,要為女性發出溫柔且尖銳的聲音,打破關于母性的神話和謊言,進而以文學的力量去改變讀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