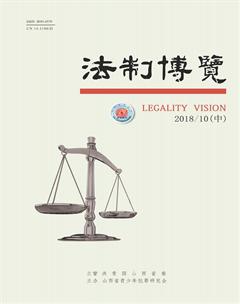淺議公安機關如何更好的支持配合打擊非法社會組織
何欣 孫小媚
摘要:隨著我國社會結構的日益變化,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不斷取得進展,大量社會組織涌現,其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顯,社會組織的規模越來越大,活動越來越頻繁。但是,非法社會組織大量存在,屢禁不止,公安機關必須立足自身職能,支持和配合打擊非法社會組織,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大局穩定。
關鍵詞:公安機關;非法社會組織;打擊整治
中圖分類號:D63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8)29-0106-02
作者簡介:何欣(1987-),男,漢族,四川渠縣人,三峽大學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任職于巫溪縣公安局,研究方向:地方政府治理;孫小媚(1988-),女,漢族,重慶人,任職于巫溪縣人民法院。
隨著我國居民個人表達意愿的強烈興起,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體系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黨的十九報告》提出:“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截止2018年4月,全國社會組織共有約81萬個。但是,社會組織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各類非法社會組織也呈增長態勢,特別是一些非法社會組織拉大旗作虎皮,行騙斂財,損害了社會組織的可靠性,影響了市場秩序和社會穩定。為了切實維護公眾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為社會組織發展創造清潔的環境,公安機關必須立足本職,堅定不移地支持和配合打擊非法社會組織。
一、打擊非法社會組織的現狀
(一)行政執法層面
根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三十五條之規定,取締的對象為:即未經批準,擅自開展社會團體籌備活動;未經登記,擅自以社會團體名義進行活動;被撤銷登記的社會團體繼續以社會團體名義進行活動。
雖然公安機關不是取締非法社會組織的主要執法單位,但在實際工作實踐中,大量行政執法單位在進行調查、取證,甚至進行處罰時,經常要求公安機關一同介入。但公安機關畢竟不是查處取締非法社會組織的主體,在民政部門進行取締工作中,通常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十條第一款第二項,若有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處罰,以保障民政部門工作人員依法、順利的進行取締工作。
(二)刑事執法層面
《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這兩個行政法規中,明確規定非法社會組織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實踐中,大量非法社會組織都是冒充身份、虛構事實,以騙取居民的財物,通常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之規定,以詐騙罪追究相關責任人的刑事責任。
二、公安機關打擊非法社會組織面臨的困境
(一)介入前提不足
當前,我國對于社會組織的登記管理一直遵循“雙重管理”的制度,社會組織必須在民政部門登記之前找到相關業務單位。因此,社會上有大量未登記的社會組織。但對于未登記的社會組織是否一律認定為非法社會組織,在理論界與實務界一直爭論不休[1]。故而,民政部門在查處疑似非法社會組織時,不能統一思想,底氣不足,自身不硬。則,若遭遇對方阻礙,公安機關也不能簡單認定對方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粗暴以“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對其采取治安處罰。
隨著我國對民間組織問題的日益重視,各級政府部門相應加強了民間組織在政府機構調整中的管理。在縣級民政部門,普遍設立了“民間組織辦公室”,專職人員負責具體管理工作[2]。但是,《取締非法民間組織暫行辦法》明文規定,當登記管理機構對非法的社會組織進行調查時,執法人員的人數必須是兩人以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中,也有類似規定。
此外,在《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中明確規定“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但畢竟公安機關并非社會組織的主管部門,即使一些非法社會組織構成詐騙違法的治安違法行為,但只要民政部門不移送,公安機關就無法得知,更加談不上對責任人給予治安管理處罰的行為。
(二)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不暢
不少非法社會組織的特點是抓住少數人對名利的不良需求,通過精心包裝、蹭“熱點”、招搖撞騙,大肆斂財。這類行為通常已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相關規定,已涉嫌構成詐騙罪、招搖撞騙罪等犯罪行為。但是,實踐中,對于此類犯罪行為的查處,通常是先由民政部門初步調查取證后,再正式移送給公安機關。由公安機關刑事立案后,再依法進行刑事打擊。
根據《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第三條之規定,行政執法機關在依法查處違法行為過程中,發現違法事實涉及的金額、違法事實的情節、違法事實造成的后果等,根據刑法關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釋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經濟犯罪案件的追訴標準等規定,涉嫌構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必須依照本規定向公安機關移送。這就是各行政執法機關確定案件是否應該移送的標準表述,也就是說如果發現案件違法事實涉及的金額、違法事實的情節、違法事實造成的后果等,達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的,則應當移送案件。
但是,部分行政執法人員對刑事追訴標準不熟悉,部分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界限模糊或操作性不強,導致行政機關難以確定案件是否應當移送。而且,從行政機關受理調查到移送公安機關時間周期較長,行政機關調查案件時固定證據不充分,程序要求達不到刑事案件的規范程度。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此規定將受害人陳述,證人證言,違法行為人前期的陳述和申辯等言詞證據均排除在外,要求公安機關在刑事立案后,重新予以收集。但絕大多數受害人與證人都不是辦案單位本地人,在行政執法單位好不容易收集了前期言詞證據,又要求公安機關再次對其重新進行詢問,浪費大量公共資源不說,還不一定能重新收集到受害人和證人的筆錄。
三、有效打擊非法社會組織的對策
(一)靠前掌控
針對大量非法社會組織和民政執法能力較弱的情況,各級公安機關有關部門和基層社區民警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徹底進行全面摸底和調查,對各行業和轄區內存在的登記或未登記的各類社會組織,能夠清楚確定其規模、數量、范圍、影響和作用等,并逐個建立檔案資料,做到“底數清、情況明”,確保常見社會問題共同預防,重大社會隱患提前預警,群體性案事件協商解決,不等不靠,牢固掌握社會輿論和公共安全管理與控制的主動權。
(二)精準打擊
要在平時加強自身能力學習,提高相關刑事司法打擊的能力。在接到群眾報警或者民政部門查處非法社會組織時,不必要等到民政部門正式移交案件后才介入,提前從收集證據,偵查要點等方面進行指導,對重大問題共同參與,完善證據鏈條,嚴厲打擊違法犯罪行為。
最后,要堅持依法打擊和源頭治理相結合,通過完善日常監管和長效機制,依法打擊非法社會組織實施違法犯罪活動,通過積極支持配合民政部門,為維護社會穩定,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作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張尤佳,隋軍,李昂.“非法”社會組織界定問題初探[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13,15(06):50-51.
[2]謝海定.中國民間組織的合法性困境[J].法學研究,2004(02):17-34.